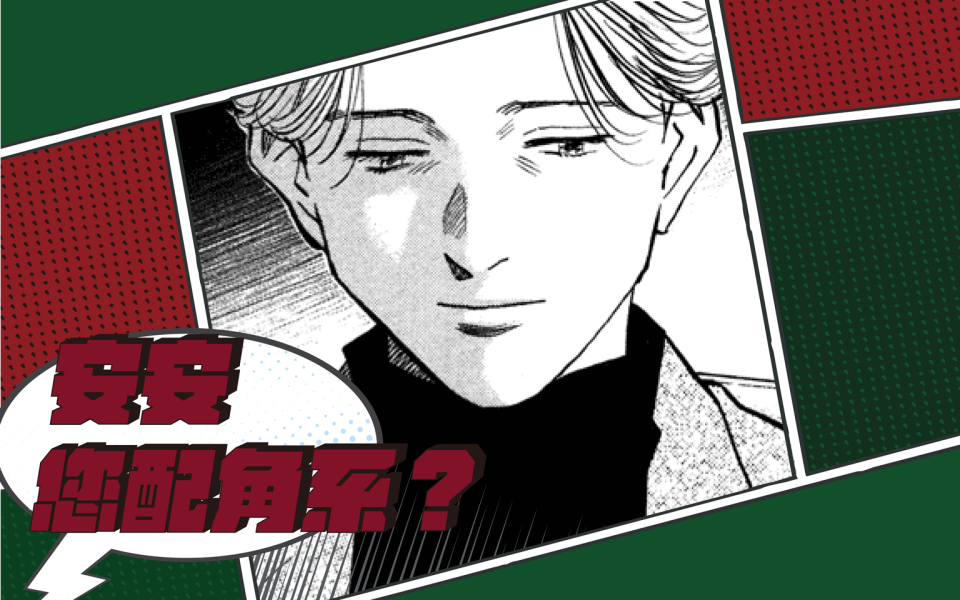
趙鐸・安安您配角系 EP3|殺人很簡單,只要忘記砂糖的味道:浦澤直樹《怪物》
殺了你,是為了找到你
「我不知道患者的善惡。」
「我的罪,是救了那個少年一命。」
「但是人命是等價的。」
「醫師有權力根據患者的善惡來選擇是否要救他們嗎?」
——天馬醫師
人類的性命究竟是不是等價的?
《怪物》故事的開頭,在西德行醫的日本籍天才外科醫師天馬賢三,某天在院長的指示下,不顧入院的順序,先行對較晚入院的知名聲樂家進行手術;被他棄置不顧的外籍勞工在技術較差的醫療團隊手下斷送了性命。從此,天馬便不斷自問這個問題。
.jpg)
一日,同樣的兩難再次上演:帶著雙胞胎養子,從東德逃離到西德的李貝特夫婦慘遭不明人士殺害,倖存的只有失語震撼的妹妹妮娜,以及腦部中彈性命垂危的哥哥約翰。而這次,較晚入院的是心臟病發的市長。由於聲樂家事件的動搖,天馬決定違背院長意願對約翰進行急救,而原先被視為院長接班人的天之驕子天馬,也因市長的死亡斷送前途。
捨己為人的天馬,沒想到這個信念之舉,令更多生命終結。九年過後,德國境內共有四對中年夫婦慘遭殺害,而這一系列連續殺人案的兇手,就是當年天馬搶救成功的約翰。
約翰為了「報答」天馬的恩情,下毒殺害了藉故排擠天馬的院長和他所挑選出的一群天馬的繼承人。約翰的行為,讓天馬被 BKA(德國聯邦警察)警官倫克列為重要嫌疑犯。天馬荒謬的證詞,倫克警官自然沒有採信,而救回殺人犯的天馬抱持著難以抹消地「罪惡感」,決定親自追殺約翰,開始一場亡命旅程。
天馬這趟追緝/殺旅程與其說是為了證明自身的清白,不如說是一場對於「人命價值為何」自我拷問之旅。這趟旅程的意涵,也與約翰究竟為何要「陷天馬醫師於不義」互為表裡:追殺過程中,天馬將體會到悖離眾人認知、為近乎信念的真相奔走的終極孤獨。同時,約翰的存在價值,也在被堅持「人命等價」的天馬追殺時被反向地證明了。
「就我剛才從你的話裡感覺到的,你簡直就是不是要證明自己無罪,只是想證明約翰這名青年的存在而已⋯⋯你給我這種感覺。」
「那個,你並不是需要律師。不希望獲得無罪判決的人,要如何去為他辯護?」
—— 博德曼律師
.jpg)
追殺約翰的過程中,天馬收到約翰的求救信號:「天馬醫生,看看我!看看我!我身體內的怪物已經變得那麼大了!」為了逃離埋藏在記憶深處那牽連著國族歷史的黑暗侵襲,約翰一次又一次殺害收養自己的夫婦,只為了抹消掉自己的存在。約翰體內中的「怪物」不斷地被餵養長大,使他成為一種近乎作為「非人類」的存在。殺戮不只表現約翰的殘酷,也表現他能夠輕易地操縱人心,激發人性當中毀滅他人的衝動。
就結果而論,天馬也被他操縱著。
約翰所犯下的殺人案件,在犯案現場中總是留下讓人難以置信的恐怖氛圍——不是強烈地蹭恨,更非無盡的悲傷,而是沒有任何動機的、以殺人為目的本身的虛空。
被日常排除的真相
約翰自小就展現出這種毀滅性的領袖魅力。他曾經在自己長大的地方、前東德收養間諜後代與孤兒的虐童機構「 511 幼兒之家」中,誘導一場彼此鬥爭與殺戮的「革命」。約翰因此成為柏林圍牆倒塌過後德國極右派激進份子意欲簇擁的新時代君王。然而,《怪物》作者浦澤直樹無意把約翰塑造成為現代的極權暴君,相反地,約翰像是吸食歷史業障而遊走在正反派角色之間的亡靈,對於權力和名利都沒有興趣,存在就是為了彰顯毀滅自身。
「這個國家的人,要的只是代罪羔羊而已」「讓無罪的人背上莫名之罪,想把事情隨便解決的法官、檢察官,這個國家無論何時都在重複相同的錯誤。」
——博德曼律師
但無論約翰的毀滅效應如何強大而真實,卻沒有佐證他存在的記憶與歷史。約翰這個角色,正象徵著過往曾經鑄下錯誤與創傷、卻選擇集體失憶的社會之病徵。失憶的集體急欲尋找轉移焦點的代罪羔羊(天馬),只為了磨平異常、讓日常繼續照常運作。
這些被磨平的異常,只能透過「妄想」的變型鏡才得以辨識出來。這就是為什麼倫克警官根據「常理」,判斷兇殺案最大的受益者天馬才是兇手的不二人選。儘管事情的走向越來越不符合他的推理,但由於「約翰」的存在無法被證明,倫克被迫解釋約翰是天馬醫生腦中妄想所創造出來的雙重人格,必須在跳脫日常儀軌與工作倫理的漫長時間(倫克稱之為「假期」)中才有被辨識的可能。日常,竟成為了區隔我們與真實之壁。
「實際存在的人,要如何成為架空人物呢?答案很簡單。便是將認識那個人物的人、知道那個人物過去的人全部除掉,將那些人的朋友和四周的人也除掉。」
「妄想之旅終於成為現實了。我這段純粹依著妄想之線而走的假期也結束了。」
「天馬醫師,抱歉。」
——倫克警官
當幽魂被承認
《怪物》最讓人驚艷的安排,是一手創造出約翰的法蘭茲・波納帕達,同時也是一位繪本創作者。他所創作出的繪本《沒有名字的怪物》不只是他們慘無人道對新生兒實驗的理論宣言,同時更是這段他急欲抹消的歷史之見證。他不只引發約翰在故事中唯一強烈的情緒反應、決定踏上他的「尋根之旅」,更是讓倫克警官開始相信約翰存在的關鍵證據。
當倫克在故事最後終於承認約翰的存在時,他口裡囁嚅著「妄想終於成為了現實」——我們終究必須面對歷史創傷所餵養出來的巨獸,而後才能重新整合既有的倫理,並再次估量人類存在的邊界。
.jpg)
「繪本」在故事推進中見證了「故事/敘事」作為妄想和現世之間虛實轉換的媒介,並蘊含著創造與毀滅的雙生——故事中也以約翰和妹妹作為意象:如果說,約翰代表的是過往的傷痕所幻化的幽魂,對集體的失憶進行末世性的審判,妹妹妮娜代表的則是在重新創造回憶的過程中,對過去傷痛進行安頓與創造性的轉移。
「如果沒有快樂的回憶的話,只要製造就好了。天馬是這麼說的。」——迪特
《怪物》這部作品野心之大,牽涉到的價值重估不僅是個人的,同時也是歷史與集體的,更可以上綱到人類存在根基的肯可與否。當最後一集天馬與約翰對峙,一位父親衝動射殺約翰,乍看之下是為了救回被約翰當作人質的兒子,真相則是約翰在他的眼中以「怪物」的形象出現,而牽引出這位父親欲將異類進行消滅的衝動。
這個微妙的情節,不只貫串了整部作品意欲表達約翰作為兇手的「不可辨識性」,更凸顯了一次次以槍口對準約翰卻猶豫不決的天馬,原來自始自終都把約翰當作是「人」來看待。
「那天我也像平常一樣地瞄準⋯⋯我不知道那是第幾個人,也不知道他是誰。它就坐在正中午的一家咖啡店裡。一切都跟平常一樣。這個人叫了一杯咖啡。然後開始放砂糖。一匙、兩匙⋯⋯三匙、四匙⋯⋯當他放到第五匙時,我口中突然充滿了平常喝的咖啡的味道。這個人很享受地把它給喝了下去。於是我便把槍放下來了。」
——羅素先生(前職業殺手)
忘記砂糖的味道
漫畫中,和約翰一樣同為 511 幼兒之家出身、被培育出「超人人格」的葛利馬,在成為國際間諜的目標下長大。練習各種情緒的過程中,他學會了最難的「笑」,成為一個總是堆滿笑容的人,卻喪失了所有情緒。
直到死前,葛利馬才因為感受到悲傷,而深感幸福。
打造出超人的夢想,最終只能生產出沒有人性的怪物。與葛利馬相對,約翰懼怕失去妹妹妮娜,為了消弭自己的行蹤而殺戮,最後墮入深淵——關係與愛,和人類的肉身性互為表裡,人類終究無法丟失掉情感並否定自身存有的肉身性。
.jpg)
《怪物》當中一個頗有意思的設定,是天馬和妮娜在追殺約翰的過程當中,不斷與不同的人、甚至曾經冷酷的殺手邂逅,體會到一同共進晚餐的溫度,重新再一次拾得對於人命與關係的珍視。
教導妮娜槍法的「前」職業殺手的一句話,因此成為了整部漫畫最震撼我心的文眼:「要殺人是很簡單的,只要忘了砂糖的味道就可以了。」
「有一個惡魔,為了尋找消滅世界的龍而出來旅行,卻在途中病倒快死了。一個路過的青年救了惡魔的命。後來青年知道自己所救的是惡魔,便追上去,好不容易找到惡魔的青年,手裡拿著刀,殺死惡魔。」
「要是我的話,我會這麼做。但是,我不能讓他這麼做。⋯⋯如果是人類的話,就會救那個惡魔」
——妮娜
作為一部具有懸疑推理外殼的作品,圍繞《怪物》的「謎團」,與其說是客觀等待抽絲剝繭的事實,不如說是「偵探」與「兇手」自身的心理迷宮彼此交織所構築的圈套。浦澤直樹將「兇手是誰」的問題從一個客觀知識的問題,上升成為屬於人類存在處境的難題,同時也將「緝兇」的行動,從特定前提下才能產生效力的舉證與搜查活動,後設地逼迫我們思考「事物的前提,究竟如何驅使我們對於真相的認定」,最終成為一場重估價值的、存在主義式的探索旅程。
【安安您配角系?】
心痛比快樂更真實。配角比主角還更有戲。如果說主角是價值拓荒旅程的開創者,創造可能性的天選之人,配角則是關於人的限制的輓歌,變相地以競爭者/失敗者之姿成為主角前往理想之地的引路人。為了永恆的贖罪,甘願上演自己被否定的戲碼,成為價值拓荒旅程中人類原罪的承擔者。
【趙鐸】
趙鐸,台北人。如果世界是座巨大的圖書館,祈願成為那位說書人。碩士班研究禪宗及心學,期許能完整理解近代歐陸哲學,第五屆金馬影展亞洲電影觀察團成員,影評見於粉專《藏書閣》及釀電影,和影評人甜寒合作 Podcast「字戀男與變焦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