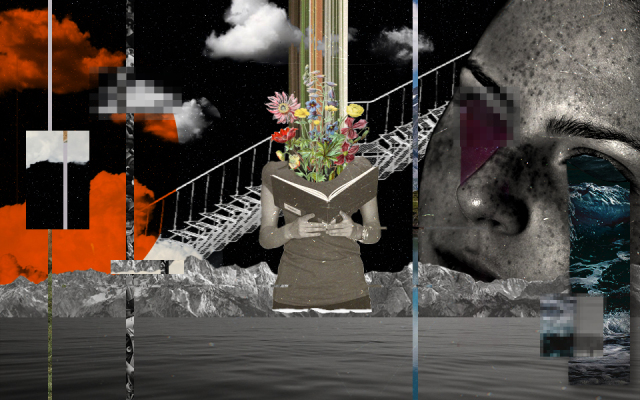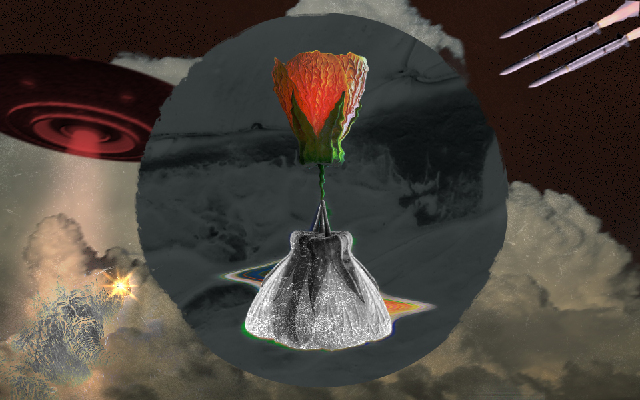黃以曦・夢遊之城|如何開口說話
我的書房有加厚的牆,特殊材料的門與窗,這是個碉堡,是最安靜的地方。走進書房,我可以不必知曉外面、到處,都發生了什麼。
但事實上,我只是沒聽到,並非不知曉。我知道,而且全部知道。今天、昨天、明天、每一天,都那麼喧鬧。綿綿流過的電視聲,腳步上上下下、走來走去,窸窸窣窣,翻找東西,然後開口。他們開口,停不下來。誰的哭鬧或嘻笑,誰的斥責或溫柔安撫。然後妻說,「噓,小聲一點,爸爸在寫作。」
最早的時候,孩子們不懂,安靜是什麼,寫作又是什麼。再來,孩子們好奇地問些什麼,狐疑地上前碰碰碰大聲敲門,再來他們不理會妻,也不在乎我,扯著嗓子,想多大聲,就多大聲。
妻從沒有對我說什麼。沒有抱怨,沒有寒暄,抗議似地,不打擾我,又或者,我想,她感覺對我的話語俱是多餘。因為我可以寫出她一生中說的所有的話:她曾說過的、她將說的、她能說的,她吞下終究沒有說出可其實也幾乎或已然存在的。又或者妻並不那樣感覺,但她認為我會那樣想她。
那簡直不可能是同一個人。妻沉默地送來或取走了餐食、換洗衣物;調過頭,她就同孩子們、同鄰居與親戚、同電話上或門彼邊或街上的人,那麼不害怕也不猶豫地,說個不停。
而我,我並沒有刻意不說話,我只是不再感覺到哪句話的非說不可。那些因應情境的話語太理所當然了,像是很早以前就在那裡,每個人已全部知道;如此,則當我真將那說出口,就只是在重複一句話。
事實上,當偶爾說話,我總是忍不住越說越快,或戛然中止,我想只要開了頭……不,甚至不必開頭,人們已知道接下去的段落都是些什麼。可他們還得從頭待我說完。像面對一場看了無數次的秀。我立刻焦躁了起來。
然而,我自己不說話,卻無法忍受妻面對我時的寡言,或甚至沉默。是的,我們並不需要話語就可以令訊息傳遞,但當話語被冷硬撤離,卻是將房子、一個磚頭、一個磚頭地取出。不自然,而且危險。我以為那是一種拒絕。
妻要說的還能是什麼?我頑固鎮守一座碉堡,在裡頭寫作。寫一群人,他們互相說了好多話,用話語從無到有地纏繞生存其中的脈絡,話語交代了他們是誰、想要什麼、按下與發動的念頭。一個故事等在彼端,更多的故事被織出。
你憑什麼?可妻要說。一個不說話的人憑什麼寫一群說話的人,假裝世界能被語言所織就?
難道你我的世界……不,是我為你守護起的世界就不算數?你有了個現成的、什麼都自動運轉的情境,一幢你以為自在又安心的關係,你就覺得由此生產出的話語俱俗氣而多餘?你以為情境會永遠轉動?你怎麼會這樣想?當你雕琢著人物用精巧的字句在打磨他們的關係、在維繫四季,那麼樣地少說了什麼就是遺憾、就讓永恆有了缺口,但你卻以為你在這裡,可以不說話。妻必定這麼說。
這些話,她是說得起的。她是這樣的個性,她傾向這樣的邏輯,她甚至可能熟練那些字句。可她從沒說過。平淡的版本、暗示的版本,都沒有。她那不曾迴避我的眼神,甚且是平和的,在最深處也無揶揄。
確實,何必說出口?如果起了具體的心意, 無所謂藏在深處。那若是要給我看的,她知道我將總是看得到的。就連根本不去凝聚與浮現的那個揶揄,我亦能看到,只要我知道那裡會有。
現實難道會比我寫下的字句更為深沉?如何有一幢沒有交鋒、靜悄悄而微笑著的緊張?我寫過那樣的東西嗎?也許我真寫不出一齣語言缺席的對峙。可在我的日常生活裡,那是如此尋常。
不再有人和我說話了,我不再開口了,空氣冰凝。
我仍記得和妻共同擁有的柔情的日子,只是很快地,我遁入我的碉堡。我想我並不是真的不再願意和妻說話了,可如果我的心思真仍在那裡,我該感覺到某些非說不可的話?總會有些話輕鬆地流了出來?像我的人物們,他們總是唱歌一樣地說起話來。一發不可收拾。流洩的音樂。
寫個和我很像的角色、模擬此時此刻的生活呢?就會有話語在我們的生活裡滿載了是嗎?我會對妻說話,她再對我說了很多;我會走出書房,對孩子、對訪客,我上街,對忙碌的小小市街上的哪個人,都說些話。有些話語為了意義而成立,另些則鋪設出一個低度、平實的日常介面。妻說得沒錯,我怎麼會以為,不說話,四季也能轉動?
我立刻寫了個短篇故事,寫得太快了,故事冒動地想變成中篇、長篇,已登場的人物熱切地拋擲話語、幾乎點燃地催生新的人物。我顧不得美學,潦草地搶著結束。情節還來不及收起來呢。可我在腦中勾勒兩種三種各種評述,未完成本來就是一種完成。
那天,我感覺自己是燒燙的,好像在一個房間裡集合了眾神,祝福與詛咒集聚一堂。我想我太急了,急著在空曠中擘劃一條打開未來的路。因為這樣,妻送來的早午餐與晚餐,還擱在門邊。寫下最後一落主角的念白,斷然停筆。不,不能再給誰還要接上怎樣各式各樣的回應。我感覺到巨大的飢餓,但更多的是說話的渴望。
好久沒有這樣的感覺。我忍不住隨意亂說幾個字,感覺發音、感覺聲量;再多說一兩句,感覺字句組裝在一起自然形成的開口、關閉、起伏和淡出。我都忘了!被說出的話語原來可以長出這樣的生命。但難道我筆下的人物就真的少了什麼嗎?我差點就忍不住要從這陌生又熟悉的新生的氣息,往回揣摩我剛寫好的故事,還有那無數無數的故事。
我略略提高音量,勇敢增加了抑揚頓挫,用正式也更信賴的態度。起先我環顧書房,看到什麼字就念出來,即興加上與此無或有關的再一兩個句子。我很快感覺到想對人說話的亢奮。
就在那時,妻慣例性敲了敲門,隨即推開門。是宵夜時間了。外頭聲音忙不迭湧入,夜深了,但仍有那麼多聲音,女兒講電話細瑣的字句也湧了上來。但無論如何,這已是比一整天其他時刻都更單純、因此更適合的時刻了。
妻並未預期竟會看到我在房裡來回踱步,轉頭看向推門進來的她,她並不迴避或掩飾什麼,但總之直接看了沒動過的之前的餐食,淡淡地說,「今天都不餓啊?」。說起來,這並非問句,妻的動作也連續性地朝向順隨地要離開。
「今天……」,我聽到自己焦急地開口,「今天我做了一個新的嘗試。」我說。妻有點驚訝,又或者這個驚訝其實是被隱藏起來的。我聽到自己的聲音,有顫抖,主要來自興奮,這樣一句話說出去,被直接地聽到,曾幾何時,於我已經是這麼新鮮的體驗。
故事裡那些話語的遭遇是什麼呢?它們事實上是整塊預先等待在那裡的命運大陸的一部份。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所說的話,都必須回到他們所在的平面,話語相嵌合。但此刻我的話,被拋在半空中,沒有人知道它能否被接住、被接好,而被收受下的那瞬間空氣又將如何變化。
「今天我做了一個新的嘗試。」我鄭重再說一次。如此,氣流開始滑進對的軌道。我,或說那個以我為藍圖的角色,開始說話。
【夢遊之城】
很多場景。無論我們可以做出如何的詮釋或編派,
我在電影裡看過太多的夢,多到以為那是我做的。
現在。這裡。全部。都是你自己的。
【黃以曦】
作家,影評人,著有《離席:為什麼看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