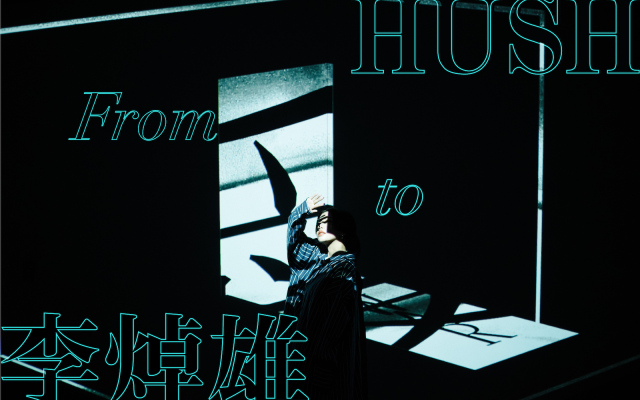你不只是聽歌詞,你變成了歌詞——張文玲 ╳ 李焯雄《WeWORD 字我訂造》新媒體展
導演張文玲做了二十多年演唱會製作,攤開合作名單,陳綺貞、蔡健雅、盧廣仲、伍佰、莫文蔚、五月天⋯⋯,陣容華麗非常。首次轉身投入策展,她邀請金曲詞人李焯雄。以流行音樂為基底,《WeWORD 字我訂造:流行歌詞及其創造的》試圖讓人游走在經典歌詞之間,體驗歌詞創造的宇宙。
如同演唱會是把歌曲的世界再放大,這場歌詞的展覽也不只是歌詞。展場裡不會有李焯雄的手稿或紀錄片,更不會有什麼「歌詞背後的創作故事」被貼在牆上,兩人試圖打造的,是從歌詞出發、卻比歌詞更大的體驗。
讓我們一起,走完一首歌
展覽選定李焯雄的十二首歌詞作品,莫文蔚〈忽然之間〉、〈不散,不見〉等首首耳熟能詳。以流行歌的架構規劃六個展區,觀眾走完展覽,也像感受了、共創了一首完整的歌。
〈SoundScape 聲音的風景〉、〈歌詞是聲音的建築〉、〈歌詞是情感的壓縮檔〉、〈歌詞是永恆的現在進行式〉、〈言無言〉、〈WeWORD 字我訂造 文字樹〉是李焯雄先行提出的展覽概念;張文玲接著以演唱會思維將它們分別對應至 Intro(前奏)、Verse(主歌)、Chorus 1(副歌 1)、Bridge(變奏)、Chorus 2(副歌 2)、Outro(尾奏),發展至此,整體展區也跟著定下了,只差如何落實。
.jpg)
兩人於是分頭尋找信任的合作夥伴:實力影像設計楊秀敏、叁式 UltraCombos 曾煒傑、陳建騏、Wing Shya 夏永康⋯⋯便紛紛到位。其中陳建騏負責展覽音樂,夏永康負責主視覺設計,展場視覺設計就由張文玲的老戰友楊秀敏統籌,「我長期跟秀敏合作演唱會,很喜歡她的作品,細節顧得好,對歌曲理解也非常深。」而總是能令人耳目一新的互動影像設計叁式,則是曾與張文玲在蔡健雅《列穆尼亞演唱會》合作過。如此夢幻的戰隊,會激發出流行歌詞的哪些可能?
李焯雄的展前導覽,從 Intro 的〈SoundScape 聲音的風景〉開始走起,「仔細聽,我們身邊都是有聲音的,流行音樂也是當下聲音風景的一部份,我們內心可能也有幾首歌一直在播放著,我們從這邊開始講故事。」步伐移動至 Verse〈歌詞是聲音的建築〉,「歌詞其實是用來唱的,歌與歌手都必須以聲音的方式來存在,歌詞是聲音的建築。」
「這個展區我們用〈紅玫瑰〉、〈白玫瑰〉創造出建築的對稱感[註1],還特別把兩首歌剪在一起。我們常說有 A 就不能有 B,張愛玲寫作時的概念可能也是這樣,但萬一都有,會怎麼樣?」若真如網路流行語所說「小孩子才做選擇,我全都要」,紅玫瑰還是會化為一抹蚊子血、白玫瑰還是會黏成一粒白米飯嗎?紅白色的影像視覺創作,音樂段落互相呼應,觀看的人也融入在這畫面中。「這超越了單一歌手、歌曲,是更大一點的概念,甚至可能是關於我們生命處境的一些思考。」
「得不到的永遠在騷動/被偏愛的都有恃無恐」——陳奕迅〈紅玫瑰〉,2007
「怎麼冷酷卻仍然美麗/得不到的 從來矜貴」——陳奕迅〈白玫瑰〉,2006
而你是否也曾有過這樣的經驗——當聽見某首歌最熟悉的副歌時,你與這首歌曾共享的時光,當時空氣的味道、體感的濕度、光線的明暗⋯⋯,以及那些愛過的,恨過的,傷過的人事物,統統像解壓縮一樣跑了出來。這就是為什麼,李焯雄說歌詞是情感的壓縮檔。
「對我來說,歌詞其實是心靈的載體,好像 zip 檔,你一碰到它,一串東西就出來了。」在這個展區裡,幾首經典的副歌會跳出來抓住你的心臟——「如果你也聽說,有沒有想過我?」、「我們都沒錯,只是不適合。」、「被自己寫壞,My Oh My,加倍草率」。此展區運用裝置藝術及互動技術,當觸動裝置歌詞即流溢出來。
在〈歌詞是永恆的現在進行式〉(Bridge變奏)區旁邊千萬不要錯過了隱藏版的彩蛋展區:〈為你而聲|藝人朗讀耳機區〉,可以讓你帶著自我最私密的記憶闖入。抽離旋律,戴上耳機享受一段專屬於你與歌詞的親密時光。在展場後段,〈言無言〉這個展區以〈無言歌〉為概念,提出了如此扣問:「意義到底有多少層?萬一字音與字型對不起來,那會是什麼?可以用語言去表達語言所不能表達的東西嗎?」展區以多片布幕投影、強烈影像對比,帶給你沉浸式的視覺與聽覺上的衝擊。
跟著 WeWORD 策展團隊的腳步,你將得以在觀展過程中累積創作能量,並於離去前在〈WeWORD 字我訂造 文字樹〉前停下腳步,成為共創展覽的一份子。
〈為你而聲|藝人朗讀耳機區〉將有魏如萱、梁靜茹、林宥嘉、A-Lin、HUSH、陳建騏等人朗讀歌詞、作品,觀眾可以戴上耳機聆聽。而〈WeWORD 字我訂造 文字樹〉由叁式打造,觀眾可自選兩組專屬字句,透過「分解重組」投入文字樹,植物景觀會因觀眾人數逐日變化。
說到底,「WeWORD 字我訂造」到底是什麼概念?李焯雄說,WORD 其實是個動詞。「我們自己選擇聽歌,好像主動在我。可是我後來想想,其實不一定,很常聽某些歌,這可能會養成一個慣性,某一些類型、某一些句子,會形塑我們的情緒反應、觀察世界的角度。」那些曾經在筆記本、教室書桌、公車椅背(小朋友真的不要學)抄寫下的字句,其實都或多或少地影響了我們面對世界的舉動。當我們在引用歌詞的時候,同時也被歌詞創造了,這就是流行歌詞的力量。
流行歌詞,讓你毫無防備
在創造一個以流行歌詞為主角的展覽之前,張文玲跟李焯雄也是聽者。
兩人都同意,組成一首流行歌的元素很多,但歌詞絕對是重要的靈魂,「我們為什麼會被一首歌打動?很多時候是被其中的句子觸動到,因此記得更深刻。」張文玲笑說,自己沒辦法像李焯雄講得那麼有深度,「但作為一個從小到大平凡的聽歌者,當下雨時,腦中自然浮現『當我走在淒清的路上/天空正飄著濛濛細雨』;看到陽光普照,就會唱『追逐風追逐太陽』。」年初剛卸下蔡健雅《給世界最悠長的吻》演唱會重擔的她,也在籌辦過程中被〈Beautiful Love〉再次打動,「因為這一年來,真的常常覺得世界就要崩塌了⋯⋯」[註2]。
李焯雄日前突聞友人離世,不常聽自創作品的他,竟也意外被自己療癒,「參加告別式那天,我突然想到寫過〈不散,不見〉,就放出來沿路聽。」寫歌多年,他當然深諳詞人的寫作手法與心機,更何況這首歌出自自己之手,「但我在那個情境下重聽,變成一個第三者在經歷朋友的死亡,非常微妙,好像是當年的我留言給現在的我那種感覺,被撫慰到了。」作為一個純粹的聽歌者是幸福的,拿掉所有防備,讓那些帶著聲韻的句子進入。魔幻的是,即使不是太專心,那些與你產生連結的歌,也會自動地印在腦海裡。
莫文蔚〈不散,不見〉,2014。李焯雄以此作品拿下第 26 屆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
在張文玲眼中,作詞人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極大,在生命的各個階段中,陪伴、安撫、擁抱。李焯雄於是提起流行音樂的極佳戰略位置,「我們心裡通常有個感覺:『不過就是流行歌』,這其實有點貶義。但它同時也是極好的位置,讓人沒有防備、沒有負擔地接收到你想說的話。」不為誰而寫,不排斥誰來聽,流行音樂就站在那裡張開雙臂,任你經過或停留。
繼續創造更多共振
即便掌握流行音樂脈動,兩人其實都是策展新手,起了頭,才發現是個大坑。
「展覽跟演唱會真的是兩個世界,加上我們是做一個原創的展覽,不像國外知名展覽進到臺灣,大家起碼知道它是展覽什麼。很多人都會問,蛤?歌詞的展?你是要展什麼?」一向表情相當收斂的張文玲,想起沿路收過多少贊助商的好人卡,只能頻頻苦笑。

張文玲曾與陳綺貞、蔡健雅、盧廣仲、伍佰、莫文蔚、五月天等合作演唱會,此次與李焯雄攜手策展《WeWORD 字我訂造》。
即便辛苦,她依然記得原點,是對中文字的痴迷。
她喜歡漢字的博大精深,認為中文的形、音、義太美了,轉化和運用的空間又有無限大。「我想做漢字的展覽,但又覺得做不贏那些學者專家。回頭想想,我們的專長是流行音樂,那歌詞其實就是字的運用。」
一旁李焯雄正認真手寫筆記,「我為了這次專訪還翻出之前的會議紀錄,其實我們過程中一直沒有忘記漢字這個東西,但順序上把它放在故事的最後面,先不要嚇跑你。」他明白越是深硬的東西,越要用不著痕跡的方式送入大眾腦袋。
「我們不會有板子跟你講字的起源、構成,但會讓你不知不覺地體驗到這些東西。深層來說,我們用流行歌詞,『反說』漢字的故事。比如說古人造字的時候,他們空間觀念是天圓地方。展場中有一區名為〈歌詞是永恆的現在進行式〉,以歌曲〈忽然之間〉為主題,如果你抬頭看,會發現頭頂是穹蒼,地面是方的空間,你會聽到從〈忽然之間〉延伸寫成的〈忽然之間,右先生〉的朗讀,時態回到 921 大地震的當下,歷史是現在進行式,體驗巨變的來臨與重生。」
「忽然之間/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麼都沒有/⋯⋯/而現在/就算時針都停擺/就算生命像塵埃/分不開/我們也許反而更相信愛」——莫文蔚〈忽然之間〉,1999
〈忽然之間〉乍看像描寫愛情,事實上卻是李焯雄與周耀輝於 921 大地震後,有感寫下人心的脆弱。
「情感有重生,文字也有它的開始,這時候黑暗之中會有象形文字的光點影像出現,彷彿天地再生,聽起來應該會蠻好玩的吧(笑)。」張文玲補充,「總之,這還是歌詞的概念展,雖然喜歡中文字,但我們沒有那麼教條,還是以比較娛樂性、大眾性的方向在做,同時嘗試一些新的科技。」
眼前兩人雖在策展新手村相遇,但以流行音樂界而言,都已經是打怪無數的 S 級玩家。原想請他們聊聊自己在原領域如於得水的經驗,沒想到卻展開以下對話:
張:「其實⋯⋯,做演唱會,到現在都覺得很辛苦。」
李:「那文玲妳還會有不知道如何開始的時候嗎?」
張:「當然有,很焦慮啊。我都會問自己:欸妳做這麼多年了,怎麼還是好像什麼都不會一樣?」
李:「欸,其實我也會。每一次都像新的對不對?」
張:「對!所以想要透透氣做些不一樣的東西,就做了一個展覽⋯⋯。」
李:「結果發現是更大的坑⋯⋯。」
他們彼此發送焦慮的電波,而我深刻擔心起了兩人的睡眠品質。究竟對他們而言,流行音樂產業有哪些迷人的地方,讓他們即便一路滿是皺摺,也能擁有一路破關斬將的動力?
「我覺得就是做完一個作品、一場演唱會,看到觀眾是帶著微笑出去的。光是這樣,我就感覺可以一直一直在這個行業做下來。」張文玲說,和團隊一起努力,打造一個能讓來自四面八方的觀眾,同時沈浸、共振的空間,這讓她覺得自己對人類社會還有一點點貢獻;而李焯雄聽到共振的說法很有感,「其實不只是療癒、撫慰,有時只是瘋一下、玩一下、樂一下或思考一下,我在意的是人這件事。」他說,把人視為人,而非抽象的數字或點擊率時,就能認真地以同理心創作。
創作不求偉大,但求餘波盪漾。如此頻率相同的兩人要一起策展了,你準備好到場共振了嗎?
註 1|〈紅玫瑰〉、〈白玫瑰〉皆是李焯雄的填詞作品,概念取自張愛玲的短篇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兩首歌由陳奕迅分別以國語、粵語演唱,共享同樣的旋律。
註 2|「當我走在淒清的路上/天空正飄著濛濛細雨」出自齊豫〈走在雨中〉,1979;「追逐風追逐太陽」出自周華健〈心的方向〉,1994;「這個世界隨時都要崩塌」出自蔡健雅〈Beautiful Love〉,2007。
WeWORD 字我訂造:流行歌詞及其創造的 新媒體展
當歌詞不只是歌詞,一場華語流行歌詞的沈浸式體驗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