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然現實足夠強烈,為何我們還需要詩?鴻鴻談安哲羅普洛斯的詩意風景
編按:適逢法國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逝世百年、希臘導演狄奧安哲羅普洛斯逝世十年,2022 臺北文學.閱影展以兩位藝術先鋒的主題電影交叉選片。兩位藝術家在處理「時間」上各有一套: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以大量意識流文字,為記憶賦形;安哲羅普洛斯也見異曲同工之妙,藉由詩意長鏡頭,將完整的人物情態再現於膠卷上。時間被他們給物質化。
本篇文章摘擷系列講座〈亂世裡的詩意: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旅程〉,由詩人、導演鴻鴻主講,剖視安哲羅普洛斯眼中的霧與希臘,展開一段關於漂泊、尋鄉、長鏡頭的討論,亦回盼他的電影拍攝之旅。
(內文以鴻鴻第一人稱口述撰稿)
漂泊,追尋,返鄉的不能
年輕的時候,我對安哲羅普洛斯在敘事外散發出某種詩意的影像非常著迷。詩意用文字打開開關很容易,但用電影滿困難的,因為電影就是以現實來溝通現實的產物,你不可能拍抽象的椅子,拍抽象的背影,非得是真實存在的某一張椅子、某一個背影,以現實為媒介時,詩意要迸發出來,就必須依賴邏輯推演之間的留白或落差——這方面安哲羅普洛斯是高手。他每個場景、每個片段,都存在著故事之外的感動。
他的每一部電影都蘊含歷史背景、真實事件,但永遠是用象徵的方式在處理,比如《流浪藝人》講述一個劇團在希臘巡迴演出,演出的《牧羊女高爾芙》正好反映當時政治狀況,那齣電影裡的戲從來沒有演完過,都是被現實因素給打斷。

《流浪藝人》(1975)
希臘史跟任何巴爾幹半島的國家都一樣,非常複雜,所以看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時,要還原其發生背景相當困難,那就很像我們看《悲情城市》,聽得懂角色現在是講上海話、日語、潮州話、國語⋯⋯但不懂中文的外國人全都得看字幕,會被混淆成同一種語言,就很難了解裡面的族群問題。我們看安哲羅普洛斯多少是這狀況,但還是能欣賞那些被安哲羅普洛斯提煉成藝術的視覺產物,他讓它變成一種具有普世性、永續性的主題。
這個主題首先是追尋,為什麼要追尋呢?因為追尋反映出事物的缺失:家沒有了、故鄉沒有了、文化沒有了,所以要去追尋。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往往發生在旅程:一旦開始追尋,就會處於漂泊的狀態。漂泊跟追尋是一體兩面的。
他最棒的意象都跟漂泊有關,比如《塞瑟島之旅》的老政治革命家,在蘇聯住了 32 年,回家時卻又被自己的家鄉驅逐出境,革命家只好跟他老婆在公海一個浮木上過夜,哪裡都不屬於的地方,竟變成他們的安身之地。那個意象非常荒涼、非常殘酷,但是又非常地美,你可以感受到那種人沒有地方、無家可歸的感覺。這完全是政治造成的。

《塞瑟島之旅》(1984)
《鸛鳥踟躕》也有兩個人隔著一條河舉行婚禮,那條河就是希臘跟土耳其的邊界。現實阻斷了他們的結合,他們只能在意念上構築一個家。或《霧中風景》有穿著黃雨衣的人掛在電線桿上面修電線,鳥棲在枝頭上,而人不是鳥,應該要下來,但他們下不來。
《尤里西斯生命之旅》也是,講一個導演去美國 35 年回後到家鄉,追尋一世紀以前的三卷默片膠卷。他電影裡常見這些返鄉跟追尋,如果熟知希臘文學的人馬上能聯想到《奧德賽》。尤里西斯是《奧德賽》的男主角,他返鄉時,得罪了海神,被迫在海上漂流十年。回到家後,尤里西斯發現老婆快被別人追走了,一大堆求婚者在他原本的房子裡,老婆不認識他、兒子也不認識他,就這樣變成異鄉人。
一間公廁的奇喻
漂泊跟安哲羅普洛斯的個人經歷有關嗎?他說他 18 歲前沒有離開過雅典,24 歲才去法國唸電影。他年少時在雅典電影院看《斷了氣》,被藝術的靈光啟發,去法國並考到法國高等電影學院(IDHEC),卻跟教授吵架,被退學。趁《尤里西斯生命之旅》放映,安哲羅普洛斯回到巴黎,曾經的同學、老師來找他聊天,但那些沒有被退學的同學裡頭,沒有一個在拍電影。
安哲羅普洛斯被退學後,還是在巴黎繼續混,1959 到 1968 年間剛好巴黎發生好幾場學生運動,加上文化的薰陶,帶給安哲羅普洛斯非常多養分跟刺激,慢慢找到自己電影的主題,選擇用藝術方式回顧希臘近代史。
我們熟悉的希臘其實是 2500 年前的希臘,有那些亂七八糟的諸神史詩、悲劇、哲學、詩學、數學、民族還有運動,但其實那時的希臘沒有維持很久,很快就被羅馬幹掉,後來羅馬變成拜占庭帝國,到 15 世紀又分裂成鄂圖曼帝國,整個希臘人種都被洗過一遍。因此,今天的希臘人跟當年創造輝煌神話的希臘人,已經不是同一批人,可是現在希臘人卻必須繼承當時的文化,遊客來希臘還是要看這些東西,你們不覺得有點尷尬嗎?
大家來看你祖先的東西,但那不見得是你真正的祖先,你還必須做一個稱職的博物館管理員,看管這些史料,甚至發揚光大?每年夏天,希臘露天劇場都還是在演希臘悲劇,人人都覺得很正宗,但這哪裡是正宗?
正宗早就消失了。安哲羅普洛斯不是站在「希臘本位主義」,而是「巴爾幹本位主義」,他把希臘視作巴爾幹半島文化的一部分,包括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尤里西斯生命之旅》是安哲羅普洛斯對這塊土地的巡禮,在整個半島走一遍,旅途中的遭遇都有所象徵,觀影時必須聯繫到這個民族、城市、國家的文史脈絡,才真正知道他在講什麼。台灣人看他的電影也會有些感觸,會覺得,台灣好像比希臘好一點點,但很多處境都很類似:外來者闖入後所留下的,變成我們的文化資產。

《鸛鳥踟躕》(1991)
波士尼亞民主廣場上有一間公共廁所,不管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伊斯蘭教徒,都膜拜那間公廁。原來那間公廁,最初是東正教的禮拜堂,但被土耳其佔領後變清真寺,奧地利人來的時候再變天主教教堂。後來狄托統治南斯拉夫,實行共產主義、無神論,下令全部毀掉,改建成公共廁所——但對信徒來說,那依然是教堂啊。
這間公廁就是巴爾幹半島的縮影,也是安哲羅普洛斯電影的手法。你會看到他在提煉意象、賦予意涵時,試圖讓每一個意象都有複雜的指涉,跟歷史、文化、宗教息息相關。
後設:關於他與高達
高達跟安哲羅普洛斯很不一樣,一個把所有影像都剪成碎片,一個把鏡頭都拍得很長,《鸛鳥踟躕》有個畫面是拍停在鐵軌上、在避難亭的火車,用一個超級長的推軌鏡頭,一路推一路推,就會看到每一扇車窗都是不同族群的難民。那鏡頭我覺得跟高達的《週末》好像,拍巴黎人週末外出度假,都在路上塞車。
高達帶給安哲羅普洛斯的薰陶是精神層面的,他們的電影都有後設意味。安哲羅普洛斯的主角經常是影像工作者,或是故事跟拍攝與放映相關,《尤里西斯生命之旅》在追尋失蹤膠卷,《霧中風景》也有小孩撿到空白底片端詳,《養蜂人》裡養蜂人跟少年在一座空白的電影院裡,發生一場不成功的性愛。當年訪談中我問「你是一個講故事的人,為什麼要一直提醒大家在看電影?」安哲羅普洛斯答,他覺得電影是一個即將要消失的行業,希望把這個行業跟媒介留下來,就像角色在空白的螢幕前不斷呼喊:我是一個不想消失的鬼魂。

《尤里西斯生命之旅》(1995)
.png)
《尤里西斯生命之旅》(1995)
《尤里西斯生命之旅》的導演終於找到膠卷,並沖洗,他就跟放映師一起散步到廣場上。一片大霧當中,能看到劇團在廢墟裡演《羅密歐與茱麗葉》。這個畫面非常像蘇珊桑塔格曾跑去被轟炸的塞拉耶佛導演《等待果陀》,他們都試圖在廢墟中重建文化傳統,安哲羅普洛斯藉由表演來完成這件事,不斷彰顯著表演跟現實的關係。
長鏡頭,一場詩的儀式
安哲羅普洛斯的長鏡頭美學非常奇妙跟有趣,不是一般的長鏡頭。
通常長鏡頭的功能是留住現實的空間,留住完整的表演,比如伍迪艾倫說他喜歡一場戲拍到底,因為他不想打斷演員的表演;塔可夫斯基的長鏡頭也非常有名,為的是留住時間跟空間的呼吸。可是安哲羅普洛斯長鏡頭不是這樣,他的長鏡頭設計感非常強,他的長鏡頭會 360 度在動。

安哲羅普洛斯經常在片場抽菸。據聞他在法國高等電影學院(IDHEC)就讀期間,時常遲到,還會在上課時與同學借菸抽。
有些導演的長鏡頭很少動、緊跟演員,可是安哲羅普洛斯不然,他的長鏡頭有自己的觀點,採取某個制高點的觀賞位置,所有的場面調度精密地被安排,所以他的鏡頭可能會推、可能會拉、可能會移動、可能會旋轉,他把這些看似隨機、其實經過精心安排的人物動態,經由他的鏡頭完整地聚集起來,變成一場儀式。所以觀看他的電影時,經常能意識到鏡頭的存在。
比如《霧中風景》出名的強暴戲,是姊姊被拉進卡車,但卡車被篷子蓋住,鏡頭就往被蓋住的地方一直推,觀眾跟鏡頭一樣,都想要探究卡車裡發生的事情,但是你看不到。後來小女孩出來了,身上流著血出來了,觀眾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鏡頭帶著我們往前走,不管看得見看不見,你會知道,你跟鏡頭在一起,鏡頭帶著你一起看事情發生,從目光的移動、構圖的改變,都是高度自覺性的,我覺得這種做法一方面很後設,讓觀眾意識到鏡頭的存在,另一方面他試圖把這一切都儀式化、表演化、凝結起來,像是在一張動態的相片中,把這些東西給聚焦、留存下來。
《塞瑟島之旅》裡主角在應徵演員時,被闖入的賣花老人吸引注意,老人把他從片場帶到真實的希臘街頭,最後老人消失,留下主角在他本該出現的地方,觀眾才知道老人是他心裡追尋的父親形象。照理講這老人是虛幻的:詩意就是從這誕生。電影裡不可能拍一個抽象的老人、抽象的思念,但是在邏輯斷錯的地方,可以讓詩意出來。
如果現實本身就夠清楚,為什麼還需要詩意?安哲羅普洛斯讓我們看到,用音樂的進出,鏡頭的調度,隨時跟觀眾調整距離,有時候把我們帶進去,有時候推出來——鏡頭遠一點,根本看不清楚時,反而讓我們有了宏觀,更感同身受——這是劇場化的,表演性更強、設計感更強,像你讀一首詩,會被韻律感給帶領,而不只是文字內容。
來自觀察者的眼睛
以前看片子都是小螢幕,常常搞不清楚安哲羅普洛斯電影裡誰是誰,跟侯導的電影有點像,鏡頭擺得太遠了,不知道是誰講話,或是知道有人在講話、但不明白他們的情緒跟狀態。他們都採取了一個遠觀的、統觀的視角,讓觀眾掌握整體的情境跟脈絡。電影裡,演員們少有表情,觀眾不知道角色感受了什麼。角色站在外圍觀察世界,這讓觀眾從敘事邏輯中得到自己的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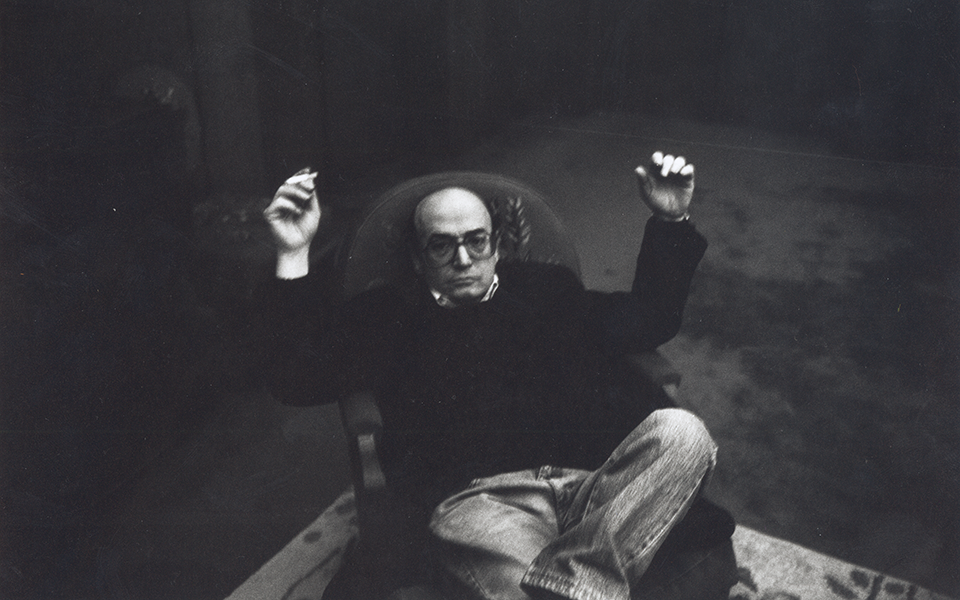
不過《霧中風景》算是例外。描述一對姊弟要去德國找爸爸,說,過了這個山壁就是德國——故事有點想像成分在,事實上希臘跟德國並不接壤——這些現實的事物,都被雪、雕像掩蓋,這是童話式的切法,但童話下是很殘酷的:霧中風景最後,姊弟在霧中奔向一棵樹,他們就在霧中抱著一棵樹,好像那棵樹就是德國、就是父親。
劇本原來不是這版結尾,安哲羅普洛斯希望姊弟倆消失在茫茫大霧當中。但拍攝時,他七歲的女兒看劇本哭了:「德國在哪裡、爸爸在哪裡、樹在哪裡?」安哲羅普洛斯不忍女兒傷心就把結局改成兩個人抱著樹。我覺得他女兒是對的,這結尾非常難忘:雖然得到救贖,但救贖是假的。那不是父親、那不是德國,卻有視覺的意象出現,讓結尾更複雜。觀眾知道是虛幻的,但也同時得到撫慰。這是電影最迷人的地方:你可以同時得到兩者,你的理性跟感性可以同時運作。
安哲羅普洛斯不是煽情、耽溺的導演,《霧中風景》姊弟剛剛跑出警察局時,一個女人坐在那邊,像瘋了一樣一直在說「繩子從脖子上滑掉了」,在講一個自殺、上吊死亡的狀態,這個電影沒有呈現瘋女人的故事,但她好像就被困在那裡,出不去;那對姊弟逃走,但安哲羅普洛斯不會那麼天真地讓他們跑掉,而是擺設一個瘋子在那邊,做出對比。真正的詩意不只是浪漫跟甜美,而是甜美跟殘酷現實的內在拉鋸。
安哲羅普洛斯透過感受去呈現世界。這也是詩跟小說的不同,小說把世界寫出來,讓讀者自己去感受;詩則是通過內在呈現世界。

《霧中風景》(1988)
2022 臺北文學.閱影展
時間|2022.05.27(Fri.)-06.09(Thu.)
節目介紹|https://literature.festival.taipei/film-festival.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