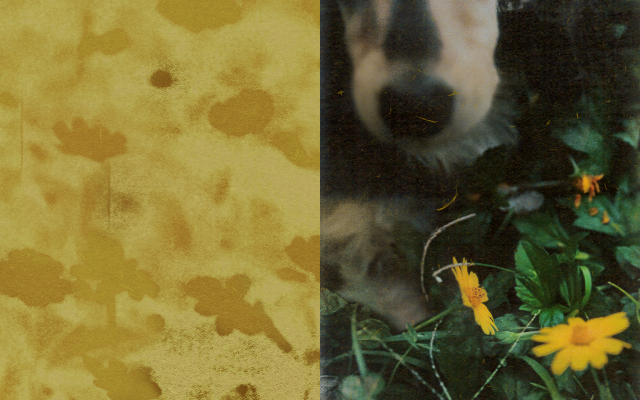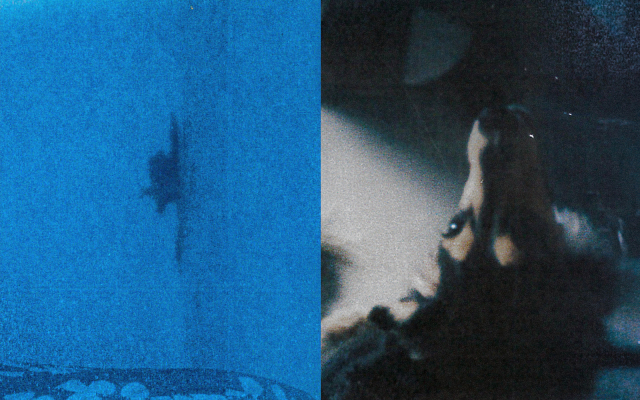長江燒不完這餘燼|我只是在等待夏天
黑暗中,一條荒蕪的走道。我聞到雨水的氣味,我聞到動物的氣味,空氣中蒼茫又濕黏,彷彿空氣的盡頭既是生命,又欠缺生命。我在黑暗中遇到了與我同樣在這條荒蕪道路上,不斷尋求真理的人。但我不會因此而停下。
我會繼續走,一直走,直到我看到城市燃起一把熊熊烈火。
水龍頭疑似沒關好,時間是半夜四點,我一直焦慮於浴室間歇性的水聲。上海已經變暖了,夏天快要來。前幾天曾有一夜大雨,大到好像要把整個城市沖刷掉。這與我無關,雖然我生活在上海,但這些風啊雨的,已經從許久之前開始,我就明白對我現階段的生命起不了什麼作用。
黑暗中,我十分清醒。現在到底幾點呢?我一邊想,一邊想到白天生活發生的種種事。確實是發生在我身上的沒錯,但同時,卻又好像發生在別人身上。
男友做惡夢,在我身旁突然醒來,有點迷茫的喃喃自語:「現在他們又把我們丟到什麼地方啦⋯⋯?」他像一盞若隱若現的燭火,在永恆無盡的夜裡幾乎無法抗衡地丟出一瞬火光。在此之後,他將繼續回去睡眠,我繼續失眠。被丟到什麼地方?是啊,所以現在這是什麼地方?所以⋯⋯我感傷的親親,我甜蜜的、無法拯救我孤寂而反在睡夢被拋棄了的可憐人兒——你也覺得我們不斷被丟到其他地方嗎?
我突然想到一些零碎畫面,以及某些對話,像冷靜的流水一樣流過我眼前。靜安寺晚上炫耀自己富麗堂皇的金色,橫山路酒吧街週末熙熙攘攘著笑鬧的外國人,很久沒記憶確切長什麼樣子的月光,以及隱沒在黑暗中,沉默的樹。

我想到我剛來上海時,去了一次 Shelter。十分失望。那是一間防空洞 live house,有時有現場表演,有時 DJ 來放電音。一進去,要通過碩大的防空洞。過了防空洞幽暗的走道,酒吧本身,裡面充斥著詭異的藍光。酒是絕對不能喝的,這間是出了名的假酒,但我看大家都已經醉了。於是人群晃動,有人彷彿中邪一般,舞著像原始部落祭司一樣的魔之亂舞。我站在牆邊,連點起一根菸的興致都無。
現在回想,當天可能酒喝太少了。
我還想到,我去過很多次 Speaklow,到底是為什麼?那絕對是一個與生命狂熱無關的無聊大師之起源之地。那是上海其中一間有名的 speakeasy bar,在上海是個風潮,外國人尤其愛。要進酒吧,必須先找到入口,因為它如魔術一般很神奇地藏在看似不起眼的書櫃後面。大家通常又驚又喜地找到門之後,會通過一條⋯⋯算了,我懶得多描述,總之很安靜,酒不錯,酒保與老闆是日本人因此對酒很講究,入口也是個小魔術,大家都很愛,很好。我痛恨自己去過很多次。
上海就是,大家都著一身名牌,華麗地一起被名為「生活」的婊子耍著玩。週末夜時,這種感覺特別明顯。
前一陣子某天,我隨便吃了晚餐,橫躺在床上跟朋友傳訊息。朋友說,他正躺在靜安寺旁邊的公園草地,抽著菸,等人把他帶走。我知道他意思是想要我把他帶走。因為我就住在靜安寺附近,以及,我知道他想要我把他帶走很久了。
我:「你回家吧白痴。其實我感冒還沒好,感覺累累的,在思考等下到底要不要出門。」
他:「你怎麼又感冒了?」
接著他說:「夏天都來了。」
啊,夏天都來了。
不必管我在想什麼,也不用關心今日的月亮是否和回憶中一樣鋪著大地,就這樣吧
我只是在等待夏天。
【長江燒不完這餘燼】
關於上海,有時關於倫敦,但其實多數我只想寫台北。
那些小公園裡閃閃爍爍像是童年被你丟在身後的陽光、夏日燙了發亮的水泥路、半夜咖啡館裡溫暖繚繞的香煙與蒼白殘破不堪牆面,還有吉他聲堆起的音牆,比永恆還早一步佔據了我。在每一個城市的時候,我想的都是台北。
好啦但這專欄還是關於上海。
【廖乙臻】
曾任報紙與電視記者,後赴英國 UCL 攻讀碩士。在倫敦經歷一場火災把所有資產都燒成灰燼包括一個剛買的限量 Prada 包,組織過一場革命叫別人在冰天雪地中躺著為了體現行為藝術,現在上海工作。
追求自由,真正的自由。追求無懼,無所畏懼。其餘的,只是在對存在的質疑與對未來蒼茫的仰望中,
期待面朝大海,春暖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