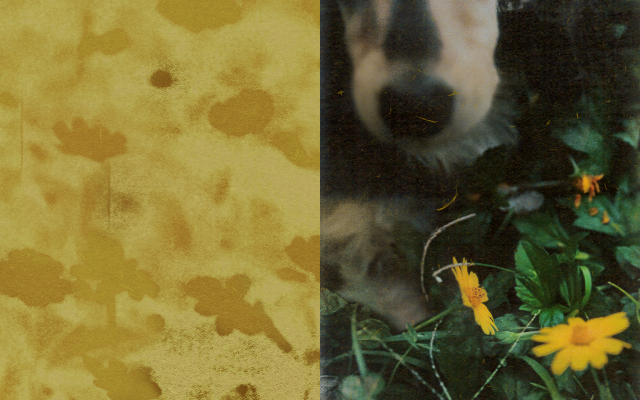語際上的小丑──談《大尾鱸鰻2》的歧視爭議
前一陣子臉書上流傳著《少林足球》台灣華語版被剪掉的畫面。這短片中濃妝豔抹的阿梅在打工處因球員們調侃其誇大穿著打扮而終究發怒,這場糾紛又因為老闆娘到來的恥笑成為這一段歧視場景的轉捩點,進而促使阿梅對老板娘發飆,友人轉而支持阿梅個人裝扮的選擇,完全改寫了原本恥笑女性裝扮的文本。這一段不知為何在華語版被刪除的片段,來對比《大尾鱸鰻2》的爭議,是再好不過了。諷刺語言的生成係透過挑動既有的語言遊戲規則,而幽默始於語言使用產生不同調的效果(incongruity),在一般語言使用上怎樣地笑,有其多種面貌難混為一談,恥笑與幽默自然有著極大的差異,把不把你當人看更有可能是文類邊界上的倫理問題。《少林足球》的例子在劇情中張開一道論述的方式,讓各種話語得以對話與反省,這是《大尾鱸鰻2》簡單挪用台灣抗議場景以為有其戲劇效果遠遠不及的。這裡的問題不是原創與否,而是什麼是小丑的原則。
小丑在戲劇作品中,無論是華語傳統戲中所稱「無醜不成戲」,或是 Jacques Lecoq 曾如此界定過小丑:「小丑只存在於扮演他的演員身上,我們全都自認為英俊而瀟灑,聰明又強壯,但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弱點,都有各自愚蠢又可笑的地方;當我們將它們表現出來,觀眾就會發笑。」在這一點上戲劇理論所服務的笑意從不混淆恥笑與幽默的差異,而如何處理恥笑的倫理問題,往往是藝術作品棘手的部分。盧卡奇在早期對於消遣小說曾經直指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渴求更易讀的文學消遣形式,並且考量讀者的狀態是其基本模式。通俗電影一般的內容也不脫這樣的思考。同時我們也都知道藝術作品與現實存在的斷裂性,而這樣的斷裂性是否就是讓電影場景中容忍恥笑的藉口呢?顯然一旦混淆了,作品本身就變成了藝術的遮羞布。

2011 年美國 UCLA 曾經發生過一件恥笑華人的新聞,當地白人使用了「ching chong ling long ting tong」作為恥笑華人學生的自我模仿。在這個例子上,正與《大尾鱸鰻2》這一次在台灣引起的爭議如出一轍,只不過後者發生於電影中。歧視語言大多時候並非只是一個詞語,而通常是一種文法規則、一種語用效用,一種社會上主客關係長期不均衡在話語中的再現。這是一個真實案例,但在藝術作品當中出現,只是單純要求一個道歉恐怕也無解於台灣電影屢犯的問題。更不用說《大尾鱸鰻2》還簡化了對台語片的理解,這些爭議體現的是台灣多種社會歧視的加成。通俗電影需要想像出觀眾,而觀眾在藝術消費品中得不到預期的超脫,這樣令人反感的問題或許也隱藏於(電影)藝術體制的生成結構。
賀歲片在台灣,作為一個檔期它就是新春期間上映電影的泛稱,但作為一種片別,它是從八〇年代在香港發展起來針對當地觀眾量身而制、可供新春期間放映的喜劇,是種電影體例(genre)。這樣的電影工業模式,在中國從 1997 年馮小剛開拍《甲方乙方》,形成香港對中國輸入的新體例。至於台灣,這幾年來對於「賀歲片」這樣的體例,顯然也是由電影工業推進的,例如 2010 年的《雞排英雄》,對於片商而言就是「台灣.人.情」訴求下所量身訂做。台灣目前電影研究尚未有太多對於「賀歲片」體例的思考與討論,我們也無法否認目前台灣的本土電影思考弔詭地在「華語」或說單一語種的大纛之下產生了諸多的倫理誤區,更不用說談起台灣電影工業再造,在這幾年常見的爭論之下,觀眾對於賀歲片不是沒有期待的,事實上反而是存在著濃厚的「民族工業」這樣的想法。那麼就此而論,賀歲片真的沒有認清觀眾組成與觀影經驗差異的責任嗎?戲劇中台語使用者的面貌被迫得接受台語凝縮為戲謔語言的功能,而原住民被排除在語言使用的它者如今業已發生,更不用說這個「賀歲」的新春假期在台灣多元族群環境下一直都顯得尷尬而諷刺。
戲劇理論中有一種小丑邏輯(clown logic)可以讓小丑裝作無知的狀態去新穎地看待世界,Louise Peacock 在《嚴肅戲劇:現代小丑表演》中將這種視角作為愚笨看待世界的方式得以將現實的樣貌呈現,類似於盧卡奇將小說視為一種生活乃至對生活超越的方式。也就是這種描述事實卻又可以忽略事實的態度讓近年來台灣一些搞笑片得以立足。但賀歲片如今是否仍然可以用過去課本上出現原住民都很窮之類的段落來辯護?又或者我們得問現在的台灣社會真的只是單純的華語單語種的構成嗎?這「多語的現實」與「戲劇作品面臨觀眾背景所擁有的現實」有差異嗎?站在語際上的小丑眼中的多種語言是否只有單一語種的溝通體系才有資格保有它的面貌,而其它語言就可以任意扭曲嗎?想起最近在看的日劇《直美與加奈子》(Naomi and Kanako),高畑淳子說起不差的中文所帶來的驚訝,這些問題該是演藝工業所肩負的責任吧。一如先前所言,賀歲片考慮到的新春時節與觀眾訴求,多種語際的問題透過台灣多語社會簡單化約進華語體系可以獲得解決嗎?或者更進一步問,台灣需要怎樣的「賀歲片」?

道歉是簡單的,但藝術事實上總是存有自身面對共同體的倫理,或是真實描寫的責任。電影可以重新搭建歧視的場景,但歧視的開展與效果也有高下。電影可以再製恥笑族群的可能,但你的觀眾如果就是其中一員,那單語種的思考可能就需要重估。一部以現實作為背景的作品如果連背景都難以重新再現,在創作層次上能有藉口嗎?隨著族裔問題爭論的發展,更進一步的是在工作權層次要求聘用原住民演員的責任,並使用正確語言來表述當前的政治現實。台灣演藝工業中的歧視結構未曾解決,一如社會對於原住民的長年剝削,那藝術機制內部是否也存在著不平等的狀況呢?去年台灣難得有部《太陽的孩子》,然而類似的原住民創作者相關問題目前仍在台灣各種語言教育與藝術中擱淺著。台灣電影中的小丑如何走在語際之間真正發揮劇場功效,藝術體制的不平等除了討論歧視,拉回藝術歸藝術時,也正是電影工業面對自身結構未曾面對族裔問題的時刻。
【專欄簡介】
藝術作品不會主動地揭開它的深刻,本專欄將提供台灣當代戲劇、視覺藝術展演的介紹與論述。由「關係藝術」的理論,這勢必帶著藝術作品與文學之間的認知差距,但也希望藉由這些差距,討論作品的文化脈絡及其美學觀點,提供讀者進一步的討論空間。
【印卡】
七年級詩人,《秘密讀者》編委,詩歌作品散見於《自由時報》、《字花》、《衛生紙》、《創世紀》等刊物,曾被收錄於合集《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著有詩集《Rorschach Inkb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