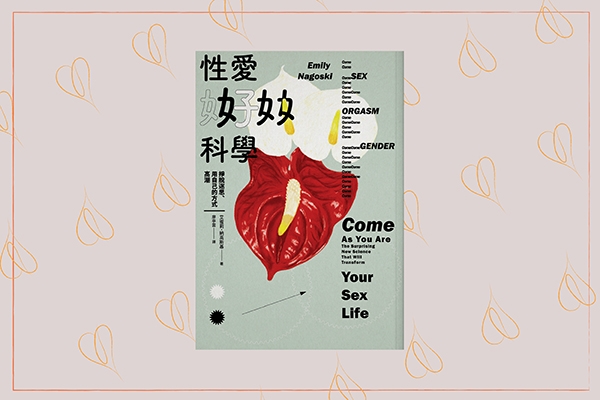背誦的身體哲學(三):
默會知識的觀點
在本專題的第一篇文章中,我們介紹了讀經教育的爭議中正反兩方的意見。在背誦的問題上,我們的看法是:以理解為基礎的背誦,是一種結合心靈與身體、理性與感性的學習方式。不過,第一篇文章並沒有正式論述這個立場,以下我們要展開討論。
這次專題的標題為「背誦的身體哲學」,顧名思義,我們希望能從「身體」出發,探討「背誦」的運作機制與意義。僅著眼於可言述的「命題知識」的立場,會認為可用翻譯取代原文,只須理解不必背誦,但我們認為「身體」蘊含了語言無法轉譯,但卻確實形構語言意義的層面。因此,在從語言通往意義的過程中,起著作用的不只有邏輯思維,還有一個隱默的身體維度。
默會知識與兩種意識
邁可.博藍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是著名的猶太裔哲學家,1958 年他提出了「默會知識」這個術語,以及一個重要的命題:「我們所理解的多於我們所能說的」,認為我們所擁有的知識未必都能訴諸言說。
近代以來,分析哲學以「知道的東西一定能夠說出來」為立場,惟「命題知識」之為聽,認為知識是理性對於認知對象的「表徵」(representation),因而所有的知識都可以用概念、命題形諸言述。
博藍尼的「默會知識」所要反對的正是這一種立場。對於「我們所理解的多於我們所能說的」這個命題,他提供了不少的案例,其中最經典也最完整的表述要屬「用鐵錘捶打釘子」的例子。
簡單來說,在我們關於「用鐵捶捶打釘子」這項知識的實踐中,包含著兩種意識:一個是我們把注意力鎖定在釘子上的「焦點意識」,另一個是我們整合骨骼、肌肉、筋膜、神經等複雜生理機制的「支援意識」,好讓我們可以執行一手拿釘子,一手揮動捶子的動作。如果沒有支援意識的存在,我們的焦點意識就無法順利執行,例如會造成揮動鐵錘卻敲到手指,或是無法固定釘子導致鐵錘揮空等情況。博藍尼因此提出,人類的知識是以「支援意識」為背景,以「焦點意識」為前景的「默會知識」。

其實,類似的例子也發生在我們的日常中。就像我們可以說出騎腳踏車的一般性規則──腳踩踏板,雙手控制方向,身體保持平衡,但是任何人都無法僅僅依照這樣的「言述知識」便立刻學會了騎腳踏車。又像開車,究竟轉彎時方向盤要打幾圈?路邊停車時什麼時候該打方向盤切進空位?又如同從頭學習一種語言,就算我們掌握了聲韻系統以及發音原則,但總是有一種「口氣」不到位的感覺。
這些經驗都顯示了這樣一個事實:知識無法僅靠指導手冊的說明就傳授或習得,因為所有的知識都是「默會知識」,其中有無法言述的支援意識,它們以隱沒的形態內在於我們的身體記憶之中,這正是博藍尼之所以說「我們所理解的多於我們所能說的」的原因。
知識,寓居於身體
博藍尼特別強調「默會知識」中的「身體」因素。不難發現,以上所舉的例子都需要身體的參與,所以「默會知識」的形成總伴隨著身體的存在。這說明了知識的習得需要我們同時帶著心靈與身體介入,而不是僅僅用理性映照客觀知識的內容,因此他又提出了一個命題:「通過寓居而認知」(Knowing by indwelling)。
我們可以設想這樣的情境:當一位盲人掌握了使用「手杖」的知識以後,他就能夠以手杖碰觸事物的震動,透過肌肉的接觸與神經系統的傳導,形成對於世界的認識。在此,盲人將自我寄託在手杖之中,寓居其間,手杖因此不再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物,而是盲人身體的一部分,而因為寓居於手杖之中,他的世界變得和一個摸黑行走、顛簸碰撞的世界不再相同──因為他認知世界的「身體」已經不再相同了。
.jpg)
從另一面來說,一旦我們健全的身體因為疾病而損傷時,身體的不便將鮮明地形成許多知識與技能的障礙,此時我們會驚覺日常對於肢體的寄託之深刻。試著回憶你落枕的經驗,生活起居會有多大的改變,你會發現日常許多技能與知識的運作,竟如此深刻地寓居於身體。又如依賴手機生活的你,一旦手機故障或是遺失,會不會突然覺得自己少了一隻手,甚至世界開始變得陌生?這都證明了,當工具或技能內化為我們身體的延伸時,它們便成為我們認知事物的「支援意識」。
因此,博藍尼說:「默會認知的任何一種行動,都改變我們的生存狀態,重新定向和收緊我們介入世界的活動。」藉由身體的「寓居」,我們將知識對象、工具「內化」為身體的一部分,成為我們身體的延長與變形。每一次寄託於新的知識之中,我們面對世界、認識世界、接觸世界的方式就不會再與從前相同;每一次的默會認知,都是我們自身的變形,同時也帶來世界的更新。
語言的隱默向度
說到這裡,一定會有人質疑,上述的例子都是屬於技藝或是操作技巧,這和語言與思考還是有差別的。所以,如果「我們所理解的多於我們所能說的」這句話可以成立,博藍尼就必須說明:即使是以邏輯見長的語言,同樣也是一種默會知識;也就是說:他必須說明「使用語言說話、表達、思考」也是一種技藝。
我們不妨思考一下「詞語」與「詞語的運用」之間的差異。儘管我們可以說明某個詞彙或句子的意涵,但我們卻很難直接說清楚某個人說某句話究竟想「表達」什麼,因為語言的運用要參考的因素不僅是詞彙的概念和語句的命題,同時還要整合情境、人物性格、知識背景、彼此的共同經驗、傳統等許許多多因素,這樣才能決定自己的心意該用什麼樣的語句表達。
同樣一句話,在不同的場合、被不同的人說出來,可能會有不太一樣的意思;相同概念或命題的語言,用不同詞彙的排列組合、選擇不同的語句順序表達,也可能會產生不太一樣的效果。這說明語言不只是概念與邏輯,其中還具有一種與「身體技藝」相同的層面。
通常,我們會稱這樣的整合能力為「說話的藝術」,如果我們認為說話的藝術是重要的,那是因為我們知道決定語言的意思的因素不只是概念本身。說話就是一種「技藝」,而沒有人可以依靠說明書就成為說話的高手;語言這項技藝,就如同騎腳踏車的技藝一樣,需要學習者的實作,以「默會致知」的方式將其內化。
.jpg)
概念、命題並不比身體優先。博藍尼告訴我們,默會知識具有優先性,只要把人跟動物相比,這個事實就會被凸顯出來。所有動物賴以為生的知識,都是無法被言述的默會知識,而人類因為握有使用語言的能力,因此在智力和文化水平上高於動物。表面上看來,人類因為語言而大量產生的「言述知識」似乎蓋過了「默會知識」的重要性;然而,我們對於語言能力的掌握,其實是隨著年齡、生活經驗、與人互動以及求知的過程中不斷精進、擴大與變化的。
就如同一位初生的嬰兒並不懂得運用語言進行思考與表達,他與世界最直接的接觸點是他雙眼、耳朵、鼻子、嘴巴與四肢,他對世界的知識源自於身體的默會。而後,當他開始懂得使用語言、運用符號,他原本用身體學到關於世界的知識,便與語言這個新的工具帶來的新知識交融在一起。所以,語言對於人類來說,同樣也是一種知識的「身體化」,人類運用語言,就像運用自己的身體一樣,總有我們自己無法轉譯的規則。
人類語言知識的從無到有,從肢體動作到語言符號的過程中,我們的「理解力」始終在作用著,而語言與身體一樣,都是被「理解力」內化的「工具」。所以,如果我們內化了語言這項技藝,我們就擁有一個語言化的身體,以及身體化的語言;我們運用語言思考、認識世界,那麼我們就寓居於語言之中形構我們的世界。
背誦與默會知識
語言的用字遣詞、聲腔、節律、言述策略等修辭意識,正是語言技藝的大觀。學習一種語言技藝,就是將這些語言因素內化為我們思考、表達的器官。學習語言技藝,我們通常會認為「潛移默化」是最自然的方式,但是背誦也有它存在的意義。
嚴格來說,潛移默化當中也有「記憶」的存在。事實上,我們在日常中是透過反覆操作、調整、精進的語言實踐,以及各種新的與舊的經驗相互摩擦、嵌入、配合,才掌握了日常語言的技藝。此時,「記憶」自然而然地發生,而非透過明顯而直接的外力驅使,但潛移默化的「記憶」仍發生在身體之中,所以我們才能將語言「技藝」內化。
潛移默化的背景通常是日常生活,口語的表達方式雖然自然,但人類的思維與意念畢竟不止於此。我們還有更多日常以外的時刻,需要挖掘心靈的暗角,我們有時需要理解世界中難以言喻、超乎邏輯但卻迷人或者傷人的時刻,那些人與人之間的摩盪、交接之際,幽微而不可言說的種種,那些關於人生雖不可測但你總渴望追求的問題,並不是日常生活的語言技藝可以捕捉與處理的。
.jpg)
日常語言無法言述,但是透過文學語言,我們得以追求。龍應台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為什麼需要文學?了解文學、接近文學,對我們形成價值判斷有什麼關係?如果說,文學有一百種所謂『功能』,而我必須選擇一種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個很精確的說法,macht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在我自己的體認中,這就是文學跟藝術最重要、最實質、最核心的一個作用。」
如果文學可以使許多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那麼將這種語言技藝內化、記憶,使其中的思維方式、節律美感、布局策略成為我們思想的器官,裝備我們觀看世界、接觸世界的身體,我們將會看見許多日常語言看不見的風景。因為,我們熟練了「什麼樣」的語言,我們就寓居於「什麼樣」的世界。
「背誦」,是為了熟悉一種與日常語言有所差異的語言工具,就如同盲人掌握了手杖、長輩接觸了智慧型手機,對他們而言,「世界」都不再是從前那個樣子,而認知的方式也因為裝備了不同的「肢體」,而有了轉化。
「背誦」,就如同當初你學習揮動捶子卻不免受傷,你試著滑水踢腿在泳池中嗆水浮沈,而那些陌生的語言就如同無法被歸類、定義的物體,橫在我們面前而難以入嚥。一旦學會以後,那些規則、指引都化為無形,透明如空氣,而你終於得以釘下釘子,自在泅泳,在語言中認知、內省與想像。這就是在我們重探「背誦」的意義時,可以在博藍尼的「默會知識」理論中得到的啟示。
以上我們通過博藍尼之眼,重探了「背誦」的意義,也點出了基於「命題知識」的立場,對原文做出翻譯所將犧牲的東西。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們將從詩人羅毓嘉的創作經驗,談背誦中的身體,以及身體中的語言。
參考資料
1|Michael Polanyi 著,許澤民譯:《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台北:商周出版,2004 年。
2|Michael Polanyi、Harry Prosch 著,彭淮棟譯:《意義》,台北:聯經出版,1984 年。
3|Michael Polanyi 著,彭淮棟譯:《博藍尼演講集》,台北:聯經出版,1985 年。
4|郁振華:《人類知識的默會維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龍應台:《百年思索.自序》,台北:時報文化,199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