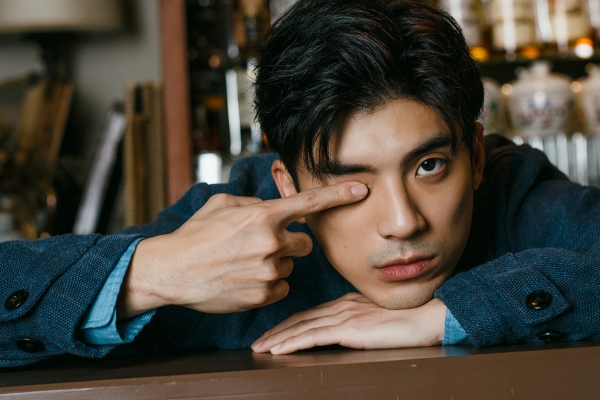天蠍男孩們的靈能對談:王可元 ╳ 范少勳,演員經驗的神祕性
早早妝髮完成的王可元,窩在攝影棚一角,對著樹木希林的《離開時,以我喜歡的樣子》做筆記,安穩寧靜,像老早就種在那裡一棵根深的樹。范少勳推開門,對在場人員嗨聲連發、一一握手,於是現場除了有樹,也有了陽光。
這兩年,對兩位演員來說無疑是重要的。王可元演《我們與惡的距離》,以殺人犯李曉明為觀眾所知,《陽光普照》、《軍犬》表演奪人目光,又以《情色小說》入圍台北電影獎最佳新演員獎;范少勳演《越界》,讓夏邱 CP 至今仍令觀眾深陷,《樂獄》打戲精準有力,並以《下半場》入圍金馬獎最佳新演員獎。

不完美,不擔心
做演員,王可元與范少勳都是半路出家,一路上嘗試的東西很多,演戲卻在他們的人生標記了一個定錨點,要常駐下來一探究竟。入圍新演員,像嬰兒初生到學會爬步的過程被肯認,更像是確認了自己能被讀懂。
以慎重寫完一份考卷的心意,范少勳拿入圍當認真讀書後的小確幸,說之後還是要繼續用功啊。「我剛開始喜歡表演,只是因為叛逆,不想做機械化的事情,演戲就沒有所謂公式,每種情緒都有不同路徑,是無法重複的。」沒料到後來,越演越上癮,「我決定要當演員時,心裡吶喊『嗯!我想要成為一位有影響力的演員(握拳)』,現在會覺得,經過《越界》、《樂獄》、《下半場》,離這個想法好像越來越近了。」他眼神發光如置身熱血少年漫畫。
他口中的影響力,是觀眾投入在電影裡與角色走過一遭後,在現實生活中激發出一些改變。「會有人跑來跟我說,看完《樂獄》他終於有了換工作的勇氣;《下半場》映後,也有身體不健全的小朋友說,他喜歡打籃球,如果有那麼一絲絲做夢的機會,他不會放棄,我們很多人都哭了。」一旁王可元猛力點頭,出道以來,他演同志按摩師、小兒麻痹的作家、殺人犯、少年監獄受刑人,透過這些非傳統框架認同的角色,他得到作為演員的認同。

王可元說,演員是極為脆弱與缺乏安全感的職業,唯有不斷確認自己在做的事是有價值的,他也才能演下去。
「我的角色都充滿不完美或瑕疵,因此我對帶給別人勇氣跟力量這點也很有體會。我常收到大家的訊息是『謝謝你讓我看到不一樣的人生』、『謝謝你讓我知道人生是有希望的』,這些都是讓我願意繼續做這麼痛苦的事、嘗試不一樣角色的力量。」
剛出道時,王可元常因長相被打槍,被說路人臉,但現在他已經學會從外至內,接受所有。他提及自己臉上那些,常在工作中強制「被完美」的瑕疵,「我臉上的痣、斑、眼袋都被修掉,這什麼意思啊?」如果說能發揮演員的影響力,他希望這社會能出現另一種審美觀,人都不完美,有什麼好擔心的?
演員的起乩儀式
新演員,顧名思義入行不久,一切都是新鮮的嘗試。對於如何讓自己進入演戲的狀況,王可元當然曾有過擔心,「比如說接到一些哭戲,我心裡會想說,幹如果哭不出來怎麼辦?但真正工作之後發現,當下其實不需要去想,你在那個情境裡時,全世界都會幫著你。」眼藥水就丟了吧,拍電影是團隊的事,對手演員對了、場景對了、氛圍對了⋯⋯,眼淚就掉下來了。

.jpg)
范少勳回憶《下半場》的拍攝過程,也同意王可元的說法:「現場劇組把環境塑造得非常好,只要專注在那個情境帶給你什麼,感受它就好了。所以其實到後面,我感覺我真的輸了一場比賽,可是我卻獲得了一開始最想要的東西,我真的輸了嗎?好像也不一定。」演到後來最關鍵那場戲,在拍攝四天當中他經歷一場比賽的起落,甚至已經分不清那是自己還是姜秀宇。
讓情緒流動,順著感覺走,「我目前拍過的電影都是順拍,順拍很可怕,因為拍到後來你好像是在過角色一模一樣的生活,到後面有幾顆我自己都難以區分,到底是我真的經歷過,還是那是劇本裡的生活?」范少勳說完,王可元惺惺相惜:「那很珍貴!那你曾經有喊 cut 之後忘記自己剛剛在幹嘛嗎?」嗯?看來兩人都曾體會過某種宇宙的神秘力量。
范少勳申論起演員與乩童的相似性:「演員其實跟乩童很像,只是乩童會有很明顯的起乩、退駕標準儀式,但演員沒有。」於是找尋讓演員起乩的那把鑰匙就成了重要大事。兩人都習慣一拿到劇本,就方方面面開始過角色的生活。譬如范少勳為了《下半場》戴助聽器、耳朵塞黏土,王可元為《情色小說》嘗試以障礙的雙腳行走。
「定完裝,確定角色有哪些衣服、飾品,我就全部跟劇組拿來,自己開始過生活,殺青之後再一樣樣還回去。我習慣在開拍前幫角色找幾首歌、幾張照片,因為我相信進到一個新的生活狀態,你會有新的觀點、喜歡一些新的東西、對某些特定事物有感覺。」范少勳特別強調環境,於是他也會為戲搬家,「今天回到家,看到我的床、我的客廳,會不會感到放鬆,還是有點不知道自己可以幹嘛?這能讓我確定自己是不是活在狀態裡面。」

除了過角色的人生,兩人也會用嗅覺讓自己入戲。范少勳說自己剛拍完一個 GUCCI 味的角色,那段日子他每天噴 GUCCI 粉味香水;而王可元在《情色小說》裡的激烈情慾戲,也是靠氣味闖關,「導演給我跟采儀老師一個味道,在我們快承受不住、瀕臨崩潰的時候,那個氣味就會出現,那是幫助我們進出很大的關鍵。」他也習慣劃分角色性格冷暖,以木質、檀香、水果等各類芳香替角色搭配專屬氣味。
那李曉明呢,李曉明是什麼味道?「李曉明,他沒有味道,因為他跟大家的味道都一樣,每個人身上都有李曉明的味道。」每次上戲之前,王可元會閉上眼睛,用手慢慢觸摸四周空間,以身體感受環境,監獄的冰冷與空蕩。
黑洞裡外
如果不只是在鏡頭前,連在現實生活中都分不清自己/角色,那麼,當一個演員身邊的人會有多難?范少勳說,家人的包容程度真的不可思議,「比如拍《樂獄》那時候,我開始變得有點極端、強烈,我會自己剃頭髮,也變得不愛講話。」范少勳有家人的包容,而王可元已經習慣了一個人生活。
「我覺得演戲給我最大的禮物是,我學會怎麼跟自己相處。我不會再去遷就身邊的人,這個遷就也不是冒犯,只是我不會再犧牲自己的情緒去迎合任何人了。」他提到最近在做人類圖的薦骨練習,「針對問題要直接發出聲音,用『嗯嗯嗯嗯』來回答,不要透過大腦思考。」他往自己內心挖,思緒理不清的時候就看書、寫東西,總會寫出個脈絡。
獨居前輩因而訪問起了也曾為戲嘗試搬出來的范少勳,口氣如進行心理諮商:「我想聽你自己過生活,你的感受是什麼?」
「我覺得像是一個黑洞。獨處本身不是一個黑洞,可是你獨處、又在那個狀態裡的話,那就是一個黑洞。」
「對,很像黑洞,但我以為你會愛上獨處,因為我就是。後來我沒辦法再跟另外一個人住在一起,無論我多喜歡那個人,都需要跟自己相處。」

范少勳頓了一下說,「我們好像是不同流派的。我是大自然派,我滿相信很多快樂跟認知是透過分享而來,如果我本身是一個載體,我聽到你的故事、再分享出去,就是一個流動,而這個流動會帶給自己成長。」他說,就像大自然裡的水流或樹木,透過接收與給予的循環,能讓自己是個乾淨的狀態。
王可元躲在黑洞裡讀書寫字,消化自己;范少勳徒步環島,躲到沒有收訊的山上露營。演員的起乩與退駕,填裝與掏空,一次又一次以他們感到舒服的方式進行著。
母親:用演戲換回的禮物
演員不是一份能讓父母親馬上感到欣慰的工作,兩人成長過程中也都經歷與家人的拉扯,現在他們卻反而因為演戲學會同理,修復了與父母的關係。
「我一直不是在體制內的小孩。」范少勳出身運動世家,加入球隊顯得理所當然,「但我媽帶我就很辛苦,大家都刻板說,學運動的小孩都是壞小孩。」那年,他歷經轉學,三個班導師沒人願意收他,最資淺的那個最終不情不願,「老師來大門接我,第一句話就是:『喔,運動員,壞小孩。』這種話,唉,直接在我媽面前講。」范少勳不是壞小孩,只是讀書不是他的菜。出社會後,他工作換來換去,開過 Uber、當精品店保全,直到接觸表演才定下心來。
他經歷過一段埋怨父親的時光,性格強烈也曾讓媽媽很無奈,「我以前比較單一,個性很衝,就是火爆份子。但開始上表演課之後,透過分析劇本裡的潛台詞、人的動機或目的,就開始成長了。你會理解家人之間有說不出來的話,不知道怎麼表達,對爸爸媽媽也就有更多理解,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改變。」
拍攝《下半場》期間,范少勳有次摔斷了手。
「我馬麻有我手機定位,那天她就打來問我是在三總拍戲嗎?我說不出話來,愣了一下才說手斷掉了。我媽當下變得非常嚴肅,極冷,問我現在是怎樣?所以好了嗎?然後就掰掰,掛掉了。」電話掛掉那一刻,范少勳哭了,「要是我以前,一定會覺得,哇,我是妳兒子,我手受傷妳還用這種態度對我。可是那一刻我知道她的擔心,知道她語氣裡的痛,可是她說不出口。」表演訓練出的細膩,讓他轉變為會牽著媽媽逛 Costco 的大男孩,還不怕肉麻,一天到晚喊愛。
「以前媽媽牽著你的手去菜市場,你會覺得,天哪,不要這樣。或是生命中某些階段,你會希望媽媽不要來學校,覺得很丟臉。但現在會常常叫她來,就說,欸我有電影啊,妳要不要來看?像回到小時候一樣。」
王可元邊聽邊笑,說自己也經歷了一樣的轉變,現在他常窩在媽媽肩頭,動不動訊息查勤、看看媽媽有沒有亂跑。誰能想到這對母子關係曾經完全摧毀,整整一年時間,王可元避不見面,媽媽完全不知道他的行蹤,連到住處堵人都沒能見他一面。
「人家說運動員都是壞小孩,學音樂的都不會變壞?但我真的也沒乖到哪裡去。」從小被父母逼著學鋼琴、讀書,相較於范少勳直接待在體制外,他更像在體制邊界載浮載沉,一路遵從父母意志讀到研究所,回過頭來才發現都是一場空。

「我從小就活在他們的期待之中,我花了很多力氣,卻都是在做我不想做的事情。那年,我覺得自己無止盡地被情緒勒索,也去找諮商師聊過,對方建議我要先學會放手,不然勒索只會在關係裡反覆發生。」於是他躲進自己的洞穴,展開人生中對父母對激烈的一次抗議,直到他接演《與惡》,透過劇本反覆思考家人關係,終究發覺父母已老。
「我看過一種說法,當你發現父母老了的時候,你其實只剩下 55 天跟他們相處。」雖然現在媽媽仍不明白兒子為何搞消失,但他覺得也無妨,「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用同理心去理解她的世界觀,再悟出一個相處的方式,這是我成為演員之後很大的啟發。」王可元想起《陽光普照》最後那一幕,母與子角色對調,騎著腳踏車,抬頭仰望穿透樹葉縫隙的陽光。當演員,就是學會用他人的眼睛,欣賞形色不一的風景,當然也包含家人的眼睛。
除了修復家人關係,表演還能為生命帶來哪些驚喜,兩人都在等著看。他們神秘兮兮地聊起未知這個詞,覺得一切都太未知了,於是最近也不約而同地開始相信命運,認為只要向宇宙把身體打開,最好的安排自然會來。這兩位年輕演員,在表演路上踏實走著,不畏懼一次次把自己丟進完全摸不著頭緒的異世界裡激發更多元的作品,也是觀眾的幸運。
採訪後記:靈性の天蠍男孩 feat. 鹽燈
范少勳跟王可元或許因為都是天蠍座(?),特別容易 get 到對方的想法,訪問過程中常出現「喔喔喔喔,對對對~」的共鳴。這種情形除了發生在聊表演時,也發生在聊神秘力量的時刻。
范少勳說起他的按摩師:「我的按摩師是精油師,每次按摩之前都會先要我抽牌,抽出適合我當下狀態的精油。我只要沒在工作,抽出來都是類似的,但如果有帶角色,就會抽出不一樣的!他都會問我說『你最近是不是開拍了』,而且分析我角色的個性,十之八九都對,很妙ㄏㄡ!」
他說自己原本不是迷信的人,只是偶爾相信外星人,但經過這位按摩師的神算與反覆驗證之後,他便開始相信宇宙存在魔幻引力。
王可元年長幾歲,幽幽歎了一聲:「唉,你再過四年就會跟我一樣迷信了。」幾年前可元 boy 還是個對風水不屑一顧的男子,現在全然入坑。「我現在很喜歡精油啊,風水啊,還有鹽燈!我一開始非常不相信鹽燈欸,只是有一年衰到極點,我朋友就說我床對著廁所的門不 OK,接著我就開始研究風水。」
他們心有靈犀一般,說當演員之後看見太多命運的巧合,對某些事變得不得不信。
「像是未知宇宙啊,神秘力量啊,還有鹽燈。」王可元又再複誦了一次。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