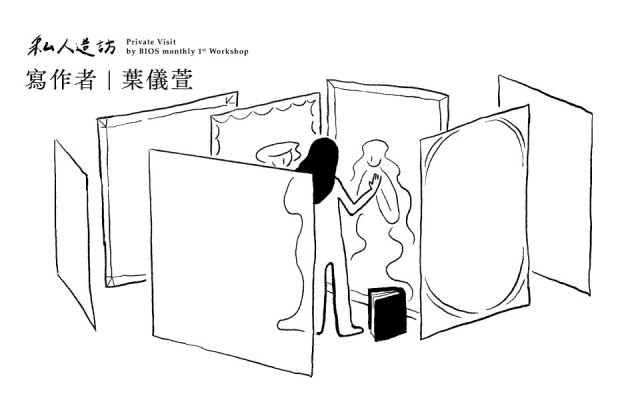在城中一夜消失|臨時政府如何創造一個臨時垃圾桶?
自六月起,常被用作堵路的垃圾桶便失去蹤影,刺眼的螢光橙外殼被換成黯淡的肉桂色膠袋。被野草蔓藤佔領的鐵絲網後,幾個零丁的垃圾桶擱置在雨後微濕的地上。一輛垃圾車呼嘯而過。妳捂著鼻子,一臉厭惡地拉著我的衣袖往前走,口裡喃喃說著什麼豪宅區怎可以那麼臭。垃圾車沿著旋轉路慢慢縮小,淹沒在像是逗號又像是問號的幾圈道路中。
上一次跟妳見面已經是半年前的事。
那時我不知道,原來一段關係可以這樣一點一點地消失,就像路邊的樓房那樣悄悄靠近海岸線,把對岸景色切割成無數碎片,偶爾在陽光下把人折射出一眼淚水。或許我早該發現,那天妳在舊同學聚會中顯得心事重重,並不是因為以前跟妳很要好的 Katy 在一次遊行中被捕;任職空姐的妳在社交媒體上保持沉默,也不是因為妳擔心某天被清算。八月那夜,我隨著人群往太古廣場散去,在漢堡包店滿佈塗鴉的窗前,瞥見一抹熟悉的背影匆匆掠過。回家路上,我傳了個短訊給你:「Safe?」卻從沒有收到妳的回覆。
也許那時我就該知道,這城裡的所有人和事都循著既定的軌道前進:垃圾桶最終淪為垃圾,惡法終究被極權暴力通過,三十年前高舉著「支持學運」橫額的年輕人今天在家裡咒罵著電視機裡血流披面的孩子,就連妳嚷著要去的西環泳棚也本是因日漸變差的維港水質變成打卡熱點。
妳指著剛才垃圾車駛往的方向,問我垃圾站為什麼會建在海邊。那可不是普通的垃圾站,我說,那是城內首個在人造洞穴裡興建的垃圾轉運站,負責把廢物收集、壓縮,再由船運往堆填區棄置。還記得在大學通識課曾學過,岩洞是在地層開挖的大型洞室,能為狹窄的城市騰出發展空間,完美隱藏污水處理廠或廢物轉運站等厭惡性設施。不過唯有真正懂得失去的人才知道,城中最珍貴的不是沒有垃圾、不是井然有序的街道,而是每天被油漆覆蓋但又重新被塗上的標語、滿佈殘存膠紙痕跡的隧道牆壁、坑坑洞洞的行人路和堆疊在街邊的磚頭。
這城熱衷於一切臨時的存在,譬如以垃圾袋臨時充當垃圾桶、以水泥臨時填補路上的沙洞、甚至以控制瘟疫擴散為名臨時限制人們聚集。有時候,臨時狀態會維持一段長久的時間,讓當權者能在期間隨心所欲地把城市捏成想要的形狀;他們似乎發現,把臨時替換成永恆的最好方法是隱藏過去的痕跡、刪除所有臨時狀態前的記憶,使人漸漸遺忘臨時的期限。
只是他們沒有想到,消失的事物總會以不同形式把消失的痕跡留住,而遠處的維多利亞城界石仍安靜地佇立在堅尼地城臨時遊樂場的角落。
我們沿著域多利道走著,零散的腳步越是與這城的過去靠近,妳我之間的距離越是拉開。我告訴妳港英政府在 1897 年興建域多利道時,曾在奠基石底安放時間囊。玻璃瓶裡載有當年的硬幣、紙幣及報紙。若要在 2020 年埋下一個新的時間囊,裡面應該會有防毒面罩、頭盔和磚頭吧——瓶口還要塞著布塊。妳聽後眉頭一皺。「應該再往前走五分鐘就到了。」妳把頭顱埋在手機的地圖導航裡,發光的街道把妳的臉分割成若干部份。我嘗試在這割裂之中捉緊一些什麼,偶爾自以為從妳眼中看見幾道光影亮起、閃爍幾下、然後再次熄滅。
天空又再次下起濛濛細雨,夕陽還未到來。浪花拍打在本已濕漉漉的木板路上。我們小心翼翼地邁進海的結界,畢竟,這是城中僅餘幾個還未被填海工程吞噬的海。通往海面的木棧道僅容一人通過,我走在妳身後,雨水把一切蒙上灰白色的濾鏡,前方島嶼和妳背影的輪廓被一併拭去。
【在城中一夜消失】
消失在香港四處蔓延。有些人和事物在一朝一夕間不再存在,如常被用作堵路的垃圾桶及磚頭,或在瘟疫中人們的下半臉。更多的消逝卻是個不動聲色的過程,悄然在城市不同角落留下缺口。城市人彷彿都患上健忘症,讓空虛感侵蝕記憶,終日沉溺在沒有過去的憂鬱及落寞中。我又能透過勾勒消失的邊界重新抵達那個失去的香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