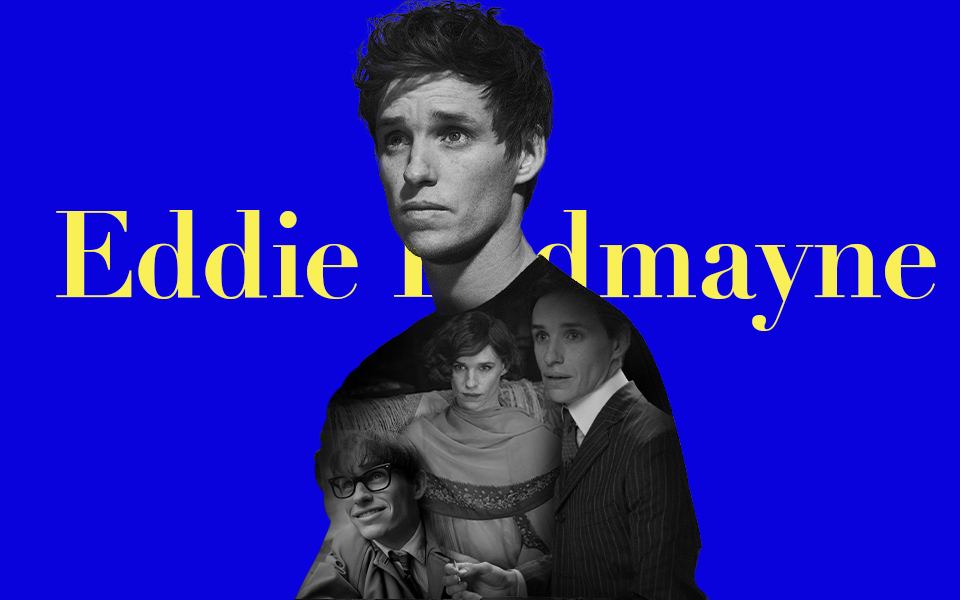
在被拒絕裡趨近完美:Eddie Redmayne 眼中,小小的自己
太在意自己的表現,他說自己總在開演前非常緊張。在劇場等待幕升起時,他習慣不斷碎唸。緊張,是他想像中永遠有另一個 Eddie Redmayne 游移在體外,觀察著自己。
Eddie Redmayne 身上有股謙良特質,面對稱讚壓制不住笑意,卻又笑得特別彆扭。回顧早年影視作品他常飾演一些小角色,如今談這些微薄的戲份時,他依然習慣把自己放得很小。《特務風雲:中情局誕生秘辛》裡可以飾演 Matt Damon 和 Angelina Jolie 的兒子,他認為是因為自己嘴唇很厚;而在與 Julianne Moore 對戲演母子的《浮華陷阱》裡,他說會被選上是因為有雀斑⋯⋯即便多少人誇讚《愛的萬物論》,他至今時常提醒大家,是因為有六七個好演員拒絕了邀約,才有這個機會。
表演作為一種賭注
從劇場走向電視電影,許多人最初對他的印象是在《悲慘世界》裡的馬留斯,一首獨白〈Empty Chairs at Empty Tables〉唱出革命裡親朋死別的夢想幻滅。但如果你說他唱歌好聽,他會先謝謝你願意這樣說,不過:「有人說我唱歌像芝麻街的科米蛙⋯⋯一直以來我都滿喜歡唱歌的,直到看見自己在《悲慘世界》中的表現。」
不難發現 Eddie Redmayne 是完美主義者(若你好奇星座:摩羯座),他也是許多人眼裡完美演員的化身。以《悲慘世界》到《愛的萬物論》、《丹麥女孩》,角色的挑戰從歌唱、肢體到性別,但 Eddie Redmayne 一一攻克,並以霍金一角於 2014 年拿下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彼時他才 33 歲。
從霍金的青年演到老年,漸凍爬滿他的身體。Eddie Redmayne 說最困難是支配所有肌肉,只為了演出霍金的靜止姿態,那是最耗費能量的「不動」。拍攝過程裡不僅有動作指導,還有熟習筋絡運作的整骨療法醫師隨時討論,他製作表格,寫下每一幕的肌肉與身體該如何動作。「為了扮演霍金,我必須像個舞者一般鍛鍊我的身體。我不伸展肌肉,而是學著如何緊縮。」
《愛的萬物論》並非按照時序拍攝。有時,他的身體必須迅速穿梭在不同年歲與症狀之中,考驗演員隨時切換的能力:「表演並不只是了解角色的進程,而是可以在一日之內進入不同的心智與體能狀態。」

《愛的萬物論》

《愛的萬物論》
最擔心的是終究還是有人會失望。他說,想到霍金及其他人會看到這部電影就讓他害怕,「如果你的角色是仍活著的人,那是另外一種表演。無論你做了多少功課,這都無法成為紀錄片。你一定會弄錯什麼,最後,你只能賭一把——因為你不在場。」
認真做好學生、總是在傾聽,他不時需要逼自己踏出慣常的學習模式:「我和許多優秀的演員一起工作,有些人真的很固執,固執到我會想說,難道你已經不願意學習新事物了嗎?他們不太聽導演的話,也不太聽其他演員的意見,就是一直、一直重複做自己。這真是個困難的情況,以我的自信心來說,我實在應該臉皮厚一些。」
追尋完美,循規蹈矩的刻苦求藝是做不到的。學會下賭,一步步前進的路上偶爾也嘗試跳躍——或許這樣的賭注,都是為了超越那雙時時關注著自己的眼睛。
一個平凡人的困惑
扮演霍金時他上了物理課,而在《丹麥女孩》裡,他與許多跨性別群體交流,從他們的人生故事裡看見自己曾有的誤解。他說,整部電影就像是一次學習,包含上映後的爭議也是。許多人抗議這個角色應該讓跨性別演員演出,而 Eddie Redmayne 也談及自己的猶豫,「至今仍然不確定,自己做的是不是對的事?」
導演 Tom Hooper 在《悲慘世界》時便與他合作過,手上早有《丹麥女孩》的劇本卻苦無資金開拍,前期便屬意由具有陰性特質、適合情感濃度強烈角色的 Eddie Redmayne 來演出。直到《愛的萬物論》讓他站上第一線演員之列,資金到位,跨性別者 Lili Elbe 的故事終於得以在大銀幕上現身。事實上這不是 Eddie Redmayne 第一次挑戰其他性別,早在 2002 年搬演的莎劇《第十二夜》裡,他即飾演主角 Viola(在劇中 Viola 又假扮為男性)。這也是他首次引起關注的劇場作品。

《丹麥女孩》

《丹麥女孩》
從《丹麥女孩》劇本早期階段參與,到最後成為電影得以面世的重要因子,Eddie Redmayne 明白邁向公平正義的困難與必要。位居風暴中心的他沉澱後說,「希望未來更多的跨性別演員不只可以扮演跨性別角色,也可以演出順性別角色。身為一個演員,我真的希望每一個演員都能演出任何角色,只要他以正直的心態和責任感來演出。」
Eddie Redmayne 的坦誠時常能在對峙的議題中帶出和緩的氛圍,他不太隱瞞自我懷疑,時時以自省堅守出一塊停戰區。
與華卓斯基雙導演合作的《朱比特崛起》,或許是形象大好的 Eddie Redmayne 近年來演技最有爭議的一次演出,他在這齣科幻作品裡飾演反派 Balem Abrasax,以氣音呈現出這個劇本設定中咽喉曾被割破的角色,一句情緒激昂的「Go!!」迎來許多訕笑與出戲的評論。
他並不避談這次演出,隨著時間過去,他說這個角色設定與演出方法有其原因,「對於角色來說那是個大膽的選擇,可惜最後沒有成功。」
《朱比特崛起》裡引發討論的一幕。
偶爾他也談起試鏡失敗的經驗,從他 11 歲參與小劇場開始便不斷錯過,他沒能成為凱羅忍,沒能成為《哈利波特:消失的密室》裡的湯姆瑞斗,沒能成為《星際異攻隊》的星爵。
「你永遠不會忘記被拒絕的感覺,那些被說不的時刻,根植在我們的腦海裡。這也是許多演員都非常神經質、緊張的原因。」
「我記得看過 Rachel Weisz 的訪問,裡頭說她一直覺得自己再也不會得到任何演出機會了。那時候我還很年輕,掙扎著要在演員這條路上前進,我想說,『拜託,妳是 Rachel Weisz 欸!妳一定沒問題的。』」直到自己有了看似「成功」的機遇,他才理解那種不安,「我真的也有一樣的感覺。」
那種恐懼,是驅使他一再努力的動力,或許也是我們能與他共鳴的原因。價值觀交錯的困惑,被拒絕的可悲與自卑,Eddie Redmayne 不迴避,總是侃侃而談。
不要被改變
演藝之外,Eddie Redmayne 的生活看來總是親切。他至今仍搭地鐵,有時被拍到正在看書,有時假裝還在《怪獸與牠們的產地》情境裡與木精對話。疫情期間,他和家人們過著農村生活,在節目上忍不住細數(女兒取的)那些雞的名字,Belinda、Sally、Henny Penny、Blanket 和 Henry⋯⋯儼然女兒傻瓜。
許多人驚訝於 Eddie 還搭地鐵,對此他實在不知該怎麼回應,因為,身為倫敦人不就是搭地鐵?「除了地鐵之外你要怎麼移動?開車嗎?從我家出發到任何地方大概要六小時吧。還是要雇用司機之類的嗎⋯⋯我不知道欸,我無法負擔這種開銷,實在太貴了。」
「要不就是改變你生活的方式,要不就學著適應那些關注。」顯然 Eddie Redmayne 選擇了後者。
訪問裡他不只一次提到「Marmite」,這是一種深咖啡色的麵包抹醬。Eddie Redmayne 愛死這種抹醬了,儘管有些人可能很不喜歡,但他回到家鄉時,每每看到 Marmite 就感覺心安,「它的包裝好像從八〇年代都沒變過。」世界越快,他越想安穩下來,去維繫某些隨時間沉澱的情懷。
2015 年他以演藝成就獲頒大英帝國勳章,或許那不僅僅是指拿奧斯卡、票房鉅片,還包含他一直以來持續讚頌的劇場,「從小時候到現在,只要踏進劇場,就是我最有想像力的時刻。我很願意回到劇場,我想讓大家知道,劇場並非很多人想像的那麼菁英,劇場裡有很多技巧像是如何說故事、建立自信心等等,都可以帶來幫助。」
看似堅定的 Eddie Redmayne,其實也曾猶豫過要不要做演員。沉浮於小角色時,他在 2009 年遇到 John Logan 的劇本《紅》。這是一齣有關藝術家 Mark Rothko 的故事,Redmayne 在劇中飾演虛構的助手,日以繼夜與藝術家辯論,試圖找出他心中最完美的顏色。《紅》讓他拿下東尼獎,也找回演戲的信仰。
在劍橋時他主修藝術史,畢業論文主題是法國藝術家 Yves Klein 發明調製的藍色 IKB(International Klein Blue,國際克萊因藍或簡稱為克萊因藍)。Yves Klein 畢生著迷於藍色,五〇年代他開始使用高飽和度的藍色進行單色創作,最終在化學家幫助下開發出一種獨特的藍色塗料,色澤飽滿、明亮。
Eddie Redmayne 為這種藍色著迷不已,「我為這個顏色寫了三萬字論文,不曾感到厭倦。這是種令人驚艷的顏料,怎麼會有一種顏色如此情緒飽滿?身為演員,真想在表演裡做到這種程度。」
事實上,Eddie Redmayne 是色盲,無法辨別某些顏色,卻總是能毫無障礙地辨識出克萊因藍,儘管只有一小塊。一如我們眼裡,他也已經成為某種獨樹一幟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