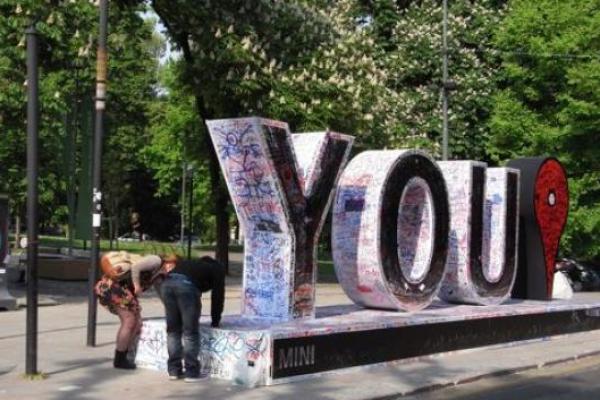非引戰:台灣的招牌就是醜嗎?──張柏韋╳陳彥安談「招牌:」
張柏韋最初對招牌的印象,是檳榔攤。
小時候住在新莊,路邊是一整排綿延的檳榔攤,一入夜就點亮霓虹燈招牌,孔雀狀的燈管把整條馬路染成曖昧的粉紫色。而經過的時候,大人會說,不要看。
「那個時候作為一個小男生,就覺得那邊是一個非常有色情感的地方。」
於是小時候的記憶裡,那隻粉紫色的霓虹孔雀連結了華麗、連結了香豔色情,也連結了禁忌。直到長大之後,才發現台灣許多夜場文化的場所,也都有那樣一隻孔雀出現。
「我發現其實招牌除了物體本身之外,它其實是象徵一種表達的關係。當這種招牌變成一種社會符號,它就跟台灣的情色文化有了關係。」
招牌就是文化的切面。2025 年,張柏韋和沿岸制作的陳彥安共同發起「p.n.g.」計劃,以社會學為經緯,織起文化的樣貌。品牌第一檔企劃展覽「招牌:」,在策展與創作中,留下更為深邃的提問——在單純的美醜討論之外,招牌還能不能有其他意義?
是真的醜
BIOS monthly:當我們在談論台灣的招牌的時候,許多人最直覺的反應是——好醜。招牌醜,連帶地讓整座城市都醜。兩位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會對生活周遭的招牌有了美醜的分判?
陳彥安:我們其實也一直在討論,到底是為什麼要討論美醜?因為對我來講,我們從小在這樣子的環境長大,其實不會覺得它醜,會覺得台灣的街景就是長這樣。直到有比較後,你才會覺得有美跟醜的差別。
但我自己認為,台灣的招牌不是醜,是雜。因為有很多不同時代的人,在不同的經濟狀況或生命經驗下,開店做了招牌。那我們又因為人口很稠密,很多不同的人都被塞在同一個地方,所以我覺得,其實是雜大於醜。
那我也並不是要引戰說,台灣的街景就是醜。可是我們需要去討論: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街景狀況?這其實是有一個脈絡的。

《招牌:》展覽呈現臺灣招牌多樣性,不同時代之下的招牌代表著審美價值觀的迭代,p.n.g.提供。
BIOS monthly:好奇這樣的「比較」,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呢?觀察國外的招牌,有什麼跟台灣不一樣的特色嗎?
陳彥安:我有一段滿長的時間是在國外生活,會發現其實在很多國外的大城市,招牌並不是一個這麼顯眼的存在。甚至我們最近在找一些大城市的招牌照片,才發現其實很難,因為他們可能就是在門上面寫一個小小的字,但大家還是有辦法找到它。
尤其在拍照的時候,透過相機就更會看到,在一個構圖的畫面裡面,我拍過去看到的是街道、是建築,因為街景的招牌少,建築物露出來的多,就會發現建築物很漂亮。可是在台灣,我們拍過去其實就是很多的招牌。
但有些時候再回來看台灣的街景,會發現我們有一些老建築也不醜,只是因為上面掛很多招牌,所以你看不到建築物的本體。
張柏韋:我覺得我的經驗還是在台灣。
我原本住新莊,後來我搬到天母去,那裡有比較多日僑或是大使館,他們的招牌風格和新莊給我的感覺,就有很明顯的巨大差別。新莊真的就是,你可以感覺到比較髒亂一點,天母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是一個新世界,包括街景跟招牌呈現的狀態,都明顯比新莊更簡潔更乾淨。
BIOS monthly:那時候就有意識到,台灣的招牌市容是「醜」的嗎?
張柏韋:你還記得我們以前的選舉海報嗎?幹,是真的醜耶!
你小時候有沒有一個印象,是施振榮在講微笑曲線?微笑曲線的 Y 軸是利潤,然後他說原創跟品牌端是賺最多錢的,而台灣就是作毛利率最低的生產這一段。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成長過程之中,有一個很大的敘述的脈絡是在說,我們只會生產,不懂得重視美學,不會發展品牌、也沒有原創精神。
我覺得那個論述的風格跟結果,影響至少這十幾二十年的人,我們會有一種自卑感吧!我覺得它好像告訴我們——我們在做的事情不那麼值錢。然後我們不值錢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不在意美感、不重視我們的美學素養。
有一方面我後來做美感教科書計劃,也是因為這樣。
BIOS monthly:但在台灣開始嘗試提倡、標舉美學的這幾年裡,你有觀察到生活周遭也有相對應的提升或改變嗎?
張柏韋:從某一年開始——當然有些地方現在還是醜,不可能全部都平行成長——但是我覺得很多選舉海報都好看很多了。直觀上最有感覺的,應該是聶永真跟蔡英文合作的那一年。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一直被說沒有美感,所以大家就想辦法,把自己覺得有美感的事情做出來。


《招牌:》展覽現場照,p.n.g.提供。
60 分的日常
BIOS monthly:在其他訪問裡,兩位將招牌定調為「日常生活中,因為過於熟悉而被忽略的事物」,這些熟悉卻被忽略的事物,為什麼會特別吸引你們呢?
陳彥安:這些東西其實我們日常都可以看到,但是因為沒有去深思,它就一直不會被改進,直到每一次開始有人筆戰,大家才又會出來討論。
我自己本來就很習慣去觀察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其實一條街上的招牌,可能有三成左右都是已經沒有在營業,可是還是掛在那裡嗎?這也是我們跟招牌商合作,他跟我們說才發現的。有一些以前很有趣的招牌工藝,它其實已經停業了,可是都還掛著,因為拆也要錢,不拆就不用付錢,所以就一直掛在那裡。
你現在在街道上看到的招牌,除了還有在營業的,還有一些已經沒有在營業的,它也都在跟你講話。這樣的事情你不去關注、不去討論,它其實一直都會在。
這也會有很多隱形的問題,小時候家長都會說不要走在騎樓下,因為招牌會掉下來。那這就是除了視覺美學之外,也是居住安全的問題。其實相關的法規一直都有,只能掛在多高、要掛多寬,只是因為增加的速度太快,拆的速度又來不及,所以很多招牌並不那麼符合法規。
張柏韋:我覺得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它有點像是人們的 60 分的理解——譬如今天你看到一個很喜歡的美術作品,那這個作品可能對你來說是 90 分的價值,但是這些被我們認知為日常,熟悉到有點忽視的東西,它其實就是我們認知中的 60 分。它是一個及格線。
在這個及格線以下,比它更爛的,你其實還是會有感受到,爛到有感覺;但跟它差不多的,你不會有感覺。
但問題就是:你的 60 分跟我的 60 分是不一樣的。而我們就是在處理這些 60 分的東西:這個 generation,或這個國家大部份的人,對 60 分的想法是什麼?
BIOS monthly:你的 90 分,也可能是我的 60 分——這個情況要怎麼進行溝通呢?
張柏韋:我誠實跟你講,我一開始做美感教科書的時候,每天都要跟人家打筆戰。
然後你會漸漸意識到,我要宣稱我做的東西比別人美這件事情,其實是很殘暴的。其實一定程度上,它就是一種優越感,就是我相較於你,我更優秀,然後這個優秀並沒有一個客觀標準,而是來自我審美的選擇。這是一個主觀價值的選擇。
所以久而久之,你會發現審美這件事情,它其實是一個說服的過程。多數人的偏愛並不一定絕對會比較好,但是如果多數人的審美喜歡的話,對你來說一定會有好處嘛。這件事情只是另外一種價值觀的選擇,所以你也沒辦法去宣稱這是絕對的優秀的。
但我覺得唯一能夠討論的東西就會變成是,我們怎麼去理解這些脈絡?
BIOS monthly:那台灣在招牌發展的脈絡上,又經過哪些不同的社會影響和演變呢?
張柏韋:第一件事情是技術的迭代。早期的招牌大部份都是寫的,因為那時候沒有辦法用那麼好的印刷方式。再來開始會去做一些凹折,或者是開始有霓虹燈、燈箱這樣的東西,到後來有跑馬燈這些電子化的設備,技術本身就是一個可以看的脈絡。
第二個就是台灣的經濟能力。譬如說早期台灣是加工出口區,有客廳即工廠這些概念,那他們會有的招牌形式可能就比較不是大型的招牌。到後期可能還出現夜場文化,當我們經濟好了,開始有人會想要娛樂,那像霓虹燈這樣子的存在,就會跟產業產生連結。
陳彥安:其實招牌也可以很明顯地反映出科技的變化。或許以前因為製作一個霓虹燈招牌的工藝相對複雜,所以大家會更節省地在做,不會說我要掛非常多個招牌。但現在不管是壓克力、雷切、卡典西德和真空成型,技術越來越發達以後,其實你掛一個招牌的成本變得很低。
那越省錢的結果就是,你做這個決定越不費力——那你當然就是多掛一點,越掛越出去、越掛越多,每個角度都讓你看得到我。
.jpg)
《招牌:》全新藝術裝置〈招牌聚落〉,p.n.g.提供。

《招牌:》 〈臺灣招牌歷史年表〉,p.n.g. 提供。
我是誰
BIOS monthly:展覽中的藝術裝置《街道地層》,以地層的概念作為招牌審美迭代的展示。但有招牌在不同的時代裡,發展出一個共同的符號標誌:比如老式的理髮廳都使用了共同的三色旋轉燈。這種共同性是怎麼發展出來的呢?
張柏韋:其實通常都是一開始有一家做這件事情,特別紅,然後大家去學。就是偷它的元素,偷到後來這個元素就符號化了,它變成一個最好理解、最好被表達的元素,然後大家就開始共用。通常都會先有一個紅的人去定義那個元素,然後剩下的人跟時代去篩選。
比方檳榔攤的孔雀燈管,它就是這樣凝煉的結果,但它必須要有文化脈絡的前提——當外國人來台灣,他看到這個孔雀霓虹燈,他可能甚至不覺得這東西是情色。它是需要有文化背景給我們影響,我們才能認得這個文化。
所以其實一個招牌要說明的東西,就是代表我要告訴你我是誰,所以它是一個自我定位的過程。然後你看到這個招牌,你也會有你的解讀嘛,我的表達不代表是你的理解。這個結果就會變成中間會有誤區,那所以招牌本身的溝通目的的存在,就是要一定程度上降低這個東西。 所以怎麼樣去降低?最好用的方式就是用符號。因為符號可以承載太多東西,可以用很快速的方式可以讓你了解我是誰。
BIOS monthly:展覽裡也有其他類似歷程發展的研究嗎?
陳彥安:我們也有做手繪招牌這個議題——其實像台中的手繪字體,如果認真去看的話,它都是來自同一個手繪師,他自己有延伸出一系列比較圓體的字型。
之前 justfont 有一系列是去調查台灣招牌的字體,然後就發現,其實手繪招牌的師傅他們有一本書,那本書是一個書法家寫下來的字體,然後他們會按照這個字體去投影,之後再描到紙上,再寫到比如說木板啊、或者是鐵板的載體上面。這些現在都還有在出版,等於現在的一些招牌店,他們還是會用這本書去做參考。

《招牌:》全新藝術裝置〈招牌地層〉,p.n.g.提供。
BIOS monthly:策展過程裡,你們有實際拜訪過哪些招牌師傅、或是嘗試過哪些工法嗎?
陳彥安:其實我本身是工業設計背景,所以對這些製程大概都有瞭解。說實在我覺得,安裝可能是最辛苦的。
因為像卡典要切割,現在也都是機器切割,或是鐳射雕刻,其實相對都是算好製作的。但是現在最主要的困難是缺工,每一家廠商都在缺。甚至有一些老的招牌廠,他們招牌其實很快就做好了,只是沒有人可以施工。
但實際以招牌製作來講,因為剛剛前面提到的技術進步,所以難易度一直有在下降,譬如說以前木刻的招牌很多,但現在木刻都變成是雷射雕刻——當然還是有些人會為了木刻的紋理手感而去使用,但大部分求快的話,其實現在的招牌店大家都身經百戰,客戶有什麼需求他們可能都聽過了,所以都很容易製作。
只是有一些比較難的技術在流失,比如說真空成型的招牌,現在台灣也越來越少廠商在做了,所以它的單價就很高。現在如果有需要做這種招牌,其實還是得跑到中國的工廠去做,只要扯到塑形類的,我們的工廠資源都在外溢。
自然生長
BIOS monthly:去年台南國華街永樂市場進行了一次招牌統一的更新,引來網路上許多討論,支持與反對各有意見。以視覺設計和社會學的角度切入,你們怎麼看待「以設計介入美化」和「保留原生的文化樣貌」之間的界線呢?「美化」的必要是什麼?又應該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發生呢?
陳彥安:我住在公館商圈,從我小的時候公館商圈就經歷過這樣的招牌整合。我記得以前的招牌就是五花八門,後來變成一致的圓角矩形,大家都一模一樣大,而且都掛在一樣的高度。當時是覺得很新奇,原來招牌可以這樣被改變。
的確以使用上來說,有些店家會反映這樣沒辦法凸顯自己的特色、好像每一家賣的東西都是一樣的。我自己也會想,到底一致性的招牌是不是一個好的辦法——但如果這是一個區域的共識跟自決,比如日本有些商店街會有協會,他們會思考這個街道想要呈現什麼樣子,就一起來做改變,不管是大小、外型、才值得統一,或者是招牌裡圖像的統一。
像以國華街的案例,因為它在外型和視覺上都統一修改,可能就會讓比較多人覺得,店家本來的特色被移除了。
張柏韋:說實在,我覺得人類自主的空間其實是很有限的。對我們來說,它就是我們生命記憶的一部分被調整被修正,但對人家來說,那是他的經營場所。
我覺得會引起爭議,是因為我們擔心有一部份我們所認同的童年記憶被篡改,我覺得這是一個大部份人都會 concern 的事情。但事實上,就算一堆人 concern 這件事情,都比不過商店本身自己想要改變,因為他才是最主要擁有主導權的人。
在這個前提之下,我覺得作為旁人也沒有什麼好置喙,頂多就是我小時候去吃的某些店,可能現在招牌不一樣,但還是很好吃,所以這對我來說真的沒有太大的影響。
BIOS monthly:讓民主來決定招牌的樣子?
陳彥安:我不知道能不能說絕對跟民主有關係,畢竟很多民主國家可能也不是這樣子⋯⋯但我覺得可能跟民主、跟我們對於法治的認同有點寬鬆,可能都有一點關係。
但我滿確定有一些不是那麼民主的國家,它可以用很一致性的方法來整合街道的美感,姑且不論這個美感是官方認為的、還是某個代表所認為的——但是我覺得自然生長的樣貌不見得是壞事。
我們現在都還在慢慢地找到我們自己,文化認同或者是美學認同,我們現在都是處於這個過程的其中一環,所以也是要靠大家接下來去討論,到底我們要讓我們的街道處於一個什麼樣子的樣態、怎麼樣讓外人可以透過這個樣態來定位我們。
BIOS monthly:這樣的定位,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過程、或是如何發生呢?
張柏韋:我們還是需要做出選擇。因為跳出美醜這個狀態,會有一個心態,叫做好像什麼都可以。就是相對主義的問題,好像都無所謂,反正你覺得好就好,覺得不好就不好。
但你會有一種失根的感覺,我們要定根在哪裡、我們要決定什麼東西對我們來說是好的或壞的,那就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的感生跟建立的結果。最後當我們形成台灣文化這個概念的過程之中,也會有一群人去完整某一種論述方式,然後它就變成一個判斷標準。但是判斷標準不會是永遠是正確的,它只會在那個論述底下是正確的,接下來就變成是全民要不要接受,或是買單那樣子的論述結果。
BIOS monthly:好奇兩位覺得,未來台灣的招牌會定根在什麼樣的方向?
張柏韋:我覺得一種是實用主義。這是目前普世最強的一種論述方式,因為實用不處理審美,它處理一種實務的結果。那這個實務結果會直接帶來好處——經濟效應也好、或者 benefit 也好,這些東西它就有說服力。
另外一種就是純感受型,它就是一個更強的審美說服結果。他可能是一個童年經驗,一個很個人的情感觸動,當下就征服你了,也有可能是很粗暴的,譬如說今天畢卡索跟你說,孩子這就是一幅好畫——在大師的光環加持之下,就覺得那應該是一幅好畫。它他沒有任何論述基礎,它就是情感上的說服結果,那我覺得最後可能就會有某一種會脫穎而出,成為新的主流論述。
陳彥安:就是⋯⋯諧音哏吧!

招牌:
時間|2025.03.21 - 2025.03.30(10:00-19:00)
地點|PPP時尚藝文空間(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26 巷 2 號 1 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