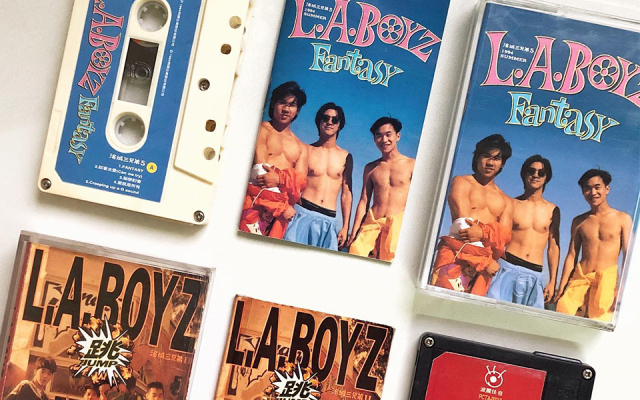e04嘛那麼累!專訪陳嫺靜:別人跟我說,我不知道妳想要做什麼
通靈少女出社會
做專輯的最後半年,陳嫺靜崩潰了。某天半夜她走進爸媽的房間,「那陣子我常常沒辦法控制,就是會突然嗚嗚嗚嗚嗚這樣;那天又有一點發燒,我就覺得說,喔我不行了,好我要麻煩一下媽媽。」
她默默坐上爸媽的床,還沒有發出任何聲音,眼淚就一顆一顆地掉。
她的新專輯名稱叫《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誰想要 sad:))》。

「他們那天好像有被我嚇到。」談失控和憂愁,陳嫺靜卻笑得興味盎然。她說自己平常喜歡觀察別人在做什麼,訪問時她談起自己的模樣也總像在觀察自己。在她眼中,陳爸爸和陳媽媽之前都是教授型的人(雖然沒有在當教授),凡事常用一種務實的態度說之以理。「我爸是那種,你只要一直嗯嗯嗯、蛤~、噢噢噢,他就可以一口氣講兩個小時的人。那天他就跟我說,工作就是這樣啊、爸媽也常常遇到工作上的問題⋯⋯」
「當下我其實就是聽,可是也沒有特別聽進去,因為我還在處理我自己。」幾乎不曾和爸媽講心事,她說因為彼此生活場景不同,他們給的建議有時反而讓她卡住。「我爸媽一直覺得我講話很快,讓他們跟不上,然後他們就會覺得我想法很硬之類的。」那天,是她成年後第一次主動在他們面前哭。
後來呢?「後來我媽泡好要給我喝的東西,回到房間,聽到我爸講那些,就說:『啊你平常不是說嫺靜都不跟你講事情,啊人家現在要跟你講了你又在那邊講,你可不可以讓她講?』」
爸爸閉上了嘴,陳嫺靜還在哭。那真的有和他們講什麼嗎?「當下有稍微再多講一點。」
多講了什麼?做專輯的這兩年多,參與製作的夥伴一直想要理解她——精確地說,是希望她努力讓他們理解她。「這也合理,因為要做的是我的專輯,所以大家一直想要理解我怎麼想。然後我付出很多精神和實際的行動去解釋我自己,比如整理參考的作品啦、做 PowerPoint 啦⋯⋯」
「但最後就是會收到別人跟我說,我不知道妳想要做什麼。」
如果每天都可以通靈,誰想要做 PowerPoint。陳嫺靜說,她原先想像專輯製作是一個共同摸索的過程,當事情不盡理想的時候一起試試看別的方法。然而,在製作期程和專業分工的條件下,有些夥伴需要知道她在想什麼才有辦法繼續往下工作。「可是我付出的這些努力,好像不足以讓別人了解我。」

「這樣的情況,會讓我產生一種懷疑:我是可以再多講一點,可是對方到底有沒有想要聽?這個懷疑會變成一個雙面的 judge,一方面對方會覺得我直接表明我的意思不是怎樣怎樣的時候,是在 judge 他做得不好;另一方面我也在 judge 我自己,為什麼我不能更好地對待別人?」
崩潰前的一兩通電話,她和自己很熟悉、認識很久的朋友也出現了這份 judge。她知道自己狀況不對了。
媽媽後來告訴她,這就叫出社會。
「她說:『妳現在出社會啦!妳還不了解社會!』我就回說:對!」
那現在呢,好點了嗎?「其實專輯出完之後好像就好了。」陳嫺靜說。
訪問這天是在專輯發行三個星期後。算起來,她才剛從崩潰中痊癒不到一個月。見面時我問她的第一題是她最近在忙什麼,她回答:「我最近好像比較常在想我想幹嘛。」
「那妳最近想幹嘛?」
「我想做別的事。」
「比方說?」
「我不知道,就是 anything。只要是別的事,aaaaanything 都好。」
遊戲登入畫面
兩年前陳嫺靜剛畢業,不太確定自己要做什麼。明明,大學時期就聲名大噪、被各路音樂人和歌迷奉為饒唱寶藏的她,幾乎每一篇訪談都被問到接下來會不會以音樂為職,而她卻總不置可否。此刻,她說做專輯前的自己像在遊戲裡玩著訪客模式,「訪客模式就是有什麼給什麼、有能力去玩什麼就去玩。當然我會想要唱歌、想表演,但那時候我不會在乎我的能力是不是可以用什麼方法再更進一步。」

出社會,其實是入社會。決定做專輯,是登出訪客模式,也是正式登入遊戲。「真的登入之後,你不可能在發現『哇賽這個遊戲有點難』的時候,就停在那邊。你一定會繼續練,點你的技能,玩到你覺得說好,這個遊戲我有玩到底了。」
促使她登入遊戲的,是顏社主理人迪拉。有天他找上她,跟她說,他要退休了。
「他說他在退休之前,至少要和我一起做一張作品。」
如今回想起來,那陣子多半是她聽他說。「他會說,要不要寫企劃投補助?要不要先寫一些 DEMO?」想企劃的時候,也是迪拉提議這張專輯要做雙版本。「除了 beats 的版本之外,他說因為我也很常和樂團合作,要不要把寫出來的歌做成兩版?」
他告訴她:妳現在這個年紀,也只能在這個時候出了;如果妳這個時候不出的話,妳再也出不了和現在一樣的東西了。「我就回說喔好,那我回去想一下。然後過幾個禮拜之後,他就說我們可以來寫那個案子。」「他說『投啦投啦,反正投了又不一定會中。』」
「我就想說,確實欸。」專輯都發了,陳嫺靜似乎仍沒有強烈的衝動,「在那當下,其實我也找不到時機跟他說,我其實還沒有想好。」
沒有想好,不代表不快樂。新專輯真的出了雙版本——《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誰想要sad:)) - 一起去度假》收錄以樂器為主的編曲,由 Jerry Li 李權哲擔任製作,請來陳嫺靜沒有合作過的落日飛車鼓手尊龍、露波合唱團吉他手洪晨、石青羅林吉他手郭以哲擔任樂手。《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誰想要sad:* - 合作的秘密》則由陳嫺靜邀集 beatmakers 加入,包含長年合作的 Sōryo、在金音獎舞台合作過的 Flowstrong、早就認識但沒一起做過歌的雷頓狗、Neil YEN 和 Charles Chang。
黃金陣容是真金,快樂也是真快樂。例如參與《合作的秘密》的 Robot Swing 鍵盤手鄭昭元,兩人合作的緣起完全貫徹創作者的浪漫:「有一天,我去他家 jam 了一兩段,覺得好好聽喔,就問他要不要一起來做專輯?」
隨性,自在,那也是她心中理想通靈的模樣:「我所謂的通靈,不是我想到了然後你剛好也想到,那樣也太不負責任了。」她說,「我覺得通靈比較像是一種傳染:我們彼此發送出各自的氣息,然後有一些氣息會彼此共振,在同一個場合裡面有頻率的連接。」
電波對上的前提,是彼此有在向外發送電波。「我覺得 Jerry 就是這樣的人。他在製作的時候會散發一個氣場,是『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那旁邊的人就會通靈到,知道他要幹嘛。」
身為作曲者,陳嫺靜和李權哲在磨合的過程中與其說是協調,不如說是談判:「我們都不太是愛妥協的類型。一開始他會說『這次聽妳的,那下次聽我的』這樣。」
同在《一起去度假》的樂手們也有相近的瀟灑,陳嫺靜稱之為「帥哥感」——「我們找的這些樂手他們本身都很厲害,可是他們同時有『不管怎樣我就是這樣、就算彈錯了也就是這樣』的心態。我們不會追求完全沒有出錯的精準。Jerry 自己也有這種帥哥感。」
「有一些合作對象,他會有很強烈的服務心態,會根據你的需求改變他們的作法和原則。但 Jerry 比較像是,他知道我們的想法不同,但他更在意最終的音樂成果是什麼、音樂才是最重要的。」

原先,專輯另一個版本也預計交由李權哲製作。「但是我們討論了很久,一直都找不到另一個版本的共識。」陳嫺靜說,「Jerry 就說,要他 all in 的話,那就全部都要聽他的。」
最後陳嫺靜決定,將《一起去度假》這個版本全權交給李權哲,但另一個版本另覓製作人。倒是這個決定反而讓李權哲詫異。「他就問我說,為什麼我可以放下?為什麼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全權交給別人?」
「我心裡是覺得說,我一方面是完全信任你,一方面我還是會下各種暗示,比方在你旁邊說『哇我覺得這好好聽喔』『是用這個嗎』之類的。」她提高聲音,示範戲劇化的慫恿,「但真正的原因是,我最初找其他人合作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想要看到新的畫面。」
「如果我還是照我的意思來,我就看不到新畫面了。」
happy 的條件
說得灑脫,但她其實沒那麼帥哥。雙版本這個形式,意外承載了她的掙扎。她形容另一版本的製作人鍾濰宇和爸媽一樣是像教授的人,業界經驗豐富,也因此共事時會嘗試以「標準模式」溝通。「小宇他一直跟我說,我如果要讓別人聽懂,就要用具象化的方式去說明。」
多具象?「比如說,直接指定這邊鋼琴要彈成怎樣、這邊鼓用哪種音色。」陳嫺靜回憶,「可是,我習慣說『我想要什麼感覺,你可不可以試試看?』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對方才會有一種創作的感覺,而不是交作業的感覺。然後小宇有時就會為了這之間的周旋傷透腦筋。」
其他令她崩潰的矛盾,表面上是工作習慣上的差異,深處卻藏著更多——「我在跟別人一起做事情的時候,會希望他們也喜歡做這件事,希望他們也樂在其中。而我認為,人在自己創造某些事的時候,更容易樂在其中。不是被套在一個圈圈之後才在裡面晃,而是自己晃一晃,忽然被圈圈套中的樣子。」
她希望別人快樂,別人卻希望她快樂。

「後來我覺得,這背後可能是一個規則:大家覺得說,企劃專輯的時候就是要懂這個藝人。可是首先,我不是藝人;其次,我要做的東西現在做出來了,大家聽了之後也明白了,那其實是一個很難詳細說明的內容。」
專輯發行之後,陳嫺靜在 Threads 分享自己讀了網友心得之後的心得:「今天一直在網路上巡邏(非常關心顧客評價)很開心看到有人分享共鳴、感動,說出喜歡或不喜的『真實心情』。⋯⋯在做最後這張 CD 的半年多遇到很多沒遇過的狀況,出社會後每天我都很懷疑,這個懷疑反映在了 CD 裡面,我很高興有人能聽出來我失去了一些意思,但也在積極的協尋中,我希望可以趕快找回來!或者還能多更多 ☆☆☆」
CD 裡反映了什麼?「我後來意識到,雖然有人會這樣要求,但『讓他人完全理解』這件事情不應該是我的目標。」她說,「本來我也覺得要學習順應規則、同時也是去練習不同做法。但回過頭來,我發現這條路其實對我來說,不是最舒服跟最有效率的路。」
「不是執著於要把自己在想什麼完全解釋清楚,而是,我現在會先想好我要幹嘛,然後我用這個幹嘛去跟別人溝通。對方也許不需要理解這幹嘛背後的意義。」
因過於努力被理解而迷惘,然後,因為摸清需要被理解的程度而放下。有趣的是,專輯裡的作品似乎比她早一步抵達這裡。「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誰想要 sad」這句話出自陳嫺靜四年前的 IG 貼文,比專輯更早出現。寫歌時她才從舊貼文中找來當歌名,最後成為專輯名稱,原因是這些歌本就沒有任何共同目標。
我原以為那 IG 貼文本身就是為了諧仿作家 Peter Su 的《如果可以簡單,誰想要複雜》,但她說她完全沒有想到這個。「我覺得我寫歌好像沒辦法先有一個主題再寫。通常是寫一寫,會發現一些重要的句子,繼續寫到一半會知道自己在幹嘛⋯⋯有點像你聽一個人演講,然後不特別去做筆記,過一段時間看自己回想起哪個段落,這樣的感覺。」
唯一確定的只有歌詞的調性。她刻意選擇使用最口語、最簡單的工具去談一件事情。原因是她會在某些場合出現一種隱微的反抗心——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討論社會議題的貼文,有些人會寫說『我覺得這一切都是什麼什麼結構問題』,用一個社會學的名詞。然後我就會覺得說,如果你想討論一件事情,但是你用的工具是別人聽不懂的工具,那你是要討論什麼?」
「只要上過一兩堂社會學就會上到,社會學之所以有這麼多學派,是因為他們意識到沒有任何一個理論可以解釋社會上所有事情。所以,每一個學派都各自消除某些設定、自訂某些前提,以便專心討論核心的價值。就像科學會設定一個無重力的環境,以便驗證某個運動定律——這是有必要的,可是這也表示那些東西不能無條件直接套用在整個社會上面。」
「每次看到這樣的貼文,我就會覺得那人好沒常識。」
我說,我明白妳選擇的討論策略了,那妳期待用這個策略來討論什麼?
她忽然愣住。「如果要我現在想一個原因⋯⋯我覺得不是我期待我的歌討論什麼,而是⋯⋯」
「我覺得我期待我講的話可以被聽懂。」
期待被理解的饒唱寶藏陳嫺靜用專輯出社會,其實也是走出自己。
.jpg)
aaaaanything
2021 年,她受邀藝術家張碩尹的線上展覽《肥皂》創作歌曲〈SOAP〉,並在開展時擔任現場演出 DJ;同年,她登上由時尚品牌 Gucci 創刊的非主流時裝雜誌《Perfect》封面,成為攝影師鍾靈鏡頭下的泡泡少女;2024 年,她受邀參與臺北文學季特展「編輯招募中」,成為「理想刊物」的五位跨域編輯之一。她說,她樂於接受來自不同領域的邀約——而且,這個「樂於」很重要。
「就算我登入了一個遊戲,我也不可能整天 24 小時都在玩這個遊戲。我一定有其他的生活,然後其他的生活讓我把這個遊戲玩得更好。」
「回到『要不要以音樂為生』這個問題,我覺得大家對於音樂人會有一個想像,好像他要傾注他的一生、完全奉獻自己,然後他做的所有決定都是因為他是音樂人⋯⋯我今天發了一個貼文、我今天穿了一件衣服都是因為我是音樂人⋯⋯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我要一直上線下線,才能在下一次上線時給別人更好的內容。對,所以我覺得這個上線跟下線還滿必要的。」
Anything,aaaaanything 都好。Anything 都是好的。
某天陳嫺靜發了一篇文,說她想要大家都要活得很開心,都對自己好一點。文一發,不少網友在底下留言「哇妳好善良」,她卻自知不是這樣。「其實我最中心的思想只是,如果大家都對自己好的話,就不會用到別人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對別人不好的人,都是自己過得不好,才會對別人不好。」
說完,她又露出幽微的笑,「開始講一些毫無理論的數據⋯⋯我的意思是,比方說我不想 judge 別人,是因為我也不想 judge 我自己,這件事情打在我身上會很痛——不是因為我知道我打別人很痛,是因為我知道打出去之後,我也會打到我自己。」
怎麼會講到這裡?「我是說,在跟不同人合作的過程中,我們互相揭露了很多不同的面向,有些可能我看過,有些我沒看過。這有點像是抽獎,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你遇到這個人的時候,你的反應會是怎樣,可是這些反應都真實存在於你的身體裡面。」
「大家應該要理解,一個人不是只有一個面向。」
音樂人陳嫺靜終於出了第一張專輯,但這不代表她從此只是音樂人。
而音樂人的她最近被要求交自介。一開始不知道自己要寫什麼。「你們有看到最近林強的自介嗎?我要以他的自介為目標。他生命經歷有足夠的狀況,讓他可以寫出一段普立茲等級的自介⋯⋯」
陳嫺靜自覺生命還不到那裡。既然如此,此刻的她交出的自介裡寫了什麼呢?
「我寫:『2025 年 3 月 7 號,我打開了兩張專輯。』」
不是發表,而是打開,彷彿那是別人的專輯。她是陳嫺靜,但她也總不只是陳嫺靜。

專訪還沒完 →→→
☆ 通靈少女出社會,跟陳嫺靜的雙版本專輯一起,我們也出了雙版本專訪、、、另一篇收錄當日的採訪全對話過程,推薦搭配服用。好看ㄉ,不看一下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