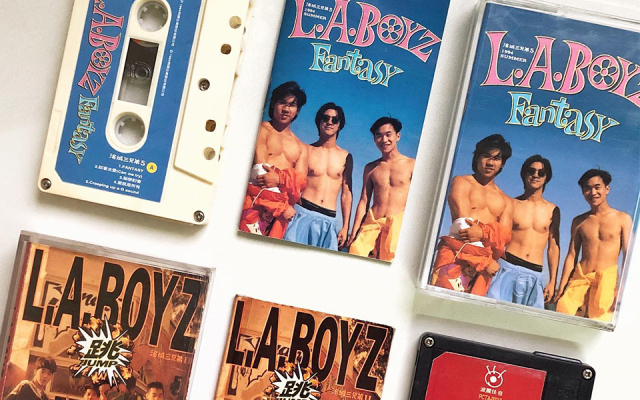專訪 philtrum_1998:我要去生活了(意思是我要去做自己的事了)
推薦你先看 →→→
☆ 通靈少女出社會,跟陳嫺靜的雙版本專輯一起,我們也出了雙版本專訪、、、還沒看過前篇的,請點擊以下傳送門;如果你已經看完ㄌ,那我們開始ㄅ!☆
陳嫺靜(Instagram ID: philtrum_1998)終於出專輯了。彷彿全世界都在等,然而專輯真的發行之後,社群上卻有人問:怎麼感覺沒什麼人在聽?
訪問時,她剛從 SXSW 的演出歸來,思考著自己是否真的以「演出者」的狀態站上那個舞台。寫作者蕭詒徽(Facebook ID: FayFluor)與她從演出聊到生活,從創作聊到登台,她不斷提起這個字:「應該」。那不是一種原則上的「應該」,更像是一種餘地——她並不急著填滿它,而是在每次行動之後,回頭問自己:那應該怎麼樣?
首張專輯《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誰想要 sad》從命名之初,就展現出這樣既鬆弛又警醒的矛盾——所有歌都寫完之後,她才從自己四年前的一則 IG 貼文裡翻出這句話當作標題。這張專輯不設主題,沒有綱領,每首歌各自出發、各自到達,靠的是陳嫺靜深思熟慮的隨性,和合作過程裡的「傳染」。
通靈少女終於出社會,她說這是自己登出訪客模式的過程。我們與她相約大稻埕的橋邊,從「應該」開始聊起。
〖 目錄 〗
— 點按標題,抵達那一個陳嫺靜 —
應該
新的照片
出社會
通靈 I
存取點
具象化
退休
通靈 II
上線下線
便便
自介
今天好嗎
通靈 III
—— 應該 ——
蕭詒徽(下記為 FayFluor):剛從 SXSW 演出回來,感覺怎麼樣?
陳嫺靜(下記為 philtrum_1998):我覺得⋯⋯有點不像真的在演出欸。
FayFluor:怎麼說?
philtrum_1998:也不是說它不是真的演出,我的意思是說⋯⋯感覺比較像參加一個活動。
FayFluor:在妳心中,活動跟演出的差別是什麼?
philtrum_1998:其實應該要是一場演出,只是我現在等級還不夠高。我應該讓它是一場演出才對。
FayFluor:我猜猜看喔,妳是指說,妳跟觀眾之間的關係應該要更有舞台距離嗎?
philtrum_1998:應該說,我自己應該要以一種「表演」的感覺去參與。
FayFluor:所以是妳自己內在的鬆緊程度拿捏的問題?
philtrum_1998:嗯⋯⋯應該說,假設你定義你自己的身份是作家,然後你去到一個聚會裡面,然後你跟他們一起寫東西,投入你的精力、你的能力在裡面,你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創作的場合。可是如果你去那邊,然後是去跟他們聊天,當然你也有講出你的想法、你的看法,或許你們有寫出一些東西。可是重點不是在那個東西本身,你可能就會覺得那只是一個聚會。
FayFluor:那為什麼這次妳會處在這個狀態?
philtrum_1998:就是等級還不夠高啊,還需要練等。如果等級夠高的話,就會更容易以演出的狀態為主。
FayFluor:妳剛剛一直用「應該」這個詞,為什麼妳覺得「應該」要是演出?
philtrum_1998:其實我不是現在才用應該,我平常就很常用。因為我覺得我的視角有限。大部份時候我都沒有很明確覺得一件事一定是怎樣。
FayFluor:但如果是這樣的話,就不會用「應該」了不是嗎?如果妳覺得每件事情都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就不會有一個「我應該要那樣才對」的想法。
philtrum_1998:對,我覺得每件事都有可能性,但是,我覺得我還是要先講出我現在怎樣想。「雖然在未來可能會打臉我自己,但我現在是這樣想沒錯」的這個感覺。〖 回目錄 〗
—— 新的照片 ——
FayFluor:妳那張筆記是為了訪問而做的筆記嗎?
philtrum_1998:喔對啊,可是我只有做到第 11 題。因為我來不及做⋯⋯
FayFluor:沒關係啦⋯⋯
philtrum_1998:我前幾天去台東看一個表演,然後就跟我朋友玩桌遊。那個桌遊是看你有多了解你朋友,它會出一些問題,譬如說,你有多大的機率晚上不洗澡?然後你的朋友就要猜大家的機率排序,0% 到 100%。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你有多常臨時抱佛腳」,我寫了 125%,直接被罵,因為超過 100%。
FayFluor:那,妳會很期待妳做的準備都被完整地問到嗎?
philtrum_1998:其實好像也還好,我只是覺得有做準備的話,感覺先想過一下⋯⋯但我也不是真的想得很深入,比較像是之前寫作文,大家不是都會說,你先看題目、寫完選擇題再去寫,你就會寫出不太一樣的內容。
FayFluor:我已經做了快三年的自由書寫,這件事改變了我思考的順序。就像妳剛剛說的那樣,以前的我比較會是有題目再往下走,現在我反而變成比較會想要去捕捉當下的狀態、然後再回過頭來思考之前到底在想什麼。但妳是不是天生就已經是後者?
philtrum_1998:對啊。我好像滿喜歡這樣的,雖然這也不是我選擇的。
FayFluor:那妳曾經想要改變這件事情過嗎?
philtrum_1998:有啊,我一直都想要變得更有邏輯啊。
FayFluor:那妳做了哪些嘗試?
philtrum_1998:會看一點我不會看的書啊哈哈哈。
FayFluor:像是?
philtrum_1998:如何溝通之類的這種。
FayFluor:那妳覺得它們有幫助到妳嗎?
philtrum_1998:它會告訴你說,首先第一步要怎樣,第二步要怎樣,讓你好像很有邏輯這樣。然後我就會覺得好像可以這樣想想看。應該有幫助吧我猜啦,只是我沒辦法鑑定。至少讓我知道有一種模式。
FayFluor:其實我最近也在看這方面的書。
philtrum_1998:真的喔,溝通的嗎?
FayFluor:不是溝通,我最近在看《順著大腦來生活》。它是一本以腦科學研究為基礎的生產力工具書,作者搜羅了很多腦科學的研究結果,然後把那些結果化為實際的做法。
比方說,要怎麼樣讓自己跳脫一個情緒狀態呢?腦科學研究發現,最快的方法是在自己心裡面幫自己貼標籤:當妳意識到妳現在很緊張的時候,妳就在心裡說「天啊陳嫺靜,妳現在在緊張欸」,然後妳就可以稍微跳脫那個緊張的狀態。
它也會告訴妳詳細的條件,比方說妳只能夠貼很簡單的標籤,不能夠掉進回憶當中,做太完整的自我描述,妳要貼很表面、很單純的標籤,那樣才會有用。
philtrum_1998:好,我回去來研讀一下。
FayFluor:回到妳剛剛說妳滿喜歡妳原本的狀態。所以妳想要改變不是因為不喜歡妳自己的狀態,只是還是會想要看看自己的另外一面是什麼樣子,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philtrum_1998:我覺得我有一個想要變動的心情,可是我覺得這個變動不是因為我不喜歡什麼,因為通常,通常我應該滿喜歡各種事情,不管好事還是壞事。
我覺得我想變成怎樣,都不是因為我不喜歡,而是因為我覺得可能可以有新的照片,類似這種感覺。
FayFluor:那這樣的話,妳曾經有過發現新的狀態,但妳不太喜歡,所以想要回到過去某個狀態的時刻嗎?
philtrum_1998:有啊。
FayFluor:有什麼例子?
philtrum_1998:做專輯的中間就有。〖 回目錄 〗
—— 出社會 ——
FayFluor:做專輯中間怎麼了?
philtrum_1998:因為做專輯就算那個嘛,出社會⋯⋯這我媽說的。她說妳遇到這些問題就是因為妳現在出社會啦,然後她說:「妳還不認識社會!」我就說:「對!」
反正就是,我覺得大家會做一些選擇,然後可是可能自己會忘記。就比如說,你可能很常明明看到訊息但沒有回。你不會去細究原因,但是在某件事情發生的時候,你就會突然想起來,想到說,我那時候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如果立刻回了,可是對方沒有回,我就會等在那邊,然後我會覺得「蛤他怎麼不回?」這樣的一個心情。但是我不想要這個心情,所以我才會看到訊息,然後過了很久才回。
FayFluor:這邊我有兩個想補問的,一個是:妳跟妳媽平常會聊妳做音樂或做專輯的事情?
philtrum_1998:不會。
FayFluor:那為什麼剛剛會出現這個出社會的對話?
philtrum_1998:因為我中間有一段時間崩潰了。
FayFluor:怎麼了?
philtrum_1998: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其實。我通常不會跟家人討論很多我在想的事,因為我覺得我的想法自己都還沒整理出一個規則,要怎麼跟別人講?加上我爸媽之前都是那種教授型的人,嗯,我不是說職業,我的意思是說,就遇到一件事情,他們就會一直說妳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FayFluor:原來如此,應該教授!我們接回去了。
philtrum_1998:但他們就是一種關心。只是,時代不同⋯⋯也不是啦(笑)應該說場景不一樣,所以有的時候他們給我的建議會反而讓我有一點卡住,然後我也覺得,這樣會給他們一些不必要的擔心,所以通常我不太會講。
但反正做專輯中間我有一度就是大崩潰。那陣子我很常就是,嘴一開就這樣咦咦咦,然後嗚嗚嗚嗚嗚。
FayFluor:妳說哭嗎?
philtrum_1998:對啊。就是沒辦法控制,然後有一天我就是,就是有一點發燒吧,然後我就覺得,喔不行了,到了半夜我就想說好,我麻煩一下媽媽這樣,然後去他們房間。
然後我在他們床上,從頭到尾沒有發出聲音,就是直接眼淚一直掉。
FayFluor:這是妳人生中很少數的,在他們面前哭的經歷嗎?
philtrum_1998:對啊,就只有那段時間這樣。他們那天好像有被我嚇到。
FayFluor:那為什麼會聊到出社會?
philtrum_1998:他們就對著大爆哭的我說。
FayFluor:⋯⋯如果是我的話,聽到這個回應我會繼續大爆哭。
philtrum_1998:我爸也是教授嘛,我爸是那種,妳只要一直嗯嗯嗯、蛤~、噢噢噢,他就可以一口氣講兩個小時的人。
那天我媽先說完了之後,就去泡一些東西給我喝,然後他就在旁邊,說工作就是這樣啊、爸媽也常常遇到工作上的問題⋯⋯當下我其實根本就是聽,可是我也沒有特別聽進去,因為我當下就是也沒辦法控制,我還在處理我自己。
結果過了一陣子之後,我媽聽到我爸這樣講,就說「你不是都說平常嫺靜都不跟你講事情,啊現在她要講了你又在那邊講,你要不要聽她講?」
FayFluor:哇!
philtrum_1998:哇!
FayFluor:那妳後來真的有跟他們講一些事嗎?
philtrum_1998:當下有稍微再講多一點。〖 回目錄 〗
—— 通靈 I ——
FayFluor:講了哪些事?
philtrum_1998:就是可能遇到的狀況。
FayFluor:我想聽。遇到了什麼?
philtrum_1998:就是製作中出現了一些問題。總結來說,這整段過程之中有一個我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通常我會覺得,遇到困難可以解決,可是現在有一個我沒辦法解決的問題,造成了各式各樣的事情。
FayFluor:Which is?
philtrum_1998:就是在這整個過程之中大家一直想要理解我。也是合理,因為要做我的專輯,所以就變成說大家一直想要理解我怎麼想。然後我覺得我付出很多精神,同時還有實際的作法,就譬如說作品的範例,然後整理什麼 PowerPoint 的,就是各種事情去解釋我為什麼這樣想,但最後就是會收到別人跟我說,我不知道妳想要做什麼。
可能我跟對方回饋說,好像不該是這樣子,我們要不要試試看什麼的時候,對方就會這樣跟我講。或是他會跟我講說,喔他覺得他沒有辦法做。類似這類狀況。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那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因為我覺得我已經 pulled up 了。
如果依照我的感覺的話,我會覺得說就大家都通靈就好啦!就各自做各自的事情。然後總會有一個喜好是對到的。
但最後陷入這個別人跟我說「欸,那我想要知道妳在想什麼,所以我們才能繼續下去」的狀況。可是,我付出的全部這些努力,好像不足以讓別人了解我。
FayFluor:妳的這個沮喪比較多是針對妳自己,還是比較多針對合作夥伴不能理解的表態?
philtrum_1998:在那個視角之下,我會覺得我是可以再多講,但是對方有沒有想聽?我對人產生了一種懷疑,然後這個懷疑就變成一個 judge,然後 judge 這件事情是雙面的。
我 judge 別人,但我最懷疑的是我自己。就是,因為我會直接講說,可是我覺得是這樣這樣這樣⋯⋯我的本意可能是:我覺得事情好像可以怎樣做,可是可能會讓別人覺得說,妳是不是在指責我做不好?別人也會覺得我在 judge 他。然後當我這樣懷疑別人的時候,我也會覺得別人在 judge 我⋯⋯
這一個懷疑跟 judge,讓我覺得我沒辦法好好地對待別人。
那陣子有幾通電話,會讓我覺得說,如果不是在這個狀態下面的話,我可以用好的視角去看待別人給我的反應,我不會去懷疑他這樣子說是不是因為背後有什麼心情是我沒有察覺到的,然後其實我們現在正在談論的這件事情,其實根本就不是這件事情。
有大概一兩次,是我面對很熟悉、已經認識很久的人,也出現了這一個不好的視角,然後我覺得在電話裡面,我變得有一點尖銳。
所以我就開始覺得自己狀況不對。
FayFluor:這個情況持續了多久?
philtrum_1998:半年。
FayFluor:那這兩張專輯的製作大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philtrum_1998:從我那時候要畢業,大概兩年多前。
FayFluor:等於是在兩年中的最後這半年,出現了妳剛剛說的這個情況是嗎?
philtrum_1998:對。〖 回目錄 〗
—— 存取點 ——
FayFluor:後來這個情況有解決嗎?還是現在還是這個樣子?
philtrum_1998:我還是在解決我這個懷疑的問題。
其實這就是一個規則嘛,大家覺得說應該要這樣做專輯,就是要懂這個藝人然後才能繼續做下去。可是實際上來說,首先第一個我也不是藝人,然後再來就是,我要做的東西,現在真的已經做出來了嘛,大家也聽到了,那是一個很難說明的內容。
所以這也不是他們理解我,就能說明好的內容。後來就會覺得說,雖然他們這樣要求,但這件事情不應該當成我的目標。
一開始會覺得說好像要順應這個規則,我也覺得這樣子才會有練習不同做法的感覺嘛。但是後來,收到這些結果,我發現這條路其實對我來說不是最舒服跟最有效率的路,我可能就又回到了⋯⋯也不會回到原本⋯⋯但是去了一個新的地方,所以我現在就是會覺得說,我不會很執著於說我要解釋我在想什麼,變成是說,在音樂之外,我會先想好我要幹嘛,然後我用這個「我想要幹嘛」去跟別人溝通,或許對方也不需要理解這個幹嘛背後的意義。
FayFluor:所以妳可能原本期待一個彼此一起摸索的這件事情,妳現在有點放掉了?
philtrum_1998:我原本期待,然後我也被期待這樣子做。
FayFluor:做法上我 get 到了,但情緒上呢?妳後來的崩潰是怎麼處理掉的?還是也還沒處理掉?
philtrum_1998:好像專輯發完就好了欸!
FayFluor:原來如此。專輯這邊我再補一個:妳幾年前很常被問到,到底要不要以音樂為職,那現在看來妳做了這個選擇。為什麼做了這個選擇?
philtrum_1998:但是,其實我沒有覺得我做了專輯,就會是音樂人。
我現在確實會想要鑽研這條路,但是,不是因為我做了專輯。
FayFluor:好,那我的問題就會變成,為什麼想要繼續鑽研?
philtrum_1998:一開始是因為迪拉問我。因為他那時候要退休嘛⋯⋯他就說退休之前一定至少要和我做一張。
我就覺得說喔好,那可以試試看,因為一直以來我也都是別人問我,我就會很容易被迷惑。
然後,就好比你玩一個遊戲,你不可能在你開始感覺到「哇賽這個遊戲好像有點難」的時候,就停在那邊啊,你一定要練到你覺得,哇這個遊戲我玩到底了的這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有點像這樣。對音樂這件事,我之前可能還在玩訪客模式,然後我一旦登入了之後,就開始發現,哇塞這些技能要點要花很久的時間。
但我既然已經登入了,我就不能讓我的角色停在這裡。
FayFluor:這個所謂登入的時機點,如果要由妳來定義的話,是在什麼時間點?
philtrum_1998:我覺得是開始製作專輯的時候。因為要用到很多之前沒有用過的工具。我之前等於是零能力⋯⋯
所以寫完歌要去跟 Jerry 一起工作的時候,我要跟他講我的想法,一起聽音樂或是幹嘛幹嘛的,後面開始要跟大家同步錄音,討論說我的 vocal 想要呈現怎樣的方式,然後要怎麼錄音——在這之前我都是用 iPhone 耳機在家裡錄音——但開始製作之後就是買了一些設備,研究一些內容,然後找到自己適合什麼東西。
這些過程你就必須要存檔。你沒辦法重新再玩。
FayFluor:妳在這個過程當中,是覺得有趣的嗎?
philtrum_1998:我覺得很好玩。你玩遊戲會覺得不好玩嗎?
FayFluor:我最近在玩一個遊戲叫《Don't Starve Together》,然後我發現,我之所以一再回到這個遊戲裡面去玩它,是因為不甘心跟倔強。對我來講,這就不是一個好玩的情緒,但是我依然因為這樣子點了很多技能樹。所以我才會想問妳這個問題,有沒有因為不甘心或壓力而驅動的時刻?
philtrum_1998:我覺得不甘心被我擺在比較後面的位置。但當然還是會有。像 SXSW 表演完我也覺得很不甘心,可是這個情緒被我擺在比較後面的位置,因為更前面的位置是我知道有新的東西可以選或是挑戰。
至於驅動這整件事⋯⋯我不太確定原因是什麼。〖 回目錄 〗
—— 具象化 ——
FayFluor:妳和權哲通常怎麼樣討論製作上的事情?
philtrum_1998:我覺得因為我們兩個都是比較,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對,我們都比較不是妥協的類型。所以,譬如說一開始在調 vocal 的時候就是會有一個情境是他會說「欸這次聽妳的,下次要聽我的。」這樣。
我後來發現有些人是比較偏向服務型合作的——就是你有什麼需求,他就會努力幫你做到,調整自己的做法、改變原本的規則。但 Jerry 不是。他比較像是「我知道妳有妳的想法,但我們的目標是什麼?」他的重心會回到音樂本身,他覺得音樂是一件事情,那這件事情的本質是什麼?所以音樂才是最重要的。跟這樣的人合作,會有新的畫面出現。
FayFluor:妳們討論最久的是哪件事?
philtrum_1998:我其實跟他討論超久的,本來這兩張專輯都要給他做。
FayFluor:妳是說原本這兩張都打算找他製作?
philtrum_1998:對,原本的想法是這樣。但後來中間臨時換了製作人。
FayFluor:換的原因是什麼?
philtrum_1998:一是時間太趕,再來就是我們其實磨了很久都找不出一個清楚的方向,特別是在討論第二張的時候。他那時候就有說,如果他要 all in 的話,那就要完全照他的想法來做。
後來我們討論了很久,決定把黑膠版本這張專輯就請他 all in。那時候我們也聊了滿多,他就有問我說,為什麼我願意這樣放手。因為他自己的作品,他沒辦法這樣放下——那時候他也正在做自己的專輯,他說他自己不可能把整件事完全交給別人。
我心裡其實是覺得,我說「放給你做」是因為我非常信任你,但我也還是會在某些時候想要偷偷下暗示,比如說:「欸這個好好聽喔~」「是用這個嗎?」這種方式。
但因為我後來發現我想要跟別人合作的原因,是想看到新的畫面。如果什麼都照我自己的意思來,那就不會有新的畫面了。
FayFluor:那妳和濰宇的合作又是什麼樣子?
philtrum_1998:跟小宇合作的話……小宇是金牛座(笑)
FayFluor:Which means??
philtrum_1998:雖然 Jerry 也是在金牛座跟牡羊座的交界那一天,但他自我認同是牡羊座,我也覺得他這樣很好。但他同時也有金牛座的堅持。這兩個人技術上都是金牛座(笑),但 Jerry 覺得他是牡羊座⋯⋯
總之!小宇的話,他比較是「事情應該要怎樣怎樣」的類型,也比較像教授的人。
雖然他看起來溫溫的,但其實也有鋒利的一面。畢竟他做過很多不同的藝人或樂團,也熟悉工作時「應該怎麼做」的模式,像是要在什麼時間內完成什麼階段的東西。
而我對這種流程有一點不太習慣。後來小宇一直跟我說的重點是——妳要讓別人聽懂妳想表達的內容,就要用比較具象化的方式去說明它。
我有試著這樣做,但站在我的視角來看,我不覺得每個人都會因為這樣就更有效率地接收到。所以我後來還是⋯⋯嗯,沒有完全照那個方式繼續做下去。
FayFluor:他的「具象化」是指很多 references 嗎?
philtrum_1998:對,references。還有技術細節上的,比方說直接指定某段鋼琴要怎麼彈、這邊鼓要用哪種音色這類的。
但我通常還是習慣會用「欸我想要一種什麼什麼的感覺,你可以試試看嗎?」來溝通,因為我覺得這樣對方會有創作的空間,而不是當成在交作業。
在小宇的工作環境裡,這套具象化、明確的說法可能才是最有效率的,所以有時候他就會為了這之間的周旋傷透腦筋哈哈哈。對,但我覺得⋯⋯總之就是剛剛前面那段思考。
所以我很謝謝小宇可以用他的方式,讓我,或說這個作品,可以在安全的軌道上賽車。〖 回目錄 〗
—— 退休 ——
FayFluor:一開始就預設要做成雙版本嗎?
philtrum_1998:那是迪拉提的想法。
FayFluor:那他怎麼說服妳,妳又是為什麼接受了?
philtrum_1998:為什麼他會提這個——嗯這個你可以直接去問他啦。但我可以說說我自己的感覺。
那時候我要畢業了,他就找我聊天,然後他說他準備要退休了。他那時候說:「妳這個年紀只能現在出,如果現在不出,以後就不可能再做出像妳現在這個狀態的東西了。」
他說他希望退休前至少能跟我一起做一張作品。那時候我其實也不知道自己畢業之後要幹嘛,就想說:嗯,好啊,那我回去想一下。
過了幾天、幾個禮拜,他又約我出來,說:「那我們來寫那個補助案吧。」
其實那陣子我跟迪拉的溝通狀況一直都是我主要在聽他講,所以在當下我也找不到時機說,其實我還沒想清楚。
但後來他說:「反正就先投投看嘛,也不一定會中。」我就想說,確實。然後就寫了一些 DEMO。
FayFluor:這整個過程對妳來說是快樂的嗎?我越聽越覺得妳有點被催促的感覺。
philtrum_1998:被催促會不快樂嗎?我覺得要看態度欸。我這個人滿容易被迷惑的(笑)
如果我當下就已經感覺到對方的態度不對——像是有些人是有隱藏企圖的催,比如像一些媽媽會說:「欸都九點了妳怎麼還不出門?」但其實才八點。她其實只是想要管妳,但把自己的願望講成某種事實。
我覺得我喜歡的「催」是那種,我知道對方要什麼,而我也覺得那個方向我們都可能會開心;我不喜歡的是那種有隱藏內容、卻不說清楚的。
FayFluor:所以如果妳當下有意識到對方有隱藏目的,妳就會不舒服。
philtrum_1998:對,如果我沒有意識到那個隱藏內容,我就會有點後知後覺,會卡住。
雙版本這件事,迪拉那時候說,除了音樂本身,企劃面也要有一個哏。所以他就提說可以做雙版本。除了我自己跟 Sōryo 之前做的比較 beat 感覺的編曲,我後來也開始跟很多樂團人合作。他覺得這樣的編曲方式跟我跟樂團一起表演的狀態也很搭,所以他說不如這樣——先把所有歌都寫完之後,乾脆直接做成兩個不同版本。
FayFluor:妳剛剛提到很多編曲者都是妳原本就認識的人,為什麼會傾向找熟人,而不是完全沒合作過的人?
philtrum_1998:喔,其實黑膠那一邊其實大多都是我原本不認識的,除了 Jerry 之外,像尊龍、以哲、洪晨我之前都沒碰過。
那時候就是有一個想法是,想要找新的合作對象。找樂手的時候,我們其實有討論到一點:我不是那種唱得非常精準的人,所以我們其實是想要找一些「會出錯」的人。
FayFluor:我懂妳意思。
philtrum_1998:對,我希望那個狀態是有機、流動的。所以我找的這些樂手他們本身都很厲害,但我覺得更厲害的是他們身上有一種「帥哥感」。
Jerry 也是有這種帥哥感——就是「我不管怎樣我就是這樣,即使彈錯了我也就是這樣」的那種心態。我們不會追求完全沒有出錯的精準。
另外一版的人是我來找,所以我就找我自己認識的人試試看。其中 Flowstrong 是因為我們在金音獎合作過。Neil YEN 是之前就認識。雷頓狗我也認識,但不是從音樂上認識的,只是覺得可以試試看。
還有鄭昭元,有一次我去他家 jam,他彈鋼琴、我就唱了一段,然後哇好好聽喔!我就說:「欸,要不要來做專輯?」
FayFluor:超政大的欸。
philtrum_1998:怎麼說?
FayFluor:很隨性,做做看的感覺。
philtrum_1998:還有誰像這樣?
FayFluor:我。〖 回目錄 〗
—— 通靈 II ——
FayFluor:妳剛剛提到,在這次專輯創作的過程中,有種讓別人覺得妳好像比較「上位」、像導演或製作人的相處模式——甚至有點像在 judge 別人的感覺——這種狀態,在妳平常的生活中也常出現嗎?
philtrum_1998:我覺得超不常出現欸。
FayFluor:所以是做專輯的時候特別冒出來的?
philtrum_1998:做專輯的時候會,然後在我家裡的時候也會。
FayFluor:在家裡是怎麼樣?
philtrum_1998:我爸媽一直覺得我講話很快,讓他們跟不上,然後他就會覺得我想法很硬之類的。但我在朋友之間完全不是這樣。我在群體裡的感覺是,大家不會期待我一定要幹嘛。
FayFluor:大家不會期待妳要幹嘛?
philtrum_1998:我的意思是,比如說一群人一起出去玩,有些人就會自然變成那個負責什麼什麼的人,像是負責記帳、負責拍照什麼的。但我不是那種會被賦予任務的人。
但不是說我什麼都不做。我也會想做事啊,就會說「那我來開車好了」,只是大家不會先預設我要負責什麼。
FayFluor:妳是朋友群裡的⋯⋯寵物嗎?
philtrum_1998:不知道⋯⋯但總之我不是那種會發號施令的人。大多時候我就是喜歡觀察別人的狀態,所以我就會是那個在旁邊觀察的人。
FayFluor:了解。第二個問題是——妳剛剛有提到「通靈」這種溝通模式。這種心有靈犀的合作狀態,是妳本來在人生中就很常用的方式嗎?還是也是在做專輯或作品的時候才特別渴望這種感覺?
philtrum_1998:它確實存在於我的人生中。但在做作品的時候,有人會跟我說不要這樣。
就是⋯⋯現在我會覺得通靈其實是必要的。因為文字會有不同的解讀,如果我丟出一個字,每個人理解的都不一樣。那在這種狀態下,如果沒有一種心靈上的感應,就會很難抓到彼此的頻率。
我中間一度以為這件事是可以 work on it 的,但後來發現不行。後來我發現——通靈這件事其實比較像是一種「傳染」。
FayFluor:傳染?怎麼說?
philtrum_1998:就是,它不是「我知道妳在想什麼、妳也知道我在想什麼」這麼直接。那種講法太不負責任了。
我覺得比較像是,我們彼此發送出各自的氣息,然後有一些氣息會彼此共振,在同一個場合裡面有頻率的連接。
拿 Jerry 來說好了——我覺得 Jerry 就是這樣的人。他在製作的時候會散發一個氣場,是『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那旁邊的人就會通靈到,知道他要幹嘛。
FayFluor:了解,所以不是憑空、隨機發生的。
philtrum_1998:它有隨機性,但不是完全沒有邏輯的。通靈可能帶有某種偶然性,但它依然會夾帶著資訊,只是接收者不一定能接收到全部。
我覺得它有自己的邏輯,只是看起來比較模糊而已。
FayFluor:妳為什麼喜歡通靈?
philtrum_1998:因為我希望跟我一起做事的人,是打從心裡也想做這件事,是發自內心地覺得好玩。
我覺得人會在「覺得自己創造出一些東西」的時候更開心。不是交作業的心態,而是「欸,這個想法是我自己想出來的!」那種感覺。
不是被套在一個圈圈之後才在裡面晃,而是自己晃一晃,忽然被圈圈套中的樣子。〖 回目錄 〗
—— 上線下線 ——
FayFluor:我發現有一個情緒好像一直在妳身上,就是妳一直覺得妳「並沒有在那裡」,還沒有真正進入這個領域、站上那個比較高的位置。不只是以前訪問中常常這樣說,我覺得專輯裡面有一句歌詞「試播集變成大製作」,這個心情好像從頭到尾都沒有離開妳。妳同意這件事嗎?為什麼這個情緒會一直在妳身上?
philtrum_1998:我覺得以前有,但現在已經沒有了,因為我已經登入了。
FayFluor:然後呢?
philtrum_1998:但現在的狀況比較像是——就算我登入了一個遊戲,我也不可能整天 24 小時都在玩這個遊戲。我一定有其他的生活,然後其他的生活讓我把這個遊戲玩得更好。
我覺得你剛剛那個問題,比較像是大家對於「音樂人」這個身份的期待,有點回到『要不要以音樂為生』這個問題。我覺得大家對於音樂人會有一個想像,好像他要傾注他的一生、完全奉獻自己,然後他做的所有決定都是因為他是音樂人⋯⋯我今天發了一個貼文、我今天穿了一件衣服都是因為我是音樂人⋯⋯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FayFluor:那妳覺得妳現在的比例是怎麼抓的?妳有多少時間是「登入」在音樂的遊戲裡?
philtrum_1998:登入的時間比較像是根據任務來決定的,比如說最近要演出、要寫歌,就會比較長時間登入。
FayFluor:所以不是固定的頻率,而是看事情來安排?
philtrum_1998:對。因為我同時也在玩其他的遊戲,而且我覺得那些「其他的遊戲」反而佔了更大的比重。因為我會在那些遊戲裡找到核心的東西,帶回來用在音樂上。
FayFluor:妳說的其他遊戲有哪些?
philtrum_1998:比如說強健身體的能力、強健頭腦的能力、寫東西,或是生活本身。
FayFluor:妳今天一直重複提到「生活」這個詞。當妳說「生活」的時候,指的是什麼?
philtrum_1998:「生活」就是要怎麼過每一天。當我說「我現在要去生活了」,通常意思就是:我要去做我自己的事。
FayFluor:譬如說?
philtrum_1998:譬如說看我感興趣的東西、吸收內容、出去散步,或是做一些額外的活動,比如上課、寫一些內容。大多是我一個人做的事,是我在探索新的領域。
還有就是去找別人玩——或是讓別人來找我玩。
FayFluor:回到專輯史前史的部份。雖然妳說那兩年是「訪客模式」,但其實妳那時候也做了很多事。妳怎麼看那段訪客模式的時間?那時候做音樂、跟別人合作,對妳來說是什麼樣的狀態?
philtrum_1998:我覺得訪客模式就是有什麼給什麼、有能力去玩什麼就去玩。當然我會想要唱歌、想表演,但那時候我不會在乎我的能力是不是可以用什麼方法再更進一步,因為重心不在那裡。
FayFluor:這樣的設定好像也可以連到我們上次見面時妳提到的一段話:妳有一段時間「什麼都接」,那段時間為什麼會出現?現在那段時間結束了嗎?
philtrum_1998:我覺得這種狀態都是一段一段的。因為我要點很多技能,不可能同時把一件事情點滿。我會平均發展,所以有時候會想:欸我最近需要補講話技能,那就多去接觸這類內容。但有時候又會覺得:我講太多了,應該要回來想想自己的事,才能⋯⋯
FayFluor:互通有無?
philtrum_1998:對,互通有無。也因為這樣,下一次我才能給別人更好的東西。所以我覺得上線與下線對我來說是必要的。
FayFluor:妳有沒有哪一次在其他地方上線,讓妳特別有啟發?
philtrum_1998:我覺得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有趣點。整體來說,啟發都來自於人——來自這些人在做這些事的方式,他們對待我、對待別人的方式,會讓我看到不同的世界。
FayFluor:比如說?
philtrum_1998:像去年參加文學季的活動。
FayFluor:是因為大家工作方式不同嗎?
philtrum_1998:對,而且大家喜歡用的講法、整體氣氛也都不同。有時候我會覺得滿好玩的。
FayFluor:那就來聊聊文學季。妳去年參加的時候,看到了什麼?
philtrum_1998:我去年參加文學季⋯⋯其實也沒有什麼很明確的感受,但就是那個地方給我一種氣氛。
FayFluor:什麼樣的氣氛?
philtrum_1998:有點像大稻埕的感覺。
FayFluor:大稻埕是什麼感覺?
philtrum_1998:就是一種……很多東西蘊含在裡面的感覺。
比如說,在那個活動的影片裡,大家講話的方式都不是那種「Pop up!我要來講一個超酷的東西給妳聽喔!」的模式。他們比較像是:「我知道很多事,我想過了,我也整理過了,我現在選擇這樣跟妳分享。」
我覺得這種語氣很有意思。但不是每個地方都這樣,有些人還是會選擇直接 pop up。
FayFluor:那妳為什麼喜歡「看別人做什麼」?因為這樣讓妳覺得有趣嗎?妳今天一直在講「有趣」。
philtrum_1998:對啊,我就覺得好玩。別人有點神祕、有點好奇。
FayFluor:那看完之後,這些觀察會對妳造成什麼改變嗎?
philtrum_1998:有時候會。有時候我會覺得:「嗯,那跟我沒關係。」但有時候會覺得:「他們那樣好酷喔,我也想做點什麼。」但不是想變成他們,而是像我剛剛說的——我也想發展自己身上的某一個部份。〖 回目錄 〗
—— 便便 ——
FayFluor:妳喜歡妳的聲音嗎?
philtrum_1998:有時候喜歡啊,有時候覺得很膩。
FayFluor:膩喔?什麼時候會覺得膩?
philtrum_1998:嗯⋯⋯我覺得是我注意到聲音有一些卡關的狀況。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聲音,在他們能百分之百傳達的狀態下都應該是好聽的,可是我們通常不可能到百分之百。
就像腦容量不可能用滿一樣。身為跟自己相處的人,我會很明顯感覺到哪裡沒到,哪裡不是百分之百。一旦我看到那個地方,我就會不喜歡那個聲音。
但這種不喜歡也不是絕對的,它像是一個排序。因為有時候我也會很喜歡我的聲音,比如說我看到它在某個環境裡有影響力,或者它可以跟別人的聲音融合得很好。
像跟 Jerry 一起工作的時候,雖然我沒有特別覺得我表現得很好,或唱得很好,也沒有覺得那個聲音就是我理想中要表達的聲音,可是那個「融合在一起」的感覺讓我很開心。所以喜歡的部份就會被擺到很前面。
但如果是練習、跟自己相處很久的時候,發現某些技巧還是沒辦法百分之百做到,而我又得立刻用到聲音的時候,就會緊張。
FayFluor:這邊剛好可以接回來。妳剛剛提到身體狀態,比如關係不好,或辨識到自己不是百分之百的這些過程,好像妳是樂於跟大家分享的?像妳在 Threads 上常常寫到便祕的事情?
philtrum_1998:也沒有那麼常啦!我也不是每次便便都分享。只是有時候便便的時候會覺得「哇我好喜悅」,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順暢的感覺。
因為「順」這件事在身體上其實很難體會到,可是便便的時候妳可以很具體地感受到那種「我好順喔」的狀態。妳如果說「我生活過得好順」,那要怎麼形容?很抽象。但便便可以,真的就像溜滑梯,有時候是滑水道那種身體的感覺。
FayFluor:妳是一個前後台分得很開的人嗎?
philtrum_1998:我有跟朋友討論過這件事。我覺得是因為不同社群媒體會有不同人格。
像我在 IG 就比較不會過度分享,但在 Threads 上我就會很想過度分享我那天心情怎樣。Facebook 也有一點這個感覺,但 Facebook 跟 Threads 上面的語氣又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是因為,每個社群的氛圍不同,加上我知道誰會看到,所以會不自覺地想呈現某一面。那種人格切換不是主動設定的,而比較像是「我現在見到妳了,我想跟妳分享一些我在想的事」這種情境觸發。
可能連講話的聲音大小聲、情緒起伏也會不同,都是因為那是一個交流的狀態。
FayFluor:妳有偶包嗎?
philtrum_1998:有啊,我有偶包。
FayFluor:妳的偶包會特別在意哪個部份?
philtrum_1998:我覺得,一個人本來就有很多不同的面相。
像我最近在寫介紹專輯的貼文,就發現我在跟不同人合作的過程中,我們互相揭露了彼此很多不同的面向,有些可能我看過,有些我沒看過。這有點像是抽獎,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你遇到這個人的時候,你的反應會是怎樣,可是這些反應都真實存在於你的身體裡面。
我不太確定我是不是想消除前後台的分別,因為我也不確定我有沒有真的的「前後台」。現在會來聊我音樂或跟我深度對話的,多半是我原本就接觸過的人。像你和吹音樂的韻軒,都是原本就認識的人來訪問,所以我還沒有真正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人,然後得扮演某個角色讓他理解我。
不過就像我剛剛說的,那些合作中揭露出不同面向的過程,會讓我覺得說——大家應該理解一個人不是只有一個樣子。
你看到一個人溫柔,可能是因為他為了溫柔對待別人,花了很多力氣,他的內心其實很嚴格。或者像我好了,有些人看到我「不 judge 別人」,會以為我很善良。但其實是因為我不想 judge 自己。
因為當我 judge 別人時,我也會 judge 到自己,那個感覺會讓我很痛。所以這反而是一個超利己的邏輯⋯⋯我的意思是,比方說我不想 judge 別人,是因為我也不想 judge 我自己,這件事情打在我身上會很痛——不是因為我知道我打別人很痛,是因為我知道打出去之後,我也會習慣去打到我自己。
但如果只看表面,就會覺得「喔她好溫柔、想對大家都很好」。像某天我發了一篇貼文寫說「我希望大家都過得很開心,對自己好一點」,很多人留言說「哇妳好善良」什麼的。但其實我最中心的思想只是,如果大家都對自己好的話,就不會用到別人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對別人不好的人,都是自己過得不好,才會對別人不好。
⋯⋯開始講一些毫無理論的數據⋯⋯我自己也是啊,如果我過得不好,我才一直想要去懷疑別人。可是假如說我每天過得都超 happy,我根本就不 care 別人在幹嘛,然後我也就覺得我只想散播快樂,愛,你做得很棒,耶。
FayFluor:OK,好喔,我們居然成功接回專輯名稱。
—— 自介 ——
FayFluor:妳覺得自己是一個永遠有地方可以再發現、再開發的人嗎?妳對自己的認識,目前大概到了哪個程度?
philtrum_1998:我覺得我其實還滿了解我自己的,只是我還沒「看完」我自己。
FayFluor:所以妳是說,已經看見的部份妳都可以理解,只是還沒全部看完?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philtrum_1998:嗯⋯⋯也不是完全這樣。
我覺得——如果把我自己當作一個系統來看,我大致上有理解我的邏輯。就好比說妳在寫一個程式碼,妳知道這個程式大概要怎麼寫,可是它會有很多不同的排列組合。我現在就是知道自己的邏輯是什麼,但我會不斷嘗試新的組合,然後在這個過程中找到新的事情。
當然,也可能會出現新的邏輯,但整體來說,我覺得我對自己是有一個模糊但可操作的邏輯的。
FayFluor:那如果我只給妳大概三句話的篇幅,妳會怎麼描述妳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philtrum_1998:這種我沒辦法回答耶。
FayFluor:為什麼?
philtrum_1998:我最近需要交藝人簡介,然後我就想說:蛤?要怎麼寫啊?不管我怎麼寫,都覺得很難準確表達我到底是誰。
FayFluor:可是妳是有在拍照的人,不是嗎?我覺得這種感覺跟拍照很像啊:框在那裡,我們拍照是選擇框裡面的部份,當然它永遠不可能如肉眼看到那麼全面,但有時候我們還是會想拍那一張照、要拍那一張照。
philtrum_1998:對。那你前幾天有看到林強的自我介紹嗎?
FayFluor:有!
philtrum_1998:我要以他為目標!我覺得他生命經歷有足夠的材料,可以拍出一張普立茲獎等級的照片。
FayFluor:那所以妳最後還是有交藝人簡介嗎?
philtrum_1998:有啦,我交了。
FayFluor:那妳在藝人簡介裡寫了什麼?
philtrum_1998:我寫說:「2025 年 3 月 7 號,我打開了兩張專輯。」〖 回目錄 〗
—— 今天好嗎 ——
FayFluor:好,最後一個區塊來聊聊專輯的比較上位概念好了。不然既然剛剛提到專輯名稱——妳現在會怎麼解釋它?
philtrum_1998:它是我之前寫過的一篇貼文。
FayFluor:我知道,在 IG 上面。
philtrum_1998:對。那時候我正在寫歌,也開始整理各種資料。因為我不是那種先決定好主題再寫歌的人,通常會去蒐集自己以前寫過的東西,那句話當時就讓我有感覺。但我發那篇貼文的時候,其實也沒什麼特別原因,就只是很想講那句話。
FayFluor:「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誰想要 sad。」這句話現在對妳來說,是字面上的意思嗎?
我會這樣問,是因為我看到這個專輯名稱的時候,我最直覺聯想到的是 Peter Su。
philtrum_1998:蛤?為什麼!我要離席了!
FayFluor:因為他有一本書書名是《如果可以簡單,誰想要複雜》啊。我以為妳發那句話是有在諷刺他。
philtrum_1998:真的是字面上的意思啊。如果每天都可以開開心心的,誰會想要難過?
可是,因為講出一句話,會有很不同的反應⋯⋯就是,我覺得當時會把這句話寫下來或是留下來,可能也是因為那篇貼文發了之後,有些人會說對啊要每天 happy,可是有些人就會說如果沒有 sad 就不會認識 happy,然後有些人就會說就是他們每天都很 sad 之類的。
我覺得這很像是「欸你今天過得好嗎」的那種感覺。就是,你在聽到這句話或被問到的時候,你瞬間會想,那我現在是 happy 的嗎?
FayFluor:結果我想到的是 Peter Su⋯⋯我覺得我習慣一直去找每句話的「第二層含義」。但妳會討厭別人這樣嗎?
philtrum_1998:不會啊,我不討厭。因為有一些「第二層含義」是很浪漫的,尤其在文學裡面,那些背後的意義都很浪漫。
但如果是寫歌詞、寫口語內容的話,我會比較想讓對方可以百分之百聽懂我在說什麼。可能是因為我之前有幫別人寫過歌詞,我覺得我經歷過不同階段,也有不同想避免的東西。
像以前會很想避開某些重複詞,後來發現其實那些重複詞也很棒。現在反而會避免用太文學式的語言,因為我覺得要讓人聽懂的話,就要去除那些比較難以理解的部份。
FayFluor:我覺得我們對「文學」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樣。
我對語言的理解是這樣的——語言是流動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建立起來的共識。所謂的「口語」就是那些日常大家比較有共識的語彙系統。而「好的文學」會可以爭奪那個共識,翻轉、挑戰或擴張它。比方說我寫一篇作品,不是單純使用語言,而是想讓某個詞被賦予新的意義、撼動我們原本以為穩定的理解。
但我剛剛聽妳講,妳對「文學」的理解好像比較是在於語句是否帶有「複義」或「歧義」?
philtrum_1998:我不是真的想避開這種歧義性,只是我現在在寫歌詞的時候,會比較在意「這個形式是否讓人能理解」。就像你不會用文言文寫一首要讓大家都聽懂的歌嘛,因為理解的門檻太高了。對我來說,前面提到的「文學」指的是格式或文體上的選擇。
我會在某些場合出現一種隱微的反抗心——有時候會看到一些討論社會議題的貼文,有些人會寫說「我覺得這一切都是什麼什麼結構問題」,用一個社會學的名詞。然後我就會覺得說,如果你想討論一件事情,但是你用的工具是別人聽不懂的工具,那你是要討論什麼?
只要上過一兩堂社會學就會上到,社會學之所以有這麼多學派,是因為他們意識到沒有任何一個理論可以解釋社會上所有事情,但他們依然有找到這種理論的願望。所以,每一個學派都各自消除某些設定、自訂某些前提,以便專心討論核心的價值。就像科學會設定一個無重力的環境,以便驗證某個運動定律——這是有必要的,可是這也表示那些東西不能無條件直接套用在整個社會上面。
每次看到這樣的貼文,我就會覺得那人好沒常識。
FayFluor:好,我明白妳選擇的討論策略了,那妳期待用這個策略來討論什麼?
philtrum_1998:⋯⋯如果要我現在想一個原因⋯⋯我覺得不是我期待我的歌討論什麼,而是⋯⋯
我覺得我期待我講的話可以被聽懂。
FayFluor:欸!我們又繞回來了!妳其實一直在處理「我的話有沒有被聽懂」這件事欸。但妳在訪問過程中好像也不太確定為什麼妳想要被聽懂。我相信我如果現在再問妳一次,妳應該還是不知道答案,對嗎?
philtrum_1998:對⋯⋯但我覺得每個人應該多少都有這個傾向吧。我不知道欸,就是人跟人之間的連結,你會希望了解別人,也希望別人了解你。會希望雙向的交流發生。
我前幾天才跟朋友聊到「願望」這件事,我覺得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願望,可是那個願望不一定能夠被講出來。但你生活中做的很多決定,可能都在圍繞那個願望在發展。
所以可能我現在正在處理的,就是那個願望相關的事情吧。
FayFluor:那專輯這些歌都是基於這種情緒狀態寫出來的嗎?還是它們各自有不同目的?
philtrum_1998:我寫歌的時候沒辦法先設定主題。通常是寫著寫著,某些重要的句子會跑出來,然後我才知道我在寫什麼,再慢慢發展下去。
FayFluor:所以是後來才回頭去理解的?
philtrum_1998:對。而且這張專輯本來也不是說一開始就設定要講什麼。有些人做專輯是一開始就設定好主題,比如「我要講愛」,所以每首歌都圍繞這個主題。但我不是,我是寫完之後才覺得:「那就叫這個名字好了。」
所以整體都是一些很隨機的內容,都是當下的狀態。某些字對我來說當時很重要,我就把它抓住了。就有點像那樣。
FayFluor:但妳一定還是有做一些篩選吧?畢竟每天腦袋都會有很多想法,有些妳會留下來繼續發展。妳覺得那個「留下來」的標準是什麼?
philtrum_1998:我覺得不太像篩選,比較像⋯⋯如果你在聽一場演講,你沒特別做筆記,但過一段時間你還是會想起某一段話。就是那種感覺。〖 回目錄 〗
—— 通靈 III ——
FayFluor:我覺得這張專輯裡其實是有一種聲響上的共性,那這個聲響的共性是怎麼找出來的?
philtrum_1998:其實我沒有特別去找耶。但我覺得這還是跟「暗示」有關吧,就是大家看到我,就會想要這樣做。
FayFluor:那這個「暗示」是妳主動釋放的嗎?像妳剛說的那種「傳染」?
philtrum_1998:我覺得⋯⋯是我在這兩張都發完之後,才比較真正意識到「傳染」這件事。
尤其是在表演上——如果你想讓觀眾一起拍手或動起來,你不能直接說「給我站起來!」你一定是用某一種方式去唱,用一種態度去帶動氣氛。或者像你打了一個哈欠,對方也會跟著哈欠。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那就是一種傳染啊。他看到你身體那樣,他會想模仿,那種「舒展開來」的感覺和心情。
FayFluor:我發現妳真的很綿密地在感覺這個世界。妳會很容易累嗎?對,妳之前說過妳很容易累。
philtrum_1998:對⋯⋯
FayFluor:好,所以原來妳把精神都用在這裡——好,真好。〖 回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