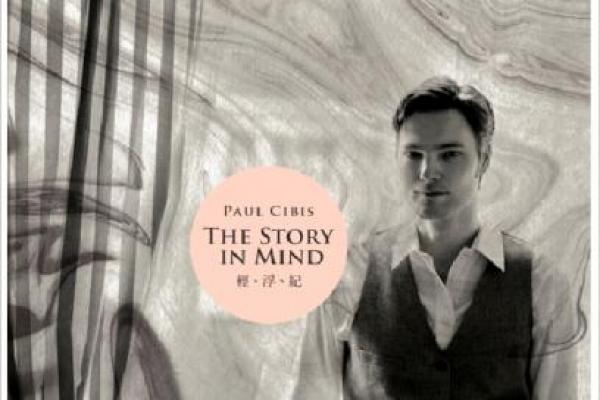將赤裸暴力砸到臉上──「撲面戲劇」(一):莎拉.肯恩,一個殘酷而美麗的名字
關於劇場,我們很難說創作者想要在台上創造中什麼光景,是藝術家自己的內心世界透過舞台、道具、音效與演員的具體化表象,還是如其所是的、具有靈魂的情節本身的自由發展?而在其中上演的劇碼究竟需要符合什麼藝術上的期待與訴求,是撫慰人心、道德教育、如實的呈現真實世界,還是創造只有夢境中才看得見的華麗景象來娛樂感官?
關於看戲,我們很難說觀者進入戲院想要得到的是什麼東西,有些人想看見現實中沒有的事物,有些人則希望自己透過藝術更看清現實的精髓,也有些人逃離生活走進戲劇院,在中性而容納一切的黑色空間中暫時忘記自己的皮膚與身體,而將精神透過雙眼全部灌注在台上發生的一切,劇終人散才肯回到現實。
在莎拉.肯恩(Sarah Kane)短暫的 28 年人生中,她寫了五個劇場劇本、一個電影短片劇本,每一個劇本都有一個精準的訴求,即以最極端的方式在觀眾面前呈現人類的痛苦、世間的惡、為善的渺小希望和在這之間擺盪的靈魂。做為觀眾的我們光是讀她的劇本,那些血與哭聲、暴力與性和對救贖的渴望就能生動的呈現在眼前與心中,而別誤會,觀眾在她的劇中所得到的絕不是救贖與教條。

英國劇評 Aleks Sierz 在他的著作《 In-Yer-Face Theatre: British Drama Today》中,總結了英國 90 年代活躍的新興藝術家之創作型態,以「In-Yer-Face」--撲面戲劇--來代表這個時期劇本中的暴力與赤裸人性的展現,最主要的創作者就包括 Mark Ravenhill、Anthony Neilson 跟莎拉肯恩,他們的作品絲毫不將醜陋的人性加以包裝,你可以在台上看見最低俗的、嚇人的、挑戰感官極限的情節被「砸到你臉上」,其中莎拉肯恩的劇本又最具悲劇色彩。
身為一個觀眾,我們不禁要問,將日常看不見的、深藏靈魂深處的黑暗物質召喚出來、放在台上演出,除了讓觀者接下來心情不好一整天或一整個月以外,究竟有什麼意義?而且在呈現了如此使人灰心喪志的情節後還不夠,在結局還需要有一個「皆大悲傷」的最低點,難道人類在世界中竟然真的一點希望都沒有嗎?
在回答問題之前,我們必須看看撲面戲劇產生的時代,當時英國社會的階級意識與性別刻板已經達到某種臨界點,而劇場藝術的內容更趨向千篇一律,莎拉肯恩以及其他年輕一代劇作家的出現打破了這個僵化的平衡,用不合邏輯、場景跳耀的劇本將看似不相關的事件連結在一起,在當時遭到很多衛道人士的批評。

也許沒有這一波打破平衡的劇作,英國的劇場就會繼續僵化到更無救的地步,而這些作品不只可以做出時代的閱讀,還可以繼續跟現代社會剁更多樣化形式的「暴力」與「扭曲」做連結。從二戰走出的世界看似逐漸趨向更和平的狀態,但事實上那些從人類存在時即創生的惡與不幸一直伴隨著我們,以更隱晦卻強度絲毫不減的方式持續發生。
也許最後莎拉.肯恩自己也不相信除了她筆下的世界以外,真實的世界還有另一個美好的可能,也許這是為什麼她在長年的憂鬱下,在醫院的病房內用鞋帶上吊自殺。她所面對的除了在世界中感知道的惡,還有獨自對抗的、內心對自我的敵意和懷疑,但這不代表她的寫作中只有醜陋的東西,透過醜陋,我們看見人類情感的真實面向,在這真實面向中,美好的可能性被凸顯出來,即使渺小卻持續存在。
下一篇文章將介紹莎拉.肯恩的成名作《驚爆》(Blasted),並以劇作本身直接探討「撲面戲劇」的獨特之處,以及為什麼邪惡之物卻正是帶給我們希望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