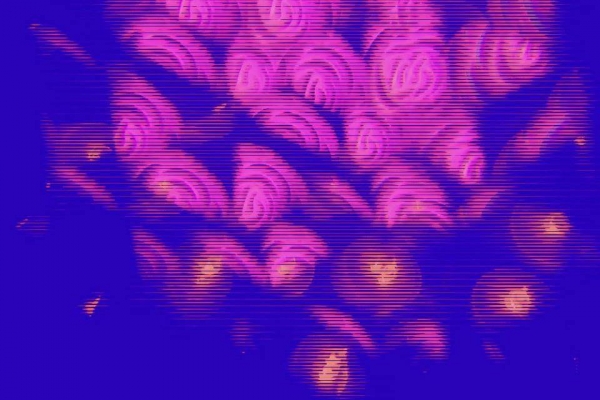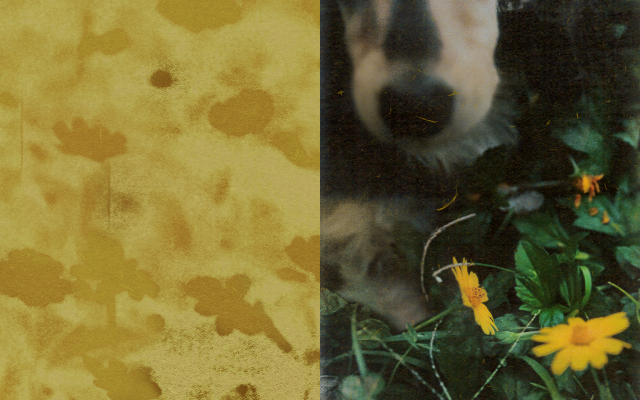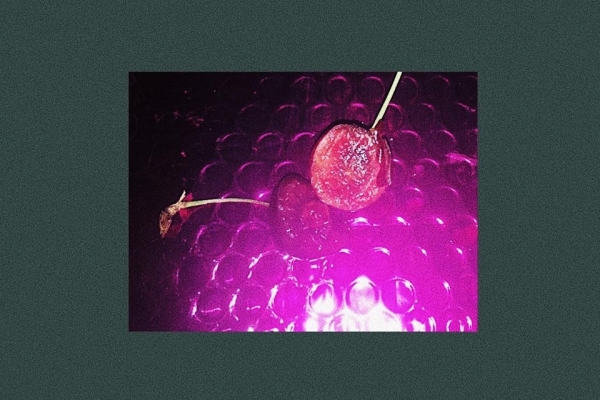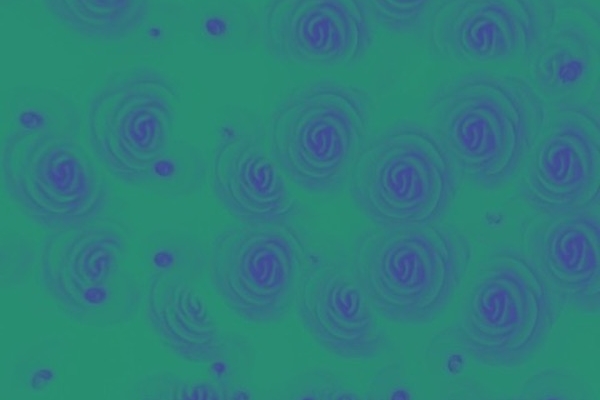早洩的塵世樂園|地獄一季.生魚
在這個世界中,他們教導我們,女人是弱勢的。
有的時候,我覺得我很邪惡,而且不是因為誰辜負了我,而是我的本性。我想一巴掌向她打過去,反正她也求之不得吧?但最後,我發現無論我如何以為這是我的「本性」,我本是受到了他人的影響。
「有一天,我的陽具走丟了。」這是一個男人的小說的第一個句子,一個開口就提到陽具的男人,到底在想什麼呢?我皺著眉讀下去,想試著了解她,為了了解她,我做了許多她不知道的事,但我又不斷暗示我做了許多事——於是,她都知道了,但是,只讓她離我更遙遠。
安格樂提議想吃日本料理,魚或涮涮鍋。她向來不是問什麼都說隨意的女生,但對吃的也不算太堅持,突然提出這麼明確的選項,我有點驚訝。
這麼熱的天氣,突然更想吃點養生清淡的、水裡游的。她說。
我們相約七點半見面。她如願以償點了鯛魚鍋,我點了豬肉鍋,又合點了幾種餃子丸子和蔬菜。有些無語,我們默默吃著,各自涮了塊魚和豬給對方,食物很新鮮,話題卻活潑不起來。
距離上次與她見面,已是約一年前了。那時她的頭髮還沒這樣長,那時的我還沒找到這份工作。
都還順利嗎?她說。順利啊,我說。我開始疑惑昨晚她怎會答應我的邀約,我昨晚是那樣地情緒化,若是一年多前,面對這樣的我,她唯恐避之不及。今日的她看上去和過去沒有太大不同,似乎較為安穩,過去的她總是些微躁鬱,而我反而總是那個冷靜的人。
— 安格樂,我快不行了,見個面好嗎?
好像角色交換、倒置,過去的我,總是在她憤怒或困惑之時,守住我安慰包容的位置,好像男人需要容忍情緒化的女友,是一種規矩和常識。昨晚的我做出意想不到的舉動,我從未想過我會發出這樣的求救訊號。而今日的她是那樣安靜,也並未表現出擔心的神情,令我感到莫名寬慰。
啊,安格樂,今天我想變成妳。
我們交換吃了一塊豬和魚、魚和豬。
我幻想今夜我獨自醒來時,我已變做女身,就像是電影和漫畫中常見的劇情,我變成了安格樂。不,不對,我是想變成安格樂,而不是取用她的身體,我想以她的精神來思考、生活。
我們又交換吃了一塊魚和豬、豬和魚。生鮮用滾熱的湯燙熟,由紅變白。
不過呢,安格樂,妳應該不可能想變成我吧?

※ ※ ※
許多人都說要自己去掌握生活,不應該藉口拖延不去改變。但如果你一生下來,就如裝錯身體、身懷異物,如站在一口地獄般的深井,那該怎麼辦?我就是如此悲觀。我不是因為愛慕男性而想變成女身,而是痛恨身為男性。我非想成為女性,而是不得不寧可交換,若可以什麼都不要而成為無,我就想成為無。
我想成為無。我不願像現在,一身濕漉漉地,站在地獄裡。
女身有多少生來的限制,不需他人來告訴我。如此痛恨現有的男身,或許就是痛恨自我吧。
地獄如滾燙深水,我這一塊肉軀,正在受折磨。
地獄可能是燦爛的,我就是行屍走肉。
我和安格樂在學校的最後幾年相識,我已記不得我是如何「認定」我想追求這個女孩,在不知不覺中,我的訊息欄、信箱充斥著與這個女孩交換的信息,我因為她,聽了許多不會聽的歌、看了許多不會看的電影。在甚早安格樂就和我表明她並不想談戀愛,但是因為她的坦率、大膽,貌似不可一世又會顯露出脆弱的時刻,我如一個一般的男孩子,繼續待在她身邊守候,彷彿等待時機。但也因為在那個不知所謂的年歲中,她對我真誠,可說是我唯一的朋友。
唯一的朋友,唯一讓我顯露出真實的人。
後來我們交往過,也分開過,我知道她渴望的可能不是我,我不知道我渴望什麼。
— 一童,我們之間還有隔閡嗎?
她曾經這樣問我,我知道她指的不是我們之間的愛情。我怨恨她,但同時亦紅了眼眶。
與安格樂的相處,是我活生生在生活的唯一證明。在我每日工作、吃飯、睡覺、自慰之外,唯一的情感。這天晚上,我回到我的租屋處,一個人度過夜晚。我像平常一樣用著電腦,看了一下明日的工作行程,準備睡去。在一片黑暗中,我在床上盯著手機螢幕,像例行公事般,滑動螢幕最後一次。意外地看見安格樂在她的 instagram 上新增了一張照片。照片中霓虹招牌閃爍,看不太清楚。過了一會才發現,那是我們剛剛吃的火鍋店的招牌,火鍋店店名是「阿法龍」。
這張照片會有多少人看見呢?我看見了,我想,她應該已經知道了吧。
※ ※ ※
有人和我說,甩了這個 Drama Queen 是我做得最正確的決定;還有人說,可能她要的就是男人用 XX 去關照她,我想得太多了。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的。我是感覺被遺棄了。
在妳給我的身體語言中,我曾以為我是被祝福賦予的;但是,我誤會了,如今我仍像苦苦哀求「再一下就好」的小孩。妳從接受到拒絕,那身體的表現是那樣微妙,我無從請妳再多留一會。
再好的成績、再多的證書、再多的工作經歷,都沒有意義。我是一個二手品。
對一個平庸的人來說,偶爾難以克制地被不平庸的人吸引,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模仿。
在我小時候,有一陣子很熱衷於躲在廁所手淫。因為母親不准我鎖房門,我只能這麼做,我越做越多、越做越順手,母親沒發現,我就彷彿希望她發現似地,甚至在吃飯中途至廁所手淫。
我試著對著雜誌、也試著純幻想,也想過母親與妹妹。
終於有一天,她只是淡淡地和我說,「別再這麼做了吧。」
那時候我想著,我想要的就是這樣嗎?我想要的,就是這麼一句簡短的羞辱,甚至稱不上是羞辱,我是重要的嗎?或者,我只是一具履行義務的機器,每日被強迫生活。羞辱應該是有顏色的,是鮮豔的紅;她的話語卻是慘白的,如她的人。
這天,那個男人在他的網誌上,新增了一篇短短的詩。
你是超自然
超於世俗的天真
超於
我一切的認知
在萬物滅絕之時
將要拯救我
關掉
過冷的
冷氣
打開窗戶
給我一杯黑咖啡
你是超自然
你是異象
控制我的意識
意圖
讓我自由
我讀了以後,覺得很難受。我不想和這個男人有相同的情感,但我在閱讀時,確實以為他說的是我心中的聲音。
我讀了這個男人的其他文章,讀著讀著,天快亮了。我突然覺得有點安慰,好像身體的某部分也被擁抱或溶解,安格樂的身影在我眼前出現,輕輕地笑了。
下一篇:地獄二季.水果派
【羔子】
台北人。喜歡從男孩的視角來寫,也寫女、慾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