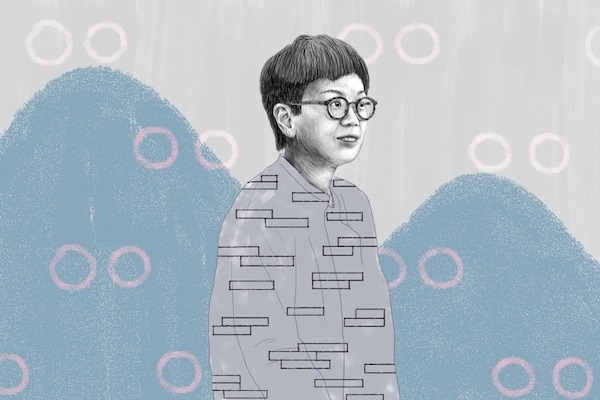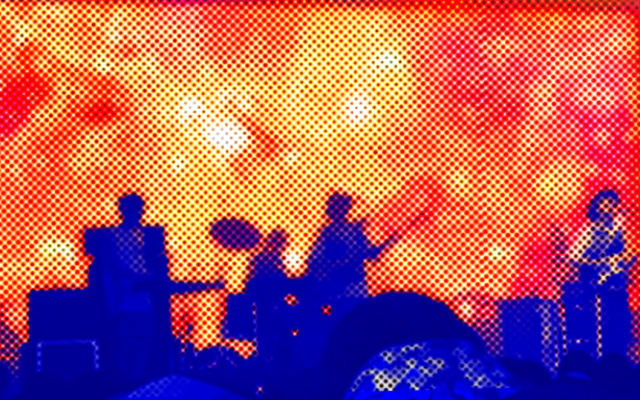飄洋過海來拼酒,專訪落日飛車:前進世界頂尖的競技場
有次參加朋友婚禮,居然看見落日飛車特別錄給新人的 VCR。原來新人就是在飛車演唱會求婚成功,獲贈超浪漫的婚禮樂隊表演乙支。採訪這天,我開玩笑說那可以認真經營婚禮場喔,國國說其實很多副業都可以啦:「也可以去賣房子、房地產。我很適合當業務啊,這個避震!KPR 係數什麼什麼的,很會哦。」
為不負此名,今日我們來到台北一處名為波士頓的理髮廳,見證新・偶像團體斜槓理髮師傅的誕生。豪氣寫成的波士頓三字有又台又洋的潮感,很適合剛回來的飛車一行人。國國、尊龍、弘禮、浩庭、小干、鳥人在此刀起刀落,輪流躺下彼此宰割。
趁阿姨梳油頭,六人也梳理自己走向世界這條心路。馬世芳在廣播節目「耳朵借我」裡提到:「我以為,落日飛車這兩年征戰世界的經歷,累積的心法,意義不下於十多年前五月天率先建立了中國大型巡演的支援系統,這是替台灣同輩音樂人打開了另一條完全不一樣的路線。」
.jpg)
左起:尊龍、浩庭(梳完油頭後)、弘禮、小干、鳥人(背對)、國國。
2018 尾聲總結,飛車全球破百場巡迴,從中國各地到東京、首爾、雅加達都有他們專場完售的風光;美國則走過紐約、費城、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舊金山等大城,歐洲巡迴更跨足西葡德法英五國,簡直闢出自己的聯外道路。BIOS monthly 本期封面「#創作者的島外行動」有請飛車,以國國為首,聊向外的跌跌撞撞與收穫。
華人小圈圈之外
看似壯闊的歐美之行,國國說起來還是有點頭痛:「成本超級高,尤其是美國,簽證超貴。」六個人要上台,兩個禮拜的表演簽證約莫要台幣十八萬,還不含經紀人和 PA:「就這個簽證,你幾乎不可能賺得回來。不可能。」他滔滔不絕翻出數字,感覺真的是滿適合當業務:「除非你找得到很大的音樂節,譬如說 Coachella,連唱最爛時間的台 show fee 都三萬美金,那這樣就台幣一百萬。如果沒有到那個等級以前,你去美國巡迴基本上沒有市場可言。」
但他們還是決定繼續去,希望每次去票房就好一點,最終能引起音樂節注意。「但是離到那一步,還有一段路要走。」他們勉強撐著,等待前行的可能:「這是世界頂尖的競技場,如果可以打開一個知名度,你就可以打開全球。這是一個比較策略性思考的決策。」
土炮開路,只能邊走邊學。我好奇團員們在這段時間淬煉出什麼學習,弘禮想了一下卻說:「有一個滿屌的⋯⋯學到怎麼出國一個月,可是只帶一個包包。」眾人滿臉問號他只好自我辯護,說這真的滿屌的好嗎,包包在手隨時可以出發。我們問說不帶行李箱嗎?他回:「行李箱的位置要讓給樂器、周邊商品,或兩個人用一個啊。」好吧,看來還是有些偉大的情操。
此話引出尊龍誠實發言:「後來也有學,怎麼樣一件 T-shirt 可以維持三天都不會臭。」此心法東南亞無效但歐美尚可一試:「洗澡的時候可以把髒衣服掛著一起洗,蒸一下,水蒸氣會把那個髒污稍微帶走,隔天會變比較香。」頓時啟動飛車的生活智慧王開關,小干也開始聊異國下廚。好餓。
|
|
|
|
|
認真來說,至少他們拓展了對於歐美音樂產業的認識。國國拉回主線:「歐美的困難是他們產業分工很細,你要辦一場 show 至少會經過兩到三個仲介單位。」理想的狀況下應會有專門的經紀公司(agency)把團的名字丟出去各地,看哪些當地的宣傳(local promoter)有興趣,最後統整所有演出資訊給樂團。但像這次飛車沒有經紀,就要自己聯繫每一個城市的宣傳人員,從租賃樂器到交通大小事,通通 e-mail 來回。
「就是會慢慢認識這些產業鍊。但最大的困難是,台灣很少有人在這些產業鏈裡工作。」現有的華人市場,以邀請五月天、陳奕迅等天王天團單刀直攻華人社群的商業模式最為常見,宣傳管道相對固定。但像飛車這樣的團,很需要走出華人小圈圈:「所以去就真的是,戰爭迷霧,都是霧。然後你要自己去試,他們單位這麼多,樂風也有分,你要怎麼找到最適合的合作單位,這些都需要經驗、時間,都是困難。」
也有經歷困難才可以得到的收穫。國國說,去了歐美才發現有意外受眾:「結束巡迴後華僑給我們的評價真的超~好,就會說,你們真的超酷這樣。」
那是努力衝破華人直銷管道的報償。落日飛車的演唱會現場裡有不同背景、不同族群的朋友共存:「很多華僑看到他的同學跟他一起來看,他們會覺得說,他們的 hometown 來了一個連白人都會聽的團,真是我們的驕傲。」
|
|
愛情導師與爆紅款
飛車在歐美主打迷幻團市場,回到人親土親的亞洲卻成為史上最強婚禮伴奏(開玩笑的),這點國國自己也始料未及:「真的是沒有預設到,但可能就因為我們紅的歌是情歌,就被定義是唱西洋情歌的老團。」中國江湖有此一說:聽落日飛車,睡到心上人。如此金句點出聽眾樣貌:「我們的 TA 大部分都是 95 後,甚至有些是 00 都有。然後都是對愛情很渴望的。」
2009 年落日飛車初現身,是以迷幻電子音樂為基底的雙人組合。草創期玩實驗音樂,後來走向搖滾,樂迷們心中珍藏的《Bossa Nova》向英美六七〇年代搖滾取經,融合藍調、龐克、爵士元素。休團三年後,2015 年更改為接近現在的團員編制,次年發行 EP《Jinji Kikko》向女孩述情,口碑逐漸發酵,也逐漸拓展海外市場。今年度的《Cassa Nova》述說主角卡薩諾瓦的成長,樂風上常被歸類為 AOR(Adult Oriented Rock,成人抒情搖滾)。
儘管曾有過各種面貌,從成員們玩的其他團如 Forests、南瓜妮歌迷俱樂部也可見得不同類型音樂的吸收,但「落日飛車=懷孕搖滾」等式深植人心。國國說文解字:懷孕搖滾,顧名思義聽了容易懷孕喔:「很多情侶喜歡來看我們演出,一群追求愛情的少男少女們,一起賀爾蒙噴發。大家就是來聽那幾首他們超喜歡的情歌,跟旁邊的人擁吻。」
出於好奇,我去中國問答平台知乎輸入落日飛車,瞬間看到一則發問「当一个男生让你听落日飞车的 my jinji 是什么意思?」唉,好青春,九把刀式那種悸動都在這裡。
挾著這樣的浪漫情懷,《Jinji Kikko》發酵後中國觀眾回應熱烈,出現各種充滿青春愛戀的回憶書寫。從小眾完售到黃牛拋售,知乎上另一則「落日飞车是如何爆红的?」或許也反應出他們在中國的聲勢。講起這點大家其實有點難為情:「在那裡很不一樣的,我們比較像偶像團隊。這點是比較難消化⋯⋯我們在台上做什麼,觀眾好像不太關心,但會很 care 一定要跟你拍到照或簽名。」
這群混地社、獨立音樂界長大的男孩們,至今對於偶像光環和愛心光波還有點不習慣。尊龍說:「那個狀況你就要去⋯⋯譬如說對他們笑啊,幫他們簽名啊,就是你⋯⋯(思考貌)不要像之前那樣不理人,這是最大的改變吧。」第一次發現要簽名簽一兩個小時,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是誰。小干在一旁悠悠說:「有時候簽名,寫字寫到眼睛都看不到⋯⋯」
|
|
當周遭太多聲音,飛車的功課回到自己身上。國國說甚至寫歌時,因為知道聽眾都喜歡情歌,多少也會受到影響:「但這就是我個人的挑戰:怎麼樣在這些環境影響中,還是可以找到一個平衡、還是要聽自己內部的聲音。其實最努力是怎麼樣不改變你自己。」
尊龍大師現在則頗有禪悟:「試著面對觀眾時要保持自己的能量,不要讓自己被影響太大。其實到頭來是這樣,也不是我去影響別人。」
如果不確定怎樣才對,國國說:「反正現在狀況就是,世界真的很大,什麼音樂都有人聽。我覺得,音樂只要是對得起自己的那種好,就好了。沒有一定要做到怎樣、真的『好』是什麼、那個好要怎麼定義?標準就是,自己覺得好就好了。不要騙自己。」
被了解之必要,盤撋之必要
說了各種泥濘與困惑,也聊一些振奮人心的事。浩庭印象最深刻的是與歐洲聽眾相知:「他們就是單純來聽音樂,很在乎音樂上細節的處理。」弘禮也有這種共感:「他們會跟你處在比較靠近的頻率,感覺到你現在有想要幹嘛。你可能做了一個很小的事情,換段落或什麼,只是小小的變化,你會知道有人在吆喝。那一瞬間——哇!」
會感覺比較興奮嗎?全部人秒答:「很爽啊!!!」弘禮繼續說:「因為你知道說,欸!那邊有人發現~~~然後你就會覺得做這個事很有趣,不會每天都一樣,反正沒人在乎啊。」
國國分析:「音樂對他們來說就是很生活的事,不會覺得因為我喜歡音樂就比較酷或比較屌,但聽到音樂就超級嗨。我們亞洲人會覺得聽音樂好像是個品味鑑賞大會⋯⋯聽音樂的習慣就是比較『聰明』,要知道這個樂手厲不厲害或是他到底演了什麼,但歐美人是不太 care 的。就他們可能喝得超醉,隔天也忘了到底聽了什麼。」
讓人興奮的還有相遇。鳥人分享最難忘的事,是遇到和飛車配置一樣、樂風相近的團 Paul Cherry。兩團彼此台上台下觀察了一番,最後由鳥人致贈伴手禮:三角鐵一個。他補充:「因為那個快要壞掉了⋯⋯」看大家邊笑歪邊譴責,他又改口:「沒有啦,那個還是可以用啦,他好像很喜歡我就⋯⋯反正我還有一個。」
除了 Paul Cherry,飛車一路結交 The Black Skirts、Boy Pablo、Phum Viphurit 等氣味相近的友團,偶爾互相客場出演。HYUKOH 的吳赫在 The Black Skirts 鼓吹下來看表演,一結束就來後台打招呼,約了台灣見。有些感情走入下一階段,像今年飛車就和日本獨立樂團 Siamese Cats 推出黑膠。國國想了想,合作上要有火花,都得從私交開始。而私交的開始,一定都源於音樂上的欣賞,聽起來是互相欣賞 → 彼此了解 → 在一起,非常健康美好的關係呢,不愧是愛情導師。
而這些交際,的確是在外走跳的重要技能:「要有人會盤撋(puânn-nuá)啊!一個團裡一定要有人會去交朋友,所以外語能力要 OK。」飛車直到 2018 年才有幫忙盤(ㄍㄢ)撋(ㄅㄟ)的經紀人與助理,在那之前,業務國國理所當然是交際第一線。一起喝酒,那才是正經事:「雖然說和音樂沒有直接關係,但音樂其實就是玩人啊!你一定要認識人,你才會知道音樂還有更多的可能性。」
接著就是各種 One night in 北京/我爆吐到不行的故事時間。聽起來經紀人瑪莉和國國都是一條命式的無尊嚴喝法。他們抖出弘禮更猛的絕招,簡直自殺式攻擊。
國國:「他都這樣。今天要出來喝,就是要有人喝倒。不是我倒就是你倒。」
瑪莉:「他有個技巧是三秒喝完啤酒,可以把喉嚨打開,直接把酒倒進去 。」
國國:「對!可以瞬間倒完。到現在他就這樣全世界和大家拼酒,沒輸過。真的是全世界。」
我們正驚嘆弘禮的才華(?),瑪莉才想到:「啊,有喝輸過一個人啦。」
可惜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打遍天下只輸宋冬野。國國抱著幫隊友說話的情誼:「他真的太能喝了。他沒辦法喝快,但他真的是千杯不醉 。長跑來看是輸宋冬野,但我們短跑很快,大家會覺得說,幹!飛車能喝,也是盤撋一部分。」
.jpg)
波士頓老闆娘表示不想露臉很怕走紅(客人已經排到東門捷運站了拍勢),於是以此特效處理。
唱英文歌的台灣人
說完各種歡笑憂傷,清醒爛醉,回歸到最一開始的問題:為什麼飛車會這麼積極往外發展?和許多人的猜測相反,國國說,其實這反而是在創作後端的考量:「我會覺得唱英文歌的團本身就應該要有企圖心,更離開華語市場一點。這就是一個滿核心的動能。」也就是說,並不是為了往外才以英文創作,是因為要唱英文,所以該往外發展。
剛卸下安溥「煉雲」演唱會樂團團長之職的國國,經歷過台灣許多重要的音樂場景。但走過千山萬水,最初創作時他本能追逐的卻是一種空白:「唱英文的時候我腦袋比較不需要去想到底是要講什麼事情。可能也不是完全都沒在想,而是自然而然唱出一些字,很像是我潛意識裡面想說的話。」
「其實我也試著寫過中文歌詞,可是就覺得唱起來很彆扭⋯⋯唱英文歌我就有一種,『我這個人被真空了』的感覺,很像不是曾國宏在唱歌,很沒有包袱,要唱什麼就唱什麼。想唱一個愛情故事也好、想唱一個簡單的生活議題也好,但我都覺得很沒有負擔。」所謂的沒有負擔,也是讓自己擺脫華文歌詞前行者那些輝煌:「讓自己感覺是一個沒有歷史的人在唱歌。」
這種「輕」也反映在音樂性上。國國在創作詞曲時也習慣留點位置:「我很希望平均調配詞曲、編曲、樂團的演出狀態,就各 33% 這樣。有些人聽我們錄音室作品就會覺得 vocal 比較小聲,但我還是希望音樂表現上是個整體的聆聽經驗。」
那還是回歸到他自己的狀態:「可能很多原因,像我對自己歌聲也沒有很有自信,所以我就會希望稍微退一點。然後我也沒有希望大家很注意聽我到底在講什麼、歌到底在唱什麼⋯⋯我就覺得英文詞給我一個足夠模糊的空間。」
讓他自己也有點意外的是,國國式英文反而吸引了母語人士。舉凡〈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和〈Almost Mature〉:「他們覺得我們的歌詞比他們的英文有趣。或許文法有點小怪,但完全不影響他們認知一件事情。」被說英文 funny 難道不會心裡有疙瘩?國國很快回:「不會欸。我會覺得,我做這件事情的意義好像又多了一層。雖然是唱英文歌,但我就完全是個台灣人,從小在這裡長大。我個人的意識、我對於美這件事情怎麼想像,都是這個環境給我的。」
順從逃離的渴望,反而打造出台洋混血的新品種:「我選擇用英文創作,讓英文母語創作者覺得我給了一個新東西。那我就覺得,我在這個世界巨大的齒輪中,好像還是有扮演一個小小的角色。就會覺得這樣做很值得,有一點意義這樣。」
|
|
半熟的我們,永遠在路上
我們聊島外這麼久,但國國思考這整個行動的關鍵必得回到根源。他強調:「走出台灣最重要的事情,其實是因為台灣有給我們足夠的養份,這件事是必然的。」
出生成長於台北,即使用英文讓自己走向「沒有歷史」,但我們依然可以從音樂裡找到屬於他與台北的私密書寫。專輯第一首歌〈Almost Mature〉到最後一首〈10-Year-Taipei (Matured 17')〉,十年沖刷讓主角卡薩諾瓦成熟,也是《Cassa Nova》中文名稱「半熟王子」的由來;藉由卡薩諾瓦對於愛情的疾呼和成長思考,寫出他在台北度過的半熟態。
這種半熟狀態,也可以解釋為他看台北的載浮載沉。國國認為,對一個創作者來說台北很矛盾:「生活很安逸,大家可能過得不優渥,但絕對也不困難。」對比生存壓力巨大的倫敦、紐約,藝術家們得要咬著牙去嘗試,一兩年時間不成功,就去找個妥當賺錢的工作。
「但在台北找慰藉太簡單了。你要從這個不足撤退出來,太容易了。反而在追尋藝術創作的時候就會差那麼臨門一腳,沒有真的把它做出來。」很多人覺得這是一個好事,但他更多是擔憂:「其實說是一個限制,就是像溫水煮青蛙一樣,你反而沒有辦法真的跳出這個鍋裡。只要有個藝術的夢想,很容易被淹沒在這個安逸的台北城市裡面。」
I will be gone.
I will be gone.
I won't be long,
I don't belong.
I'm dreaming home,
Oh I'm getting los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en the dream is coming.
——〈10-Year-Taipei (Matured 17')〉
我以為他要檢討眾人不夠努力,但其實他並不覺得這罪大惡極:「我就覺得這就很台北。全世界可能真的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這樣支撐一個藝術家,又讓他有某種程度的物質享受。所以我也是很期許,飛車可以把這種狀態表現在我們的歌曲裡,雖然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這種矛盾就是他眼中的特色:「在台北就是你有這個意念,但你會永遠處在一個實踐的路上。你會永遠在這麼做,但你不會做出來。」
半熟王子,或許他們的出走,是想以看似共通的語言包藏那還不敢說得太明白的私密心聲,以走向世界的壯志遮掩還在路上的不安。先乾一杯,成熟的路上有浪漫有現實,他們持續在面對。
|
|
|
|
【封面故事 2018 輯六】 #創作者的島外行動
「嶄新的經驗,構成了人類靈魂的核心。」——《阿拉斯加之死》
島嶼起家的創作者們,以向內深掘的精神向外探尋。他們用藝術與文化編織新地圖,抹除地域界限,從太平洋的風出發,讓小島的願望吹到遠方。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