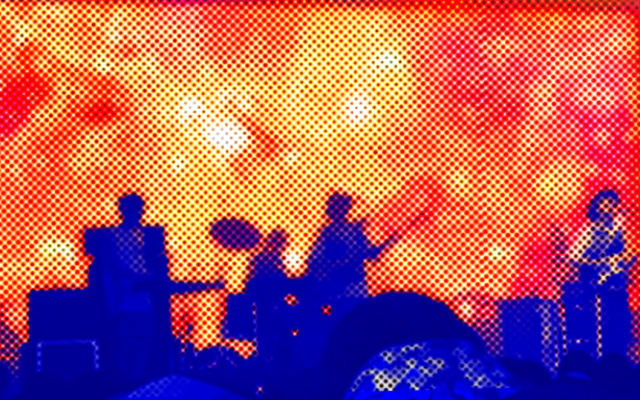新導演的幾道難題,之四:場面調度好了,那音樂呢?(上)
30 多年來,台灣沒有電影工業。沒有電影工業意味沒有多元類型,沒有多元類型代表題材限縮,導致電影在稀缺資源下自然傾向文本上的思想表述、主創者的個人實踐,其它技術部門能省則省,所以我們當然不重視電影配樂。時至今日,儘管視聽習慣早已大幅轉變,但很多人包括從業者,都還認為音樂只是電影的邊邊角角、可有可無,忽略了電影做為所有藝術的結合體,若是將配樂排除在外,豈不削弱了感染力?場面需要調度,音樂又何嘗不是,本次講座邀來金馬獎提名電影配樂王希文及導演柯貞年,從配樂工具論、片型結合論,以及實際工作流程談起,兩位也將導聆近期優異的電影配樂。
搞懂配樂之前,當然要先聽音樂,一個人聽的歌最能洩露他精神層面的眉角,所以今晚就得從個人愛歌開始聊。柯貞年分享日本數學後搖團 Toe、英國樂團 Tindersticks 和陶喆九〇年代金曲〈沙灘〉;王希文則因擔任不少音樂獎項評審,對台灣本地創作人讚譽有加,介紹了幾組他近期欣賞的樂團,「農村武裝青年比較關懷社會議題,編制就是吉他、percussion 跟大提琴,很有生命力;落日飛車是比較復古的 Rock’n’Roll,一聽滿像外國團,全部唱英文歌詞,tone 很不像台灣,有種類比的質感、天真無憂無慮的感覺;另外還有獅子吼和棋盤上的空格,因為他們做自己想做的事、反映創作當下的心境,所以音樂比較有畫面。」既然音樂端不乏人才,那問題出在哪?王希文直言,若市場上淨是校園戀愛或賀歲片,就不可能有這種音樂出現,台灣缺乏撐得起這些特殊音樂的電影題材,甚至是劇情、表演、美術,當片子沒有類型,只是很中性、主流,音樂就很難做特殊的設計。
兩位的熟識起因於短片《溺境》,柯貞年不諱言第一次跟王希文開會前,只是抱著試水溫的心態,因為很怕請不起他,「通常導演找配樂,一定會問他看完片子有什麼感覺?音樂想像成什麼風格?最直接就是講出某部片的配樂,他講出來後我覺得就是他了!我找到了!我們竟然想到同一部片,那他一定知道我想要的,觀念一致溝通起來比較順利。我一開始以為是這樣啦。」王希文解釋工作流程,「討論完對音樂的想法,就要決定哪些段落要用音樂和每段的進出,然後逐段開始工作;但也有導演都不管,全部丟給配樂,做完就用;也有導演懂音樂,所以參與得比較細,希望到現場看你每一段怎麼弄。基本上就是一起討論每段的進出點和內容,這是原創配樂的大原則。」另一種常見的狀況是使用現成品,可能是劇本裡已經註明特定歌曲,或導演會問配樂適合用什麼歌,再去找版權,「也有特例像伍迪艾倫和中島哲也,他們會找自己喜歡的音樂,在編劇跟分鏡時想好要用哪些,像《告白》都不是做原創配樂、《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裡面很多歌舞段落,我認為他從一開始都已經想好了,所以會產生很強烈的個人風格。但多數的狀況是剛剛說的逐段討論,接著就是一個人在電腦前工作,寄出去、被打槍、修改、不斷往前的過程。」

(左:王希文 / 右:柯貞年)
柯貞年為了知己知彼,合作時就把王希文做過的所有長片配樂都找來聽,「了解他的創作緣由就知道要怎麼防備他,因為不管再怎麼熟,即使我們方向一致,但第一次聽到成品還是會深呼吸一下,想著該怎麼跟他說『沒有不好,可是跟我想像中不一樣』,比如我希望在懸疑當中有點哀傷,希文就會說怎麼可以在短短一分鐘的片段中這麼貪心!關於這個我們討論滿久的。」王希文認為音樂太抽象,所以用 reference 來確認彼此在想什麼、知道對方的底細很重要,「像我在跟《總舖師》的勳導工作時,他很討厭木管,他就是喜歡銅管跟電吉它,我一用木管就會被罵,理解他的喜好之後就比較順暢。配樂沒有標準答案,它是兩個人的信任跟共同創作,像我現在知道柯貞年喜歡反覆的鋼琴與一個人的氛圍。」
配樂工作中,雙方除了有認知和觀感落差,不可忽視的一點還包括硬體設備、混音與否,配樂做好的檔案,如果用非專業喇叭來聽,其實不一定聽得清楚細節,柯貞年有類似被誆的經驗,「某一段我覺得太滿,希文說是因為太大聲,到時候調小就沒事了,或是他會說稍微修改了,我聽以後覺得比較 OK,但他又說他其實根本沒改,只是調小聲而已。」過去她和其它聲音人員合作,遇到問題對方常推說沒辦法解決,直到王希文告訴她沒有不能,只是他們懶得做而已,這才釐清她的疑惑。王希文進一步說明落差所在,「做配樂有個困境,就是聲音都還不完整、音效都還很素,那給導演聽的時候,應該很大聲讓他聽到細節?還是自己要做一個 rough mix?照理說音樂經過混音也會有很多起伏、跟聲音結合,但音效同時正在做,那我要先做音效和音樂的 automation 嗎?這也不一定是最後版本,因為聲音人員不見得會這樣選擇;我如果音樂弄很大聲你會不會嚇到?如果你不能想像它的層次會不會覺得太滿?所以彼此都要有一點想像力。聆聽的狀態也有差,如果用手機或筆電就會缺乏中低頻,甚至那天的心情都可能影響,是抱著要挑毛病、給意見的態度,或是有東西來了很興奮,真的都會影響很多。」

以上純屬理性分析,王希文再直接點破更棘手的人情問題,「我自己在什麼地方要做什麼事情,其實會想滿多的,所以會希望導演告訴我,我再看能不能調整,但往往交情和輩份都會造成創意流失,滿可惜的,彼此都沒達到能做到的最好選擇。」柯貞年對此深有同感,她確實就曾因為兩代觀念差異而導致工作受阻,同時轉頭問王希文,如果他的音樂被任意剪掉,做何反應?「現在也只會笑笑的,我的所學是電影剪接之後,配樂跟音效要一起跟導演開會,因為兩者是有關聯的。比如這邊有個爆炸,有很大的音效,我的音樂就不要用鼓去對。要讓音效知道哪邊會有音樂、讓音樂知道這邊會加多少音效。可是台灣好像不是每個人都會做這件事,導演直接跟配樂對,聲音卻在最後去動,對導演跟配樂都不是很尊重,因為他們前面已經有創意討論。我有過經驗是配樂做完了,混音那邊覺得要往前移比較好,我說那後面會對不到我設計的點,結果他就把它剪一刀、後面拉長,然後再 crossfade 就說對到了,我說可是這樣就變慢了,他們說反正觀眾聽不出來,我就得選擇要生氣、去跟導演哭、還是自己忍下來。跟人合作都會有很多角力,所以溝通跟判斷情勢很重要,主要是因為台灣配樂這塊還不夠產業化,我做很多長片,每一部大家都不太知道程序,做法也都不同,一直還沒有標準的作業流程。10 年前很多配樂是流行歌的編曲人,因為跟導演拍 MV 認識等等,我有碰過導演全都丟給我不管、最後一次 OK,也碰過一直改的。我也在摸索國外學到的要怎麼慢慢套用在自己的工作狀態,因為現在大家都還不知道該怎麼做。」
.jpg)
另一位曾與王希文合作過的導演徐漢強亦在現場,王希文順勢提及配樂與片型的搭配,「我們合作的是《小清新大爆炸》,配樂做得有點趕,但因為片子比較類型,所以音樂功能滿清楚直接的。比較難的其實是講情感的片,因為抽象,大家想像的落差會比較大。」柯貞年則表示以前還不懂電影配樂時,會認為是片子想要懸疑或催淚但力道不夠,所以音樂趕快進來幫忙,或是哪段有點乾,所以要鋪一段音樂,但與王希文合作後,才了解音樂也要扣合電影整體的主題,王希文解釋道:「電影配樂不能把它想成是 2、30 段廣告配樂擺在一起,你聽國外很多電影原聲帶,會覺得整張有一個氛圍,有個旋律一直出現,會有結構在。」他舉《魔戒》為例,哈比人每次講到回家或是出征時,都會配上很清楚的功能性旋律,因為故事太多、種族太複雜,需要音樂來梳理情節和人物,「這是配樂很重要的功能,也才能達到電影作品的高度。我以前剛開始做學生影片,也遇過剪接跟拍攝時都沒有考慮音樂,就只是把戲順完、剪完,覺得乾才加音樂,於是就會出現只有 20 秒的音樂。這個長度超尷尬,才剛開始就要結束了。像新電影是很寫實,不需要情緒來弄觀眾,可是如果要做類型片,在剪接甚至腳本上就要思考用音樂來說故事,有音樂的情況下,剪接甚至表演的選擇都會不一樣。比如《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因為知道要配這種音樂和特效,導演都想好了,所以演員會相信必須要這麼誇張,如果沒有互相配合,那些表演就會很突兀。」(待續)
【新導演的幾道難題】
過去從媒體與出版工作開始,逐步窺見台灣電影產業的真實內裡,之後在此策劃了「於此與我的導演你」專欄,得以更直探進年輕創作者的心靈;深覺著 歷史上的輝煌已淡去,而嶄新的浪潮未到來,我們這一輩是破滅後急待重建的世代,好像卡在餘燼的末端尋找下一顆火種,正由於要面對的困境很相似,才必須有更 多的談話、更多的激盪,電影或者文化,終究得先凝聚眾人之志,才可能有不同局面被開創而出。
2015 年起,我與小路上藝文空間、晶體影像製作聯合發起的「折射計劃」,旨在透過整年度的系列活動,聚合當代電影青年的能量,用以自力救濟、自立自強。本專欄將刊載每一場對談紀錄,台灣電影的難題太多,我們只能先幹再說。
【孫志熙】
曾任《CUE電影生活誌》、《SCOPE電影視野》主編。現從事專欄與文案寫作、短片推廣、獨立製片、跨國當代藝術組織台北組頭、地下電台主持人等,擁有多重身分與很多款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