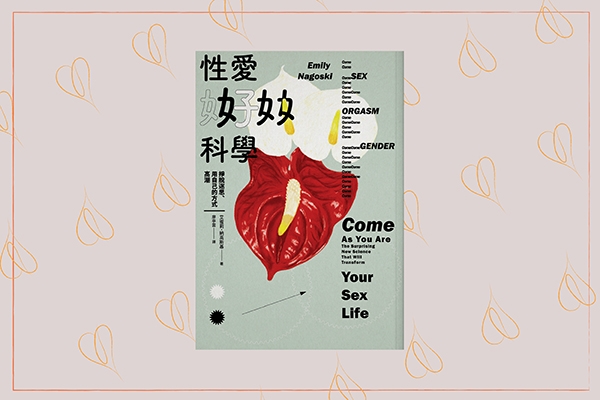張惠菁讀《為失竊少女祈禱》:在「殺女之國」女人如何活下來?
前幾年墨西哥導演阿方索.卡隆執導的電影《羅馬》,引起過很多話題。它也是那一年我最喜歡的電影。劇情發生在墨西哥城的高級住宅區科洛尼亞羅馬,一個白人家庭雇用了一位原住民女傭克萊奧。克萊奧和這家人的關係很緊密,雖有階級之分,但隨著那個家的女主人遭遇婚姻危機,克萊奧自己也未婚懷孕並被男友拋棄,她和這個白人之家逐漸同情共感,形成一種沒有血緣的新家人關係。片中的克萊奧性格溫柔穩定,彷彿是所有人的母親。但她卻意外目睹了拋棄自己的男人行惡,而無法去愛腹中的孩子。她和主人家漸漸成為世情大浪中互相依靠的存在。男人離去,女人與小孩重新分配了房間。大宅子仍然蔭涼,市聲隱微,穿窗而來,外頭陽光普照。
《為失竊少女祈禱》發生在墨西哥城外,一個惡劣得多的生存環境。那裡,男人也都離開了,但他們是去加入幫派,或偷渡到美國。留下的女人們只會生下「男孩」─因為所有女孩都要被妝扮成「男孩」,剪短頭髮、弄髒臉孔,當成男孩來養。一旦有個美麗少女長成的消息傳出,就會引來人口販子,他們將女孩們當成農作物,時候到了就開著車來收成,拿槍比著她們的母親,帶走剛開始青春,美麗已藏不住的女孩,不幸的厄運從此便降臨到女孩身上。
小說中的敘事者名叫黛妃。她的母親為她取這個名字,不是因為嚮往黛安娜王妃的貴族光環與美麗容顏,而是因為黛安娜王妃也是一個棄婦。黛妃從小活在一個顛倒的世界,女孩為了生存扮男孩,長到扮不了男孩了就扮醜。小村裡唯一一家美容院其功能是「醜容院」,幫女性們把美掩蓋起來。這樣還擋不住綁架者們的窺伺,母親們便開始挖地洞,一有陌生人來便把女孩們像種子根莖般種到地裡隱藏。她們是一種必須不斷抹消自己存在的性別。
村裡只有一個學校。每個學期都換老師,老師是從城市來的,年輕且剛從教師學校畢業,只會在這偏遠之地待一學期,完成教學服務,然後就回到城市裡重新被分發。社工人員也是,來了又走,帶來的物資有限,什麼也給予不了。
這個小村是被遺棄的世界盡頭,只會在外來者的人生中存在很短很短的一段時光。如果他們善良,這個小村會成為他們生命中一種無能為力的回憶。如果他們冷漠,那就什麼都不會留下。
這是一個當代議題性很強的題材。就在我讀這本小說的時候,二○二○年二月十四日的國際新聞報導,墨西哥女性走上街頭,包圍總統府,抗議她們的國家是個「殺女之國」。在那裡,女人的命如此不值,在婚姻裡、在男人的慾望遊戲中被當成損耗品使用。但是珍妮佛.克萊門沒有因為議題性強,就把小說寫成了一篇申論文。這本書是很好的文學。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小說家謹守著黛妃的聲音。這是一個卑微但是清晰,感受敏銳,而會引發共感的聲音。小說從她的視角,去看到了她的家、村子;看到她藏身其中而得以免難的兔子洞,看到學校;從載著她離開村子的車,一路上經過的旅途,看到她被送去幫傭的家(如《羅馬》電影中一般的豪宅?),乃至抵達和離開女子監獄。小說看到了她的母親,母親對父親的又愛又恨。看到母親因父親到處捻花惹草而怒火中燒,而和丈夫大打出手,但卻從沒怨恨和他發生一夜情的女人們,以及從那非婚姻關係中誕生的女孩。等到男人離開,女人們還是會互相照顧著活下去,不分是誰生的孩子。小說從黛妃的視角,看到那憤怒,也看到那人性。
這是一本好小說。它以文學和故事的力量,帶著我們去共感了在遙遠大陸之上,一種嚴酷的生存處境,「殺女之國」中的女性。就好像在小說中的女子監獄裡,原本互不相識的女囚們被故事連接起來,理解了彼此。我不知道女囚們在男性的世界裡能否找到出路。我知道的是,透過故事,一張女性的網,以其中每一個受傷個體的苦與悲傷、絕望孤獨為絲,被織造出來了,一個角落一個角落地連接,直到遍布整個國家、整個性別。北緯二十三度度那殘酷又溫暖的陽光正普照其上。同受苦楚者,內心的頻率,口耳流傳的話語,在空氣中震動,綿長久遠,不絕如縷。
《為失竊少女祈禱》
作者:珍妮佛・克萊門
譯者:黃意然
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