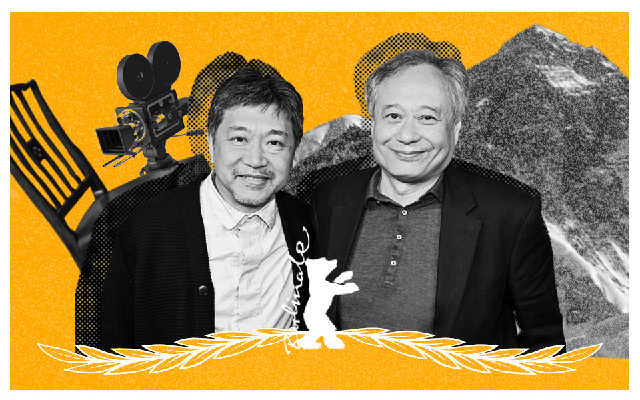2020 這一年,我們 50:50 了嗎?性別平等的實踐,從柏林影展談起
2016 年瑞典電影學院曾在坎城影展中提出 5050x2020 連署,提倡在 2020 前,電影產業能達成 50/50 的男女比。該連署被大眾廣泛誤解為,要求各大影展在節目策劃時,必須選出男女導演各半的片單。實際上,它旨在倡議:權力須要平均分配,各大影展做到人事組織透明,並提供詳細數據供大眾檢視;而非透過配額制度,忽略現實情況,打著「政治正確」口號提拔女性導演。四年過去,2020 年的尾端,是後 #metoo 時代我們得以查看影展、電影產業的階段性成果。
其中,歐洲三大影展裡最先開跑、也最注重政治及社會議題(也註定是本年最不受疫情影響)的柏林影展更值得我們分析。
今年柏林影展的開幕片《My Salinger Year》是一部輕巧討喜的女性成長電影,由 Sigourney Weaver(雪歌妮薇佛)跟 Margaret Qualley 主演,背景設在九〇年代紐約。有人形容故事像文學版的《穿著Prada的惡魔》,描述一年輕女子初到紐約大都會便進入版權經紀公司,從回覆沙林傑的讀者來信開始做起。沙林傑是本片賣點而非重點,女主角嗜好文學寫作,時間卻被工作佔據,影片呈現她的生活困擾與生涯抉擇,卻沒有特別交代她的文字創作,觀眾便無從得知她想說怎樣的故事,是這部女性成長電影留下的空白。

《My Salinger Year》© micro_scope

《My Salinger Year》
還記得年初 ,Greta Gerwig 執導的電影《她們》在海報上的宣傳標語是「寫自己的故事」,我不禁好奇,當代的女性創作者想說什麼樣的故事?本文想談三部今年柏林影展讓我印象深刻的女性導演作品,文末並簡單整理本年度柏林影展與性別有關的數據。
《Shirley》:瘋女養成記,活得不正常才自由
由 Elisabeth Moss 製片並主演的《Shirley》是部「非典型」傳記片,就如電影刻畫的主人翁—Shirley Jackson,美國恐怖、懸疑小說家,1948年憑著爭議十足的短篇小說《樂透》(The Lottery)出名。這部電影改編自 Susan Merrill 的小說,導演 Josephine Decker 形容本片風格像把 Shirley Jackson 放進她撰寫的恐怖故事,訴說一段瘋魔又鮮美的女性情誼。
故事描述新婚的 Rose及丈夫 Fred 暫時寄居文學教授 Stanley 家,條件是待產的 Rose 需負責打理家務,並照顧教授足不出戶的作家伴侶 Shirley。Rose 行為舉止看似溫良恭儉讓,起初使性格乖僻的 Shirley 反感。兩人朝夕相處下,漸漸被對方不太正常的內在特質吸引,發展出愛恨交織的複雜關係。在一場門廊鞦韆的女女調情戲碼,導演只透過運鏡、剪接,以及演員的臉部表情,不用半句對白就讓人看得心跳加速。
片中,Shirley 正構思一本小說,以新聞報導中失蹤的女大學生為主題發展,她從 Rose 身上汲取靈感,但那本小說終究寫的是她自己。她執著書寫那些迷途女孩的故事,因為迷失的女孩後來都瘋了;但不正常的瘋女孩,可能活得最不受傳統拘束、最快樂。如果可以自由,誰想要正常。

《Shirley》© 2018 LAMF Shirley Inc.

《Shirley》© 2018 LAMF Shirley Inc.
有趣的是,現實中 Shirley Jackson 育有兩女兩男,電影裏卻被導演塑造成不生小孩的獨立形象。戲中她還對懷孕的 Rose 說:「希望會是個男孩,這世界對女孩太殘忍(The world is too cruel to girls.)。」
《Never Rarely Sometimes Always》:少女墮胎記,拿回自己的身體
這是一部講述未成年少女墮胎的電影。聽起來很聳動嗎?或許,或許不。無論你對墮胎的立場為何,美國導演 Eliza Hittman 沒有要說教,也不打算高聲倡議女性權益。她用 100 分鐘時間,帶領觀眾跟著兩名白人少女,從賓州到紐約,三天兩夜,親身經歷一趟困難重重的墮胎之旅。導演說:「這不是一部處理道德兩難的片子,它關乎一個需求。」
最早在 2013 年,Eliza Hittman 讀到一則新聞:跟隨丈夫移居愛爾蘭的印度籍女子 Savita Halappanavar 因為墮胎被拒,不幸死於異鄉。她的死後來促成愛爾蘭在 2018 年廢除墮胎禁令。在那之前,許多愛爾蘭女性會跨海遠赴倫敦進行墮胎。那時起,導演便開始想像這些旅程會是什麼模樣,並想以此題材拍一部電影。然而投資人似乎對這故事興趣缺缺,尤其當時歐巴馬當政,美國社會彷彿光明又進步,計劃多年不了了之。直到川普當選總統,國內保守價值氣焰高漲,導演認為是時候開拍這部墮胎電影,並把背景改在她較熟悉的美國東岸。劇本很順利獲得環球旗下藝術品牌焦點影業(Focus Features)的高層親睞,影片在前製階段便找到發行商。
《Never Rarely Sometimes Always》電影開場是個高校才藝演出,十七歲的女主角 Autumn 打扮酷炫並自彈自唱〈He’s Got the Power〉(他有權力),歌詞內容是「他讓我做了我不想做的事⋯⋯」,唱到一半被台下男同學嘲笑「婊子」(slut),她短暫停止演唱後,略顯尷尬地在朋友的加油聲中繼續完成表演。演出結束眾人在餐館吃飯,一名男同學對著女主角用嘴巴作猥褻動作,她感到不舒服,忍不住起身拿水潑那無禮又噁心的同學。類似的「性」騷擾戲碼在片中反覆出現,導演嘗試刻劃女性平時遭遇的種種不愉快情境,幾乎像日常的驚悚片,卻可怕地寫實。
長長一串頻率副詞組成的片名《Never Rarely Sometimes Always》出現在電影中最關鍵的一場戲。當女主角 Autumn 抵達紐約曼哈頓的墮胎中心時,諮商師按照程序,先向她進行有關健康與性史的問卷調查,「從不、很少、有時、總是」為主角可以回答的四種選項。整場戲一鏡到底完成,鏡頭特寫在新人演員 Sidney Flanigan 穿著鼻釘的白淨臉龐。隨著題目越問越私密,諮商師用溫柔而規律的聲音說出:「妳的伴侶拒絕使用保險套?從不、很少、有時、總是」,「妳的伴侶強迫妳進行性行為?從不、很少、有時、總是」,表情淡漠的女主角終於眼淚潰堤,她點了點頭,卻沒辦法繼續回答下去。那一刻,觀眾彷彿同處那間諮商室,感受著主角所有情緒,她的不安、焦慮、脆弱、掙扎,與創傷。

《Never Rarely Sometimes Always》© 2019 Courtesy of Focus Features

Eliza Hittman 以《Never Rarely Sometimes Always》拿下評審團大獎。
當本片獲頒評審團大獎時,導演難掩激動地說:「我花大量時間研究『計劃生育協會』(planned parenthood),並採訪許多醫護人員跟相關社工。我要感謝他們的效力,感謝他們保護擁有子宮的人。」這不是一部賣弄墮胎議題,以博取觀眾同情的電影。它讓我們共情,設身處地揣想另一個「人」私密的生命經驗。自己的身體自己決定,說來多麼容易,現實卻是,多麼不容易。
《The Assistant》:助理求生記,看見問題後的問題
澳洲紀錄片導演 Kitty Green 的首部劇情長片《The Assistant》同樣是一部完全聚焦在女性主角的電影。故事啟發自 #metoo 真實事件,導演採訪了上百位電影圈同業,卻不把重點放在男性加害者。她無意拍一部如《重磅腥聞》那般吸眼球的好萊塢式揭弊電影,反而將故事圍繞在一名電影製作公司的基層小助理,從她的視角出發,靜靜觀察整個辦公室文化,到底哪裡出了問題?導演曾在訪談表示:「如果問題只在 Harvey Weinstein,那還容易解決。但問題出在整個體系,那些人們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以及有毒的職場文化。」
《The Assistant》故事發生在一天之內,情節隨主角 Jane 的助理工作展開。電影開場,天還未亮,Jane 便睡眼惺忪地乘著夜色搭車前往辦公室。她任職不久,充滿野心,任勞任怨。煮咖啡,倒茶水,訂外送,整理環境,各種瑣事都做,卻不受人重視。一場電梯戲中,演員 Patrick Wilson 客串現身演出男明星,她完全被他當空氣。在影像構圖上,導演時常把女主角放在中間偏下的位置,凸顯她在這個辦公室的渺小與無足輕重。影片細緻的聲音設計也讓觀眾聲歷其境,用各式環境聲響帶出主角的壓力與疏離感。
今年才憑影集《黑錢勝地》(Ozark)二度拿下艾美獎的 Julia Garner,在電影中不慍不火的內斂演出,讓人想起女性主義經典代表作《珍妮德爾曼》的主角 Delphine Seyrig,兩部片也都在平淡的日常細節中營造出緊繃的張力。儘管《The Assistant》片名意指中性的「助理」,電影卻呈現出性別化的勞動分工。比如客戶帶小孩來訪,Jane 要充當臨時保姆。老闆妻子來電發飆,她要負責安撫,情緒勞動一樣不少。偶爾犯小錯,也要聽同事「男性說教」(mansplain)解釋怎麼做才對。

《The Assistant》 © Forensic Films
影片中段,當 Jane 被要求訓練一名毫無經驗的新助理,她察覺事情似乎不太對勁。這些年輕貌美的無名女子從何而來?為何她們總被老闆約見在高級飯店?幾番糾結,Jane 終於鼓起勇氣向人資部門提出申訴。她不知怎麼向男主管開口,只能好傻好天真地問:「我們該怎麼做?」換來的輕蔑回應是:「有什麼需要做的?別擔心,妳不是他的菜。」也許這就是醜陋的真相:當握有權力的人無視問題,底下的人也無力改變。
朝向一個性別平等的影展
根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分析報告,今年度柏林影展各單元的領導職務在性別比例上確實達到一比一平衡,各自單元的選片團隊成員甚至女多於男,然而選映的作品仍由男性導演佔多數,畢竟報名作品數量上,現狀還是男多於女。數據顯示,今年影展方收到約佔三成的女性導演作品,而在最終公布的片目裡(不含經典修復單元),總共有 38.7% 的電影由女性執導,較往年稍有改善。
在主競賽 18 部影片中,有 6 部由女性獨自執導,雖然比去年少一部,仍是三大影展裡頭,導演性別比例相對平衡的(坎城影展去年 21 部競賽片有 4 部女導演作品,而威尼斯影展 21 部中只有區區 2 部)。除了選映影片的導演數據分析,這份報告也呈現製片、編劇、攝影、剪輯部門的性別比例。值得注意的是,製片跟編劇是相對男女平衡的部門,而女性攝影師的比例則偏低。報告的最後,也提及歷屆金熊獎頒給女性執導作品的次數(6次,9.5%)與競賽評審團主席為生理女性的次數(19次,29.7%)。
當我們談論影展選片的性別政治
身為觀眾,當我們討論大型國際影展的選片規劃,需要將其「產業」、「政治」、「藝術」等各種面向一併納入考慮。競賽片單不光是挑選最「好」的電影,其間還有影片發行商、影展贊助商等各路人馬明裡暗裡的金錢角力。掌權者要有智慧拿捏箇中平衡,提出讓人信服的片單,而非在面對爭議時,避重就輕地拿藝術作擋箭牌,開脫自己對性別政治的傲慢冷漠。
去年,當 Thierry Frémaux 與 Alberto Barbera—坎城與威尼斯影展的藝術總監—面對外界質疑其選片方針,尤其主競賽片單中女性導演的稀缺,兩人幾乎口徑一致回答:選片完全根據電影質量,而非導演性別。聽來冠冕堂皇,實則讓人無比困惑。他們到底根據什麼標準評判電影質量「好」與「壞」,該選什麼不該選什麼?
我們可別忘記 2016 年坎城影展,美國男演員 Sean Penn 執導、主打 Charlize Theron 與 Javier Bardem 的《戰地情》,在銀幕雜誌場刊獲得破天荒的 0.2 低分,是為坎城影展史上的競賽選片大醜聞。很巧的是,同樣由 Javier Bardem 主演,入選今年柏林主競賽的英國女導演 Sally Potter 新作《The Roads Not Taken》,敘事混亂且故事完全不知所云。很難不讓人懷疑,影片入選也只為明星卡司 Elle Fanning 與 Salma Hayek 走紅毯,以博取媒體關注。
藝術評判當然主觀,這卻無法成為選片人不解釋一切的方便藉口。在這個最好也最壞的時代,該堅守的價值是什麼?作為藝術品味守門人的影展主事者,將怎麼藉由這萬眾矚目的大平台呈現當代電影的樣貌?當她們開始說故事,你有認真聽嗎?畢竟這從不只是她們的事,是妳—你們、她—他們、我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