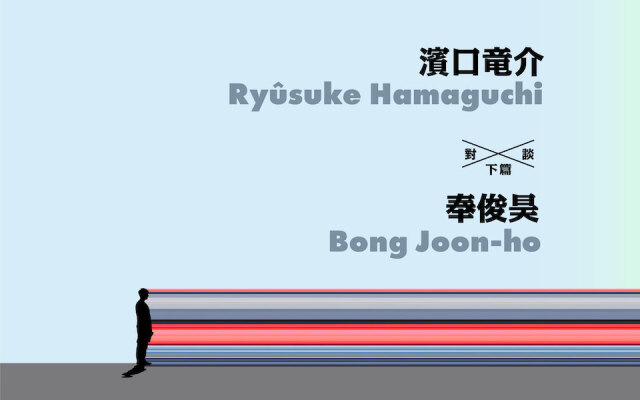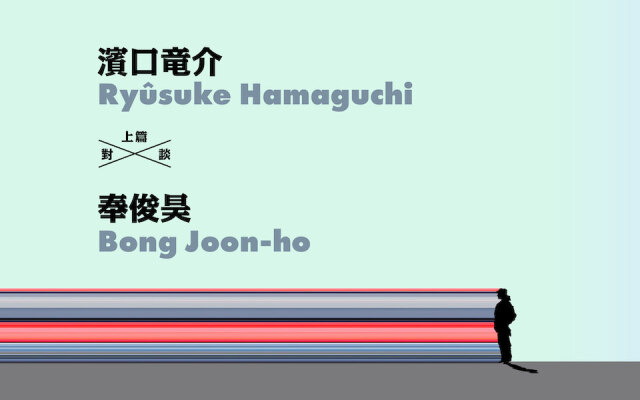出發與抵達之間,他們抽了七次菸——濱口竜介《在車上》與村上春樹〈Drive My Car〉
濱口竜介的魔法還在繼續。
電影《在車上》改編自村上春樹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的短篇〈Drive My Car〉,卻並未被原著牽制,有著滿滿的濱口魔法:一種能從柴米油鹽裡提煉奇蹟的敘事術。本次濱口竜介也挑戰在電影中,埋入多重互文遊戲,觀影時有如在玩戳戳樂,聲音一下,畫面一來,村上春樹式的「似曾相識」在眼前張開,有如一趟三小時的思想兜風。
本文將以一位身兼濱口竜介與村上春樹的雙重粉絲視角,拆解《在車上》層層謎語和咒語。看完電影,不妨讓我們對照彼此的共鳴。
下方有劇透轟炸,請在意者斟酌閱讀
1. 車
無論是村上春樹或濱口竜介,作品裡都有車。
對村上春樹來說,比起車本身,他似乎對司機與乘客的關係更為著迷。《1Q84》開篇,女主角青豆便與計程車司機在車上談論楊納傑克,而青豆也是在司機那句「不要被外表騙了,現實經常只有一個。」的召喚下,走進「另一個現實」——這麼說來,村上筆下的角色確實連一位整天開車的司機,品味都好得異常。車也往往擔負鑰匙的功能,為角色打開通往異處的門扉,不過也有時候,車就是「異處」本身。《遇見 100% 的女孩》裡的短篇故事〈計程車上的吸血鬼〉描述「我」遇上一位開計程車維生的吸血鬼司機,以一段漫長荒誕的對話,讓角色從人際關係的規訓中解放。
濱口竜介裡的車,則是讓對話發生的培養皿。《歡樂時光》第一幕,四位女主角在纜車上緩緩移動,光與影拉開她們的面容,勾勒故事的輪廓;《偶然與想像》第一個故事裡,兩位少女也在計程車上,談話間點出故事裡的「魔法」⋯⋯濱口竜介的車廂鏡頭別有風味,不過他曾在與奉俊昊的對談坦言,這樣的拍攝手法是為了填補「以寫作敘事切入電影創作」的盲點:「書寫對白時,我會想,如果電影欠缺動感會很無趣。如果對話能發生在會移動的地方,譬如在車上,場面看起來就會有意思些,讓靜寂的時刻也充斥著動態。這是我掩飾自己創作盲點的方法。」
有趣的是,在《沒有女人的男人們》原作〈Drive My Car〉中,馳騁在瀨戶內海的,應該是一台黃色紳寶 900,而非電影裡出現的紅色。關於這點,濱口竜介也有解釋,「處理拍攝用車的負責人與我見面時,開著紅色的紳寶 900 出現,遠遠開來感覺滿帥氣,我當下覺得或許這更適合。」車子作為電影裡,把角色間情感凝練成一體的關鍵,紅色確實比黃色更能吸引目光。
2. 菸
觀影前買包菸吧。相信我,用得上。
村上春樹作品裡,菸的登場別緻。《人造衛星情人》裡小菫抽輕盈的 Salem 涼菸,《挪威的森林》的綠跟《尋羊歷險記》敘事者「我」則喜歡經典款 Marlboro,《發條鳥年代記》納姿梅格愛抽 Virginia Slims⋯⋯村上春樹常以菸的品牌捕捉角色的神態,比如《挪威的森林》裡渡邊曾調侃 Marlboro 不適合綠這樣的年輕女孩抽,側寫綠的不平凡。
村上春樹寫作前期,往往仰賴抽菸釐清思緒、集中注意力,甚至有一天要抽 60 根的傳聞;據賴明珠在《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譯者序的說法,村上春樹在《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時期果斷戒了菸,理由是:不想被什麼東西給束縛。村上連戒菸都村上。
濱口竜介有沒有菸癮我們不得而知,但他倒是讓西島秀俊抽了不少菸。
《在車上》的抽菸橋段有七次。家福發現妻子家福音正與高槻外遇後,難忍內心波折,點著電影第一支菸。第三根菸則是家福與美沙紀在風大的海濱彼此借火、以秘密交換秘密:家福談起妻子的本名,美沙紀也才揭曉她的姓氏,渡利。菸讓《在車上》的鏡頭擁有了呼吸與屏息的餘裕,也是角色間安靜的火花,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菸戲有二:
第六根菸。家福跟美沙紀兩人手搭著手,伸出紅車天窗——那使夜晚靜止的「乾菸」,無聲說完了兩人曾有與現有的傷口:「活著本身就會要命。」
第七根菸。是美沙紀死去的母親抽的。兩人探訪美沙紀被土石流破壞的老家,美沙紀赤手在雪地上挖一個小洞,點菸,把菸立在洞底(有些洪常秀《江邊旅館》的味道在)雪地中央燃起一縷白息,雪在呼吸,被廢墟埋葬的美沙紀母親也在呼吸。這是生者對死者的追悼,生者也完成對自己的寬恕與諒解。
.png)
3. 雪哈拉莎德
《一千零一夜》或許是我們生命初次意識到:文學可以救人一命。
故事我們都熟。一位殘暴的國王每日娶妻,並將其殺害。直到他遇見一位少女,少女徹夜說故事釣國王胃口,國王為了知曉故事後續,每晚都饒過少女。而少女的名字,就叫做雪哈拉莎德。
村上春樹《沒有女人的男人們》裡的短篇〈雪哈拉莎德〉描寫一個神秘女子,在與男人做完愛後,會不自覺講起一段似真似假的故事,村上春樹藉由這位故事來詮釋「故事/語言」的誘力——這樁概念被濱口竜介改編進《在車上》。音在與家福性愛後,也會在意識模糊時,虛構一段故事,但音會隨著意識清醒而忘記內容,為了讓音能把這些劇情寫成電視劇腳本,得靠家福即時記下故事,如此你來我往,變成夫妻間比性愛本身更親密的默契。
.png)
這種「孕育」故事的過程,令我想到海馬的生產習性。公海馬先將精子射入母海馬體內,母海馬會再把受精卵產在雄海馬肚子的育兒囊中——家福與音對待「故事」的歷程,就好像海馬伴侶的孵育行為。恰好,音開始捏造故事,也是在失去女兒之後。曾經的失去帶給她新的產出。「故事」聯繫起兩人的情感,有如家福跟音的第二個孩子般重要,所以當高槻道出音未曾說完的故事後續時,家福也對亡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疏離與陌生。
不被身體、物理距離所契約的關係深淺,是濱口竜介常在作品中嘗試的論題。《偶然與想像》的第一篇故事〈魔法(也比不上的虛幻)〉裡,兩個女人在車上談到一種聊天經驗,不存在 dirty talk,不存在調情,卻可以深深碰觸彼此內在、令人性興奮的對話,也得出結論:單純的聊天原來可以比做愛更情色——這個瞬間在《在車上》得到新的回應,濱口竜介在日常裡建複本,醞釀自己的世界觀。
4. 西島秀俊
這是西島秀俊二度參與村上春樹改編的電影。
改編自《萊辛頓幽靈》中同名短篇的《東尼瀧谷》,由市川準執導,尾形一成、宮澤理惠主演—— 沒看過《東尼瀧谷》,也該聽過坂本龍一為其配樂的〈Solitude〉與〈DNA〉兩首名曲。《東尼瀧谷》通過故事主角,東尼瀧谷的模糊面孔,投影出生於日本戰後一代人,在過份安定的城市生活裡,內心難以消化的孤獨。
西島秀俊在本片只負責旁白。儘管無法肉眼看見他的英氣,但那宛如被壓在海底的低沉聲音,可說是本片的點睛之筆。《東尼瀧谷》不收對白,不收環境音,觀眾的聽覺被集中在旁白的敘事節奏上,搭配坂本龍一的配樂,是比小說更像小說的觀影體驗。全程沉默的角色,飽和度低的色調,東尼瀧谷的孤寂像是長在銀幕上的一顆大洞,著魔似地把人吸進去。
身為村上迷的西島秀俊曾說,自己本想主演《東尼瀧谷》,奈何市川準已找來尾形一成,只好以聲音參與本片。如今《在車上》給了他發揮(aka 袒胸露背)的機會,也算圓夢。
5. 美沙紀
在關係裡掙扎的女性,是濱口竜介劇本的重心。與黑澤清合作腳本的《間諜之妻》,也繪製女性被時代與愛情所逼,毫無保留奉獻自己的淒涼圖像。
單就對女性刻畫深淺而言,濱口竜介跟村上春樹很不一樣。我們多能在濱口竜介的電影裡,看見女性在異性戀關係中嚐盡苦澀;村上春樹的小說中亦有類似描述,只不過大多仍以男性視角出發,就連光譜中少數處理女同志題材的《人造衛星情人》,敘事角度都帶有一些男性對女性的無能為力或費解,性別意識在村上春樹的小說中略顯單薄。
這樣的濱口竜介,翻拍這樣的村上春樹,處理性別的策略令人好奇。濱口竜介確實照著原作來,《在車上》有別以往,從男性視角出發。儘管女性角色的內心刻劃較少,卻沒有因此變成陪襯。美沙紀擔任家福司機一職。對開車技術極為苛扣的家福,對陌生人的開車技術戒慎,沒想到美沙紀的駕駛手法意外與家福契合。
原來,美沙紀之所以被家福稱讚「坐在她的車上,幾乎感受不到重力,有時甚至忘記自己在車上」肇因於美沙紀的創傷。美沙紀國中時,賣淫的母親讓她擔當駕駛,為了不把母親吵醒,美沙紀練就了路況再糟糕、還是能保持車體平穩的技巧。小說〈Drive My Car〉最後如此漂染兩人的依賴:
「我睡一下喔。」家福說。
美沙紀沒有回答,就那樣默默繼續開車。家福感謝那沉默。
有時不拍勝有拍。濱口竜介營造角色回憶時,不如一般電影會轉場,讓往事在電影裡復活。他更傾向現實情況,角色自述過往,給足觀眾想像空間,也讓故事更專注於當下。故事中美沙紀對母親的描述皆是如此。
美沙紀也告訴家福,原來她的母親體內存在另一人格,幸知。幸知對待美沙紀親和,有如朋友。對美沙紀而言,當她目睹母親瀕死,而不出手拯救,其實也是在殘忍地凝視幸知之死。她既殺死了母親,也殺死了密友。
「如果我是你父親,我會抱著你並說:『不是你的錯』。」即使家福如此安慰美沙紀,「但事實是,你殺了母親,我殺了妻子。」兩人隨後進入隧道,黑暗傾斜而來。

6. 凡尼亞舅舅
「光是朗誦契訶夫的劇本,真實的自己也會被拉扯。」
——《在車上》
敘事中放置「超連結」跟「壓縮包」,是村上春樹小說裡常見的筆法。不同的音樂、文學、藝術作品,甚至是人名、地名,在村上春樹的調度下,成為一道道若有似無的隱喻,建構獨特的世界觀,也成為一代文青養成指南(?)而〈Drive My Car〉裡,村上為我們安排的,是契訶夫的名作《凡尼亞舅舅》。
《凡尼亞舅舅》是什麼樣的故事?劇情描述一位農莊主人、退休教授謝列布里亞科夫,與貌美年輕的妻子伊蓮娜返鄉居住。伊蓮娜的到來,使農莊管理者凡尼亞舅舅、鄉村醫生阿斯特洛夫內心蕩漾。尤其凡尼亞舅舅開始反思生存的意義:二十五年來,凡尼亞舅舅替視為偶像的謝列布里亞科夫看顧莊園,虛擲生命的結果,卻是在某日發現謝列布里亞科夫的庸俗。莊園在謝列布里亞科夫造訪後,回不去往日平靜,角色們突破了一層情緒阻力,開始瘋狂地愛、瘋狂地恨。
濱口竜介替我們解壓縮、點開超連結,把《凡尼亞舅舅》的文本更完整地穿縫在《在車上》中,包括家福在車上播放的錄音帶、家福帶領演員們捧讀台詞的時刻、以及演出現場。錄音帶是家福讓音錄製的,音的死,彷彿只是她的身體消失,她的聲音把靈魂保留在電影裡,到最後甚至成了紳寶 900 的地縛靈,也是家福給自己下的緊箍咒。
錄音帶的聲音,或家福開車時的台詞練習,經常在電影裡混肴著觀眾的認知:這究竟是台詞?還是角色藉台詞坦承心事?當家福朗誦「那女人的忠實是徹頭徹尾的虛假⋯⋯原來我們有同一種悲傷,因為我們愛上同一種女人⋯⋯」,觀眾也不寒而慄,表情冷峻的家福對音的背叛,是否也抱持熾烈搖曳的恨意?
但我想,《凡尼亞舅舅》也是讓《在車上》不如濱口竜介前幾部作品來得靈動的主因。在看《歡樂時光》時,觀眾都能注意到,濱口竜介有意拖長電影的速度,比如在一小說朗讀會的橋段裡,讓作家唸完小說段落,電影裡的聽眾開始疲倦,電影外的觀眾也不太耐煩,完成了電影時間與現實時間的同步。
《在車上》裡《凡尼亞舅舅》的出現,像一個機關咬著機關,劇本裡的對白,都影射角色的情狀、並如發條般與角色密切互動。這樣的設計實則有些刻意了,濱口竜介沒有在文本與電影人物之間,留足縫隙與呼吸節奏,私認為,若是能再鬆動一點會更好些。濱口推進日常的膚觸,被創作者的手痕稍稍破壞,是電影比較可惜的地方。
7. 高槻耕史
高槻完成凡尼亞舅舅時,凡尼亞舅舅也完成了高槻。
劃破寂靜的一聲槍響,飾演凡尼亞舅舅的高槻,在最後一次排演中向謝列布里亞科夫開槍。此時,一批警員來到排練現場,抓捕高槻。原來高槻不只在戲裡,也在現實中殺了人。
高槻是電影中推進劇情的要角,他鑄下的錯誤、說了一些煞有介事的話,不斷影響著家福的思緒與行動。不過在〈Drive My Car〉原作中,家福跟高槻摩擦少,兩人也稱得上情投意合的好友,高槻在村上小說裡的定位,類似《聽風的歌》裡的老鼠、〈燒掉柴房〉裡縱火的「他」,是村上小說裡常出現、愛給主角下指導棋的酒友型角色。

濱口在電影裡更劇烈的解壓縮,是解出高槻這個角色的另外一層存在意義。在車上,高槻間接承認與音的外遇關係,卻也銳利指出人際關係的無能,那是家福原先不願面對的:
「我們難道能夠了解誰的全部嗎?就算深深愛著那個人?」
「想要看清別人,就只能更深刻而直接地凝視自己。」
8. 上十二瀧町
米蘭昆德拉《不朽》裡有這樣一句話,「公路自身什麼也不是,而只從所連接的兩點獲得了它的全部意義。」是啊,公路什麼也不是,但為什麼我們仍喜愛公路電影?並且在看公路電影時,比起他的出發與抵達,更癡情於被車窗剪裁的每一段風、每一寸風景?
作為漫漫人生的隱喻,公路使我們凝視自身。
《在車上》最後,家福與美沙紀來到美沙紀的故鄉,上十二瀧町,也儼然是一場公路電影特有的(未)完成式:角色在旅途中完成些什麼,回歸日常後,也有什麼變得不一樣了。「什麼」是什麼並非重點,而是「什麼」的發生本身,讓人意識到,「經過」有時比出發或抵達更美。
那輛紅色紳寶 900 離開隧道的瞬間,畫面切換成極白的雪景。原本的環境音被一下子撤銷,濱口竜介拍出了語言或文字無法追及的無聲狀態,然而無聲也是聲,鏡頭在耳鳴。
聲音的真空,也讓觀眾明白,兩人已經來到上十二瀧町。
村上春樹在小說中對北海道告白不少次,也與十二這個數字緊密相繫(生日剛好是一月十二日),他在《尋羊歷險記》裡虛構了北海道地名,十二瀧町,故事設定中,那裡是日本綿羊的發源地,也是「羊」這個超現實角色離開羊博士後,暫時的落腳處。
放心,我沒有打錯字。《在車上》及原著中的「上十二瀧町」、《尋羊歷險記》的「十二瀧町」確實有一字之差。但倒也無妨,或許我們都可以將其視作村上春樹對北海道的投射。有意思的是,村上春樹〈Drive My Car〉最初在《文藝春秋》刊登時,使用的是「中頓別町」的真實地名,但因為寫了句「輕輕嘆一口氣,把點著的菸就那樣彈出窗外丟掉。這種事可能在中頓別町大家都平常地這樣做。」而受到中頓別町議員的抗議,認為村上春樹污衊町內居民。村上春樹事後道歉,坦承無此意,並將其改成「上十二瀧町」。
廢墟,雪地裡飄零的鮮花,點著的菸,上十二瀧町發揮了公路盡頭的無限魅力。「我應該是受傷了,傷到都瘋了。我深深地受傷,卻選擇對現實視而不見,選擇不傾聽自己的心。」家福講出改編自短篇〈木野〉的台詞,村上春樹把痛失妻子的角色封印在黑暗安靜的房間,濱口竜介選擇讓角色面對創傷——
殺了母親的女兒,殺了妻子的丈夫,殘缺的兩人在雪中擁抱,完整彼此。
「活下去的人,只能不斷思考死者的事。」
被死者改變的生者的眼睛,將會繼續確認未來的風景。
9. 結局
「凡尼亞舅舅,我們要繼續活下去,我們走過漫漫長日,度過漫漫長夜,咬緊牙關度過命運帶給我們的考驗,儘管不能休息,但我們會持續努力為他人工作,等到最後的那一刻到來,我們都可以平靜離去。」——《凡尼亞舅舅》
比著手語的索尼亞,最後在凡尼亞舅舅的胸膛上,劃下一刀般比示:我們將得以休息。
契訶夫並未讓索尼亞與凡尼亞舅舅得到幸福,卻給予他們善於等待的雙眼。儘管直視傷口,但不代表疼痛消失,濱口竜介電影裡的角色總是如此,他們帶著失去活下去,多像我們的人生,殘酷得清清楚楚。《在車上》是一則溫柔的提醒:痊癒的前提是受傷。我們不免想起生活中,那輛紅車抵達的盡頭,如上十二瀧町的風景,大雪覆蓋廢墟,沒有聲音的魔法時刻,我們能夠好好地練習受傷,好好地痛。
這是一部讓人想活下去的電影。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
作者|村上春樹
譯者|賴明珠
出版者|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2.01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