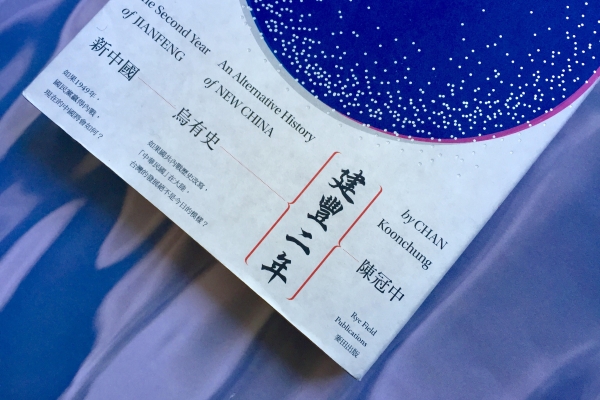恨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恨是不嫉妒──專訪小說家寺尾哲也《子彈是餘生》
「你要怎麼在外商公司裡,最惡毒地罵一個人呢?——就是罵他笨。愚笨,是最惡毒、最惡毒的形容詞。」
他常稱工作了八年的 Google 為 G 社。加上 Facebook、Amazon、Apple 和 Netflix 五柱擎天組成 FAANG,那是打工人薪資的頂點,也是當代台灣神話裡眾人夢寐晉升的神殿。在此,聰明成為基礎共識,愚笨則是喪失生存資格的髒字。
工程師寫的小說疊合自己走過的路,從台大資工到 G 社,捏塑出一群自尊心極高的角色們。
被霸凌時也是冷靜的。角色被關進廁所掃具間,下一秒就要被其他人的尿洗臉,只說:「可不可以讓我先把眼鏡拿下來?」灣區工程師們算起如果出車禍,公司保險金會發放多少錢。不確定是否包含年終股票,但結論是:「如果包含了,那就是一筆死得很值得的數字。」
「我覺得人都是冷靜的。」寺尾哲也談他筆下角色們的冷淡行事,那些幾乎過於理性的對白:「如果慌亂、表現出不冷靜的樣子,你就輸了。對這些自尊心非常非常高的人來說,是無法容忍這一面的。」
輸了
他也曾嘗試寫魯蛇,但自覺做不到。〈雪崩之時〉原先想寫窩囊父親與天才棋手兒子,寫了一整年還是寫不好,最終繞回了天才父親與天才兒子的故事。他熟悉自尊心高漲所撐出的人物內景,以及應運而生的魅力:「當角色天生就擁有一個內面性、和表面有所區隔,就會立刻產生美感。」
18 歲那年考入台大資工系,像是展開「輸了」與「不能輸」的漫長體會,鋪墊出他人生的內面。
就算電腦課還算喜歡寫程式,但完全不可能和高中就開始鍛鍊競賽的人比。籠罩於整本小說之上的 ACM 競賽,全稱為「國際大學生程式設計競賽」,匯聚世界各國的程式菁英,三人組隊,一台電腦,五個小時內用程式解決八到十三個困難問題。台灣至今最佳成績為第三名。
小說〈州際公路〉裡,明亨和主述者「我」回想起當年班上的大神介恆,在競爭出賽名單的選拔賽時竟遲到三小時。全班放下鍵盤,站起身哀求助教,一定要讓介恆考,同時也心知肚明:即便只剩一個半小時,介恆也還是會拿第一。
教授又不是白癡。誰都知道要是介恆沒選上,整場選拔都會變成歷史留名的笑話。介恆那時一副沒睡醒的樣子,頭髮亂得像被炸過一樣。全部人都等著他開口。結果他說:「我忘記了。」
明亨說,對,那次差一名被擠掉的人就是我。——〈州際公路〉
天才的存在超越規則,超越競爭,進而超越了我們理應在意的其他——而且他們並不在乎。祂們甚至忘記我們在意。
他說,其實剛入學時還存在幻象,好像努力就可以追上大神。「要到後來才發現,不,追不上。」「你會覺得自己是原始人。你看到電腦,知道按這個鈕可以開機,除此之外你什麼都不會。」
寫程式為何讓人感覺渺小?他說有個比喻大家應該能懂。
「比如說我現在要製造一台冰箱。這世界已經毀滅了,你,一個完全不會製造冰箱的人,現在要製造一台冰箱。你會覺得說,啊我怎麼可能製造一台冰箱?首先你要先從電線這種等級的東西開始造起,電線外面那種絕緣膜。我們需要先製造工具,用工具來製造工具,再用那個工具來製造工具,再用那個工具來製造工具⋯⋯重複無數次,最後才製造出冰箱。」
在程式裡鍛鍊也像人與神鬥,過程可歌可泣,但注定失敗。沒有寒暑假,沒有休閒娛樂,當然不可能有週末,就是一直寫、一直寫。他總結就是:「我那時候真的非常努力。用很變態的方式努力,也因此造成非常多精神上的傷害。那像是一個債務,我當時就是欠下巨額的債務,要慢慢還款。」
那段時間他養成焦慮的習慣。
「現在擁有的都不夠好,我一定要趕快再追求更多、更好。在忍耐的過程中,我必須要有無限催逼自己的能力。即使非常非常累、非常非常厭倦,都還要能夠認真做事,這個動力,就是要用焦慮感來催眠自己。」
把經歷寫成小說,工程師的筆名取做寺尾哲也,來自漫畫。寺尾是《鐵馬少年》的寺尾晃一,哲也是《黑子的籃球》的黑子哲也。運動漫畫裡總有天縱英才,但他們是在天才旁邊的人——他們被稱為最佳左右手、影子,各有才華,佔據的是近距離凝視太陽的視野。在那裡他們到底看見的是什麼?
彼此的刑具
台大資工系一屆 120 人,寺尾哲也說,像他一樣專注在競賽的人大概二十人上下。追不上大神,但又集體仰望,他們聚在一起——他引用朱宥勳的句子——成為彼此的刑具。
累了想休息,只要看到其他人還在寫,就會坐回電腦前。刑具貼合著身形與渴望,讓他們成為最了解彼此痛苦的人,竟有同溫層的溫暖:「那是知己的快樂。天底下只有這些人懂我,出了資工系系館,世界上其他人都不懂我們。」他們可能是戰友,但無疑是對手。對方的成長就是最強的激勵:「看到他們在努力,我就會願意繼續勉強自己。」
小說裡寫大神把凡人們逼入絕境,寺尾哲也說,那其實是虛構。
「現實生活中對於這些大神,我們就是仰望、頂禮膜拜。真的會有負面情緒發生,都是在和我們程度差不多的人。當他變得比我們好一點點的時候,那個妒恨就會非常可怕。奴隸不會妒恨主人,但會妒恨稍微過得比較好的奴隸——我覺得是完全地體現在這裡。」
他不是沒想過離開。
大三數位電路實驗課,期末報告所有人在系館熬夜,很多人熬到發燒,病毒一個傳一個,他們也只能接著遞送退燒藥,他說,簡直像戰地醫院。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有個同學講出一句千古名言,我也有寫進去。他就說:『難道我們以後會賺大錢嗎?』就是,太苦了,怎麼可能辛苦成這樣?那是不是代表,未來一定要獲得一些非常巨大的補償,才算是夠本的?」
小說裡角色們常提到錢,那些被割捨的青春,被踐踏的自尊,總得要換來一些什麼。〈健康病〉裡探視完跳樓後住院的同學,「我」立誓要賺大錢:「雖然不知道賺很多錢要幹嘛。但,我就只是想報復而已。」〈州際公路〉裡的公路旅行,邊開邊計算自己薪水有沒有比同學高,即使車子拋錨,已經是可以撥打白金會員專線、不須等待直接接通業務代表的大人模樣。
其實包含他自己,FAANG 的朋友們大多出身中產階級以上,成長過程不愁吃穿。但不缺錢,並不代表不渴望錢——金錢成為他們衡量彼此能力的指標,薪資單拿出來,他們依然是彼此的刑具。
問寺尾哲也,賺錢是對著誰的報復?
「有點想說是對這個社會的復仇,但⋯⋯與其說是復仇,不如說它後來就會變成像是清教徒的那種習慣。你刻苦生活,刻苦工作,就是一種很強、很值得被推崇的事。」那無法對準目標的仇恨竟回頭向著自己。
想起一個 G 社同事成天為薪水焦慮(即便已經比台灣中位數高很多了)。「你說他真的需要那麼多錢嗎?他的生活很簡單啊,吃吉野家、松屋。有天他和我說,哪天如果真的賺超級無敵多錢,他就要去買全套 MUJI 的傢俱。我心裡想說,有很多薪水只有你五分之一的人,都去買全套 MUJI 的傢俱了呀。」
追逐著無上限的金錢來證明自己,但又勉強自己成習慣。終於賺到錢時,他們並不揮霍,而更在意如何用最少資源行最多的事,慣常忍耐,把痛苦的耐受轉為成就的指標。「我們彼此都會互相監督,如果有人買了 BMW,大家就覺得不上道、不入流。」搬運公司零食飲料、假日還去公司裡用洗烘衣機以顯節制美德⋯⋯彷彿神祕的基因流傳,他看許多剛來美國的資工學弟妹也有相同習性。「會覺得說,哇真的好像看到以前的自己(笑)。」或許,忍耐的慣性也會世襲。
想起〈州際公路〉裡,汽車拋錨在 middle of nowhere,明亨與「我」即使撥通那隻白金會員專線,依然得在無盡、寒冷的黑夜裡等待救援。故事收尾是這樣:「再忍一下下就好。再忍一下下。再忍一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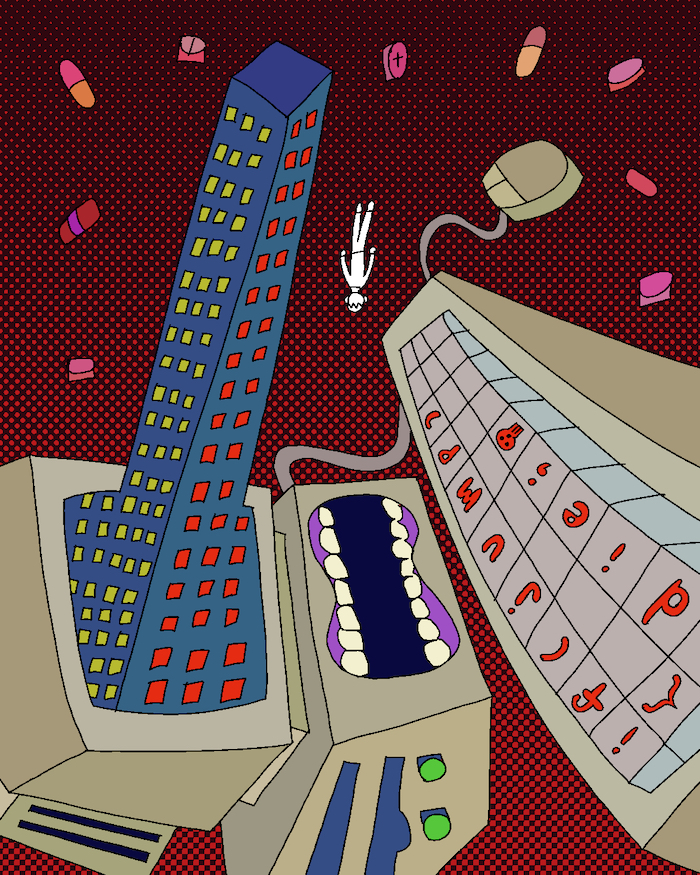
操控者
「說到底,除了介恆以外的人都是廢物。包括你,包括我。我恨不得所有人都能明白這一點。」
只有提到介恆時,她的眼裡有光彩閃耀。這種人我已經見過太多——越是自恃天賦,從小被師長同儕捧在手掌心的人,越會在明白自身與介恆的差距的絕望後徹底迷上他。
——〈健康病〉
〈健康病〉裡的小花,在準備 ACM 過程裡選擇從系館頂樓跳下來。也是在大三,寺尾哲也經歷了系上同學自殺的事件。聽說隔兩年,又一個。
短篇小說串起《子彈是餘生》,寺尾哲也描寫的世界觀也更為完整:這裡不只有死亡,也有愛慾,互為養份。如同小花在跳樓前,大一女舞舞台上的過度努力;又或是〈渦蟲 ∀〉裡被霸凌的「我」回想被吳以翔弄、尿在臉上時,竟然勃起。
現實生活裡他也愛過大神。
智性戀對聰明的迷戀,連結了絕對的性感,「這也是我在生命當中觀察到的。大家會覺得那些程式競賽的選手非常具有性吸引力,是因為他們非常非常聰明,而不是因為身材或長相。」
這種看法在主流男同志圈,不免有些審美孤單。但想想還是要對自己誠實,那些會讓人性奮的本就不只是身體:「我常常覺得,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去重訓?與其重訓,為什麼不去練練你的腦?你說重訓可以老了之後有肌肉,做數學題還能預防老人癡呆。你怎麼不怕你老了之後癡呆呢?」
除此之外還有更急迫的。
「你需要他來救你。程式作業有一個特性,儘管你已經寫對 99%,如果找不到 1% 的錯在哪,就等於 0 分。你會陷入一個非常焦急、悲慘的狀態,你只能去求他:哎呀我現在遇到這個問題,怎麼會這樣啊⋯⋯你們之間就會有強烈的權力關係。你無時無刻都需要人家的拯救。」
不斷向神求取足夠活下來的聰明,這樣的權力關係延伸出書裡貫穿的主奴關係。敘事線從主與奴的觀點交錯,讀者直到最後才領悟:原來擁有霸絕眾人能力的大神有可能是性愛裡的奴嗎?介恆原來一直是想被踐踏的。
從國中開始寫同人文,寺尾哲也以熟悉的 BDSM 翻轉「誰在上面」的權力關係,交織出小說的高潮。他用帶點科普語氣解釋:「其實主奴關係裡,奴是比較佔主導地位的,會由奴來決定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不能做。」即便大神有被霸凌的過往、在性愛關係裡表現為奴,他在精神上還是操控了世界,操控了他的主人。
「你假裝我當你主人就可以解決一切,可以拯救你的一切。你一直這樣假裝,連我都差點被你騙去。」——〈渦蟲 ∄〉
而主人即使拼了命要成為他心裡的主人,依然無法阻止介恆去死。
許多人第一次認識寺尾哲也是 2019 年他以〈州際公路〉拿下林榮三小說獎第二名,那時,介恆就已經死了,而這個死對許多人來說難以理解。小說家林俊頴在評審時提出疑問,「小說核心人物『介恆』為什麼跳樓自殺?」郝譽翔則提及,「如果是寫一段同志情誼,那麼自殺的設定,就顯得有一點俗套。」
我好奇他怎麼看評審的看法。
「李奕樵講得很好。他就說,要是可以這麼簡單就推理出為什麼想死,他就不是天才了。」
長大了
但這都只是小說。當年眾人仰望的大神原型人物,如今其實也就是個快樂的 G 社工程師罷了。大神看完小說,並沒有特別說什麼。寺尾哲也懷疑他覺得文章太長,可能根本沒看完?
現實生活裡隨著年紀漸長,極端的關係,無論是愛、恨、依賴,也都漸漸消退。
「我覺得大神們承認了,承認自己就是比別人好。而我們現在可以工作賺錢,已經不那麼焦慮了,地位就比較平等。」從仰望到平視,他慢慢清還過往積累的「債務」,那些戰地醫院的風景也能拿來說笑。「之前那些努力,雖然造成很多副作用,但是是有成果的,讓我們的關係更平等。」
工作後,即便時常自主加班,但壓力比以前減輕許多。他有點苦笑,「台大資工系真的是最辛苦最辛苦的,工作完全無法跟它相提並論。」有個主管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爸、一路升等到許多人一輩子無法達成的 L7,但至今,他還是會做回到台大資工系的惡夢。
競爭裡很難釐清努力和勉強的分寸。「那時大家都還不知道,到底要多好,才能活下來。」
他第一年進 Google 時,有個同事分享自己使用公司提供的心理諮商服務的經驗。帶著強烈的冒牌者症候群走進診間,當諮商師不停說「You’re doing fine. You’re doing good.」 時,同事只是一直哭一直哭,哭到停不下來。
「我就想說,哇,這是一個好棒的小故事喔。這就是我們的心靈寫照。」
他說,那句 You’re doing fine 之所以發揮了作用,是因為生活裡永遠沒有人會說這種話。
我問,即使你創造出一個冰箱,也不會有人說這是個好冰箱嗎?
「不會啊。你創造出一個冰箱之後,人家就會說,你這個冰箱不夠耐用啊,門怎麼拉一萬次就會壞掉啊?你就要開始研究怎樣可以讓門拉兩萬次(笑)」
兩年前他還在日本 G 社,起床時突然頭非常地暈,暈到睜不開眼,被救護車直送到醫院,診斷出神經炎。痛苦讓他警覺,剩下的時間是有限的——那些追求,職位的晉升、金錢的遊戲,突然變得不那麼急迫了。
「如果我現在死,我會有非常大的遺憾,就是我還沒有把書寫完。」
半年內他辭了工作,專心磨練小說技藝。其實中間斷了很長一段時間不寫字了,是 2015 年調回台北,隔年重新開始落筆。他加入想像朋友寫作會,與其他人頻繁交流,像是又回到一起準備競賽那樣。起初他不太敢寫灣區工程師,怕讀者覺得太無聊,是寫作會同伴和他說:這很有魅力、你要繼續寫。新夥伴間接催生了老朋友的故事,他感謝李奕樵的磨練與鼓勵,又稱林楷倫是「專門奉承我的朋友」,但至少,寫作日常多了一種可能的聲音:你很好。
離職讓他稍稍能脫離天梯的競逐,多了旁觀的餘裕。粉專裡有次他寫學歷大戰中紛擾的「純血」論,覺察自己身上也有的優越感,因為曾經痛苦過,觀點裡留下餘生難以抹滅的階級印痕。很多時候,優越感浮現其實是因為缺乏安全感,需要確定自己更有發言的「資格」。
他寫,感受到心中的鄙視鏈又開始蠢蠢欲動時,他個人的小訣竅同樣是對自己說:「我已經夠好了。」(I am good enough.)
他和書中的角色一樣,再活一次,也還是會讀資工系。角色背負著命定輪迴無法逃脫的悲劇性,但寺尾哲也的義不容辭,似乎參雜了留戀。他說,唸資工一是可以賺錢,二是符合興趣,三是可以寫:「它可以賦予我大量寫作的材料,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把痛苦寫得晶瑩剔透,好像那些忍耐又有意義了。
《子彈是餘生》
作者|寺尾哲也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時間|2022.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