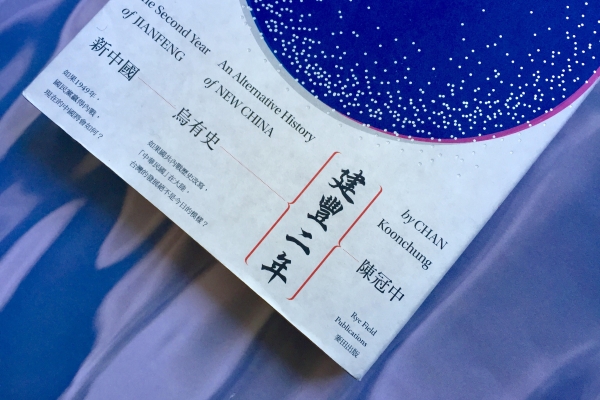女中學姊的直播開/關:馬欣對談鄧九雲(上)
甫在今年五月當過 BIOS 封面人物的鄧九雲,六月出版了她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暫時無法安放的》。當被問到,如果要辦一場對談式專訪,想跟誰聊聊?她提及景仰了很久的馬欣,覺得兩人都能懂某種寂寞:「我讀她寫給 SNOOPY 的查理布朗那篇〈無用之用〉,讀到哭了!而且很佩服她用書信的體裁來寫人物,那篇真的好棒!」
我回想自己認識的馬欣,不確定該不該用「寂寞」來形容她。有一回遠遠過了晚餐時間,我們在戲院旁的麥當勞巧遇,像兩個在平行地道裡、透過涵洞彼此望見的寫字人,為了趕場啃著麥克雙牛堡。那天我看的是文青女神自導自演(自嘲)的法國片,她則要看《國定殺戮日》,關心完近況又各自潛行,回到只有一人的星光票滑水道。這樣的她,是寂寞的嗎?我還真不知道。
但我知道,這兩人對談會很有意思。我只是沒料到兩個女生一聊開,我這個負責引導話題的主持人,幾乎沒有插嘴的必要了。從童年、成長、創作到面對的環境,這兩個很不一樣又能「懂」彼此的創作者,一見如故。
太早得知真相的童年
作為一個寫作者,馬欣幾乎是「享受著」離群索居的生活。而這源自於成長經驗,也源自某種老靈魂式的、早熟的憂慮:「小時候看哆啦 A 夢,總覺得故事裡的一切終將會、或根本已經是過去,因為從一開始就預設了分離的成分。」這讓她忍不住一直想:結局之後會怎樣?機器人會被汰舊報廢嗎?或是被升級成 2.0?「如果變成 2.0,那大雄又會怎麼看他?」
這樣的馬欣,說自己長大後要嫁給查理布朗,讓媽媽很憂心這孩子的審美觀出了什麼問題?但她的共鳴來自於:查理布朗總是在角落思考著自己的「人生大哉問」──聽到這裡,九雲補充:「小丸子也是!」──「但小丸子的討喜度超越了這些,又會撒嬌賴皮,就比較無害性地過去了。可是大雄跟查理布朗不會這些取巧,所以大家才替他們憂心,好像沒綁好安全帶就坐上雲霄飛車。」
妙的是,文章發表後發現,很多男生都喜歡大雄那篇,「就算我們認為很成功的男性,內心仍有個大雄,不知道該走哪條路好,恆常覺得孤單。」這樣的孤單卻是馬欣從小,就從卡通的世界領會的。「譬如那時候看《小甜甜》,根本是每天看伊莉莎怎麼欺負她,或像是《喬琪姑娘》中的主角曾和一個有錢人私奔,結果火車上一個老婆婆冷冷地對她說:這個穿緞面襯衫的男生,不可能永遠跟你過這樣的日子⋯⋯」
她說當時很震驚,覺得我才幾歲,為什麼就要告訴我這些?「我不過是看個漫畫而已,為何要這樣?」但現在回想起來,那正是日本文化的思維,「日本漫畫不像童話,他們一點都沒有要騙你的意思。就像宮崎駿,一再地強調要堅強,不管怎樣都要活下去,面對未來要好好準備,就這樣預先一直打強心針。」
鎂光燈與爛肉
但說到宮崎駿,生在不同世代,成長經驗也不一樣的鄧九雲,果然看法就完全不同了。她解讀《龍貓》比較像給孩子一個夢,「雖然 Totoro 出現了又離開,但那是讓你抱著這個夢繼續下去,繼續堅強。」
外型出色、高䠷的鄧九雲,從念女中時代就是風雲人物,名列前茅的成績更讓她高中三年都很清楚,自己的一舉一動正被注目著。我請馬欣說說在專訪前,閱讀九雲的文字有什麼想像?她說她的直覺告訴她,這一定也是個待過女校的女生,才會對女生觀察這麼細微。「實際見面果然沒錯,像個很可愛的女大學生,內在通透細膩,外表又很活潑,而且在女校待過的那種保護色,其實很熟悉。」
九雲一聽連忙追問,得知馬欣唸的是崇光,她自己唸衛理,兩人聊起女校的種種,包括二十四小時和同學長時間相處,「一旦被排擠,就是世界毀滅的感覺」。還好她們都安然存活下來。「純女生的環境,因為不再有男生時時打分數,大家就變得很奔放,但我們這性別又像是隨時以為有個舞台,有鎂光燈在旁邊照⋯⋯」馬欣形容這像在直播,九雲狂點頭,補上自己的經驗:「很可能我今天做了什麼,明天就被傳到連國一都知道,而且完全不是原來的樣子!」
這樣的直播揮之不去,到了大學時代,反而給九雲留下了些許遺憾。「上大學之後,突然從隨時被矚目變成沒有人在乎我,一下子很難適應,就都自己躲起來。」加上衛理的訓練讓她連考上政大了,還覺得「沒上第一志願讓學妹失望了」,一直努力拼轉學。「現在想想真的很莫名!」馬欣笑得忍不住補刀:「人一旦經過直播狀態就很難關機啊!即使可能已經沒再被 follow!」
九雲想像中的學生生活,是男女校辦聯誼,或上大學玩社團,這些她都錯過了。但馬欣這時候補充:「即使沒錯過這些,也可能只是像爛肉一樣躺在那邊!」她說過去在世新,因為大家覺得課外活動比課業充實,真的在教室碰面了,也都是爛肉狀態,就「嘿你好啊爛肉」這樣。她的社團經驗則是:一開始參加新聞人社,發現每兩天要發一篇稿就逃跑了,接著去泛愛社,但職前訓練的時候要互砸蛋糕、夜唱和在河堤邊玩捉迷藏──九雲插嘴:我就是想過這種生活沒過到(激動)!──「這種腎上腺素高漲的狀態我真的沒辦法。」最後是在國父遺像下面,發現一個小小的辦公室,裡面的人都在下象棋、玩大老二,「我心想這真是天上人間,一問之下對方說:『我們是國父思想社』後來幾年就都在那邊。」
寫實的劇本最能打動人
那幾年,馬欣他們沒聊過一天國父思想,只是打打塔羅牌、算算紫微斗數,但都成了很好的朋友。這讓九雲更羨慕了。對馬欣來說是逃遁的,對她卻是錯過。大學時代的鄧九雲,一度加入模特兒公司,但最後待不下去,「在那個環境裡,必須把自我意識丟掉,比如那時候才二十歲,但模特兒是男女生一起換衣服,走秀的時候只貼胸貼跟丁字褲⋯⋯」她形容進了那圈子,就像被丟到非洲不能回來,渴的時候就非得喝那些水,「而且要在很短的時間內適應,還要犧牲很多東西,比如超過三天後的聚會都不敢約,因為要隨時 standby。」
沒辦法長期這樣「關掉自己」的鄧九雲,改走演戲的路,近年更開始創作。原本那顆直播鏡頭,變成觀眾在特定時間空間看向舞台的視線,或讀者在自己的世界裡翻開書本,和她築起的連結。而不論是演員身份,或寫作帶來的充實感,都讓她變得自信、自得。「劇場的環境比較隨性,而且演出的時候有角色包覆著,反而有種安全感。」
然而說到台灣劇場,九雲又有好多無奈想傾吐。跨足舞台和小螢幕已經十三年的她,談起劇場界的問題,跟我們熟悉的國片界真的很像。首先是好劇本缺乏:「寫劇本需要時間,需要好好發展,但現在根本沒有給編劇足夠的時間。」她舉電影《藍色情人節》為例,說那樣的故事像黑洞一樣可怕,「它非常簡單,但可以寫實到讓你很痛,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寫出那樣的劇本,因為寫實的東西它『耐』。」就像她喜歡是枝裕和的電影,或艾莉絲孟若的小說,「心理寫實的東西,最是打動人。」
但不論小說、戲劇或電影,現在許多創作都在靠形式挽救,「東西不夠好,就用形式去加分」,她說其實演員最想演的還是寫實的東西,「為什麼選擇舞台劇,就是因為如果夠好、夠完整的劇本,會讓你真的像做了一場惡夢,真的覺得『經歷』了。而電影電視不可能這樣。」這樣的劇本在台灣卻很少。除此之外第二個問題是「時間」,而追根究柢是市場的關係:「台灣太小了,做一個戲頂多就演幾場,能選的場地也有限,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有時候甚至是:場地檔期已經先搶好,再來想要演什麼,在兩三個月內硬產出一個東西,還要趕上輔導金的期限。「每個環節都被壓縮,演員當然也很慘,很可能演出之前沒多久才拿到劇本!」她笑著說,所以下一次看到演員忘詞,真的別太苛責,可能根本不能怪他們!
「歡迎加入自殺突擊隊!」
聽到劇場界慘況,我想起上次在專訪裡,馬欣也形容現在的文字產業很「寒涼」,有志投入者要先培養出「不至於清貧,但很有彈性的生活」。這次對談到一半,馬欣一度看著對街的龍門客棧餃子館看到出神,一回頭才解釋:「我對方便的食物有一種迷戀,而且因為山東人血統,可以吃大餅饅頭配乾辣椒,覺得那麵粉越嚼越香,就好開心!」
這讓現場所有人都嘖嘖稱奇。九雲忍不住說,她非常重視吃,拍戲的時候如果拿到難吃的便當,心情會很差。「我覺得一整天工作下來,吃就是第二重要,再來就是睡覺。這兩件事一定要處理好。」她還會事先研究附近好吃的便當,然後偷偷跟負責人建議。但馬欣補充說明,她是為了維持「盡量少社交,不需要跟別人 team work」的狀態,所以儘可能用減法生活。「這是我從小立志要達成的目標,我從幼稚園到小一被霸凌,就是因為都不想講話,那是天生的本性。後來為了不被霸凌,跟大家維持一個和諧的關係,但內心那個想獨處的慾望非常強烈。」
於是二、三十年來,那個慾望被壓抑到如果可以獨處,食物的慾望可以擺在很底層,有時候肉包子啃一啃就繼續打字。「我看到村上春樹說,他是為了維持現在的生活方式所以繼續寫作,覺得心有戚戚焉。」聽到這裡的鄧九雲若有所思地說:說不定,這也是她在追求的。「不然我幹嘛寫那麼多東西,而不繼續瘋狂地演戲?我其實常想如果可以靠寫作,不管寫什麼,只要能資助我的生活,我就可以更在自己的世界裡,不用跟人接觸。」
然而聽到這我忍不住插嘴,因為兩次專訪(加上之前聽演講)的經驗讓我不相信馬欣是個不喜歡說話的人。她想一想,解釋道:「是這兩年出書之後,我才必須習慣說話的頻道,或是在這樣的場合(專訪現場)我才能打開,不然平常如果兩三天不跟人講話,我是 OK 的。」但九雲又問:「你還當記者耶,如何能夠孤獨?」馬欣說記者是丟球給人家,就算在採訪、探詢你,但並沒有建立一個互動關係,「這對我來講是安全的,我是個隱秘者而你在亮處,這符合我的本性,而且有個合理的觀察的旁觀席。」
何況繼續接採訪,是因為不能只靠(影評)稿費維生。「要有演講以及接案子,那些都沒辦法放掉。」聊到文字工作者的辛苦,九雲也提到香港的稿費相對高,因為地緣關係,那邊的商業發展還是很蓬勃。馬欣則感嘆地說,當然我們都有收到中國香港的邀稿,但內心情感上還是想為台灣多寫,只是稿酬薄,相對量就要大,算一算每個月要生產好幾萬字,還付出了時間分配永遠一團亂的代價。「一直在抓時間、偷時間,而且無法避免變成夜貓子。」她說靠寫作維生,根本像自殺突擊隊,還要過很清貧的生活,「但如果考慮清楚的人,歡迎來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