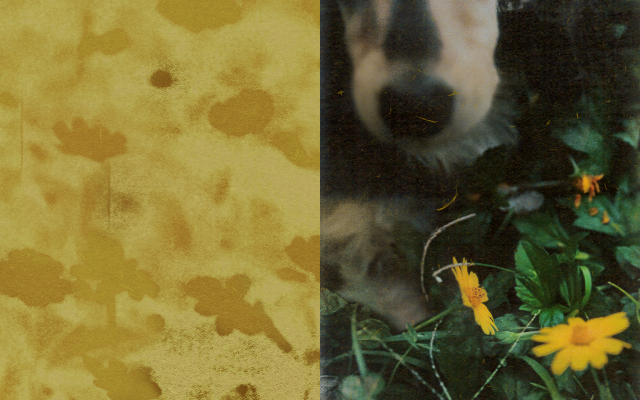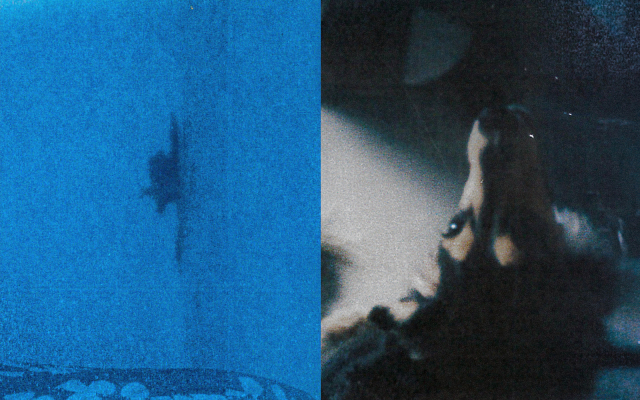思凡
年紀漸長,讀書範圍日益廣泛,或許不能直接等同於眼界開展,但確實領略了某些世情,如偶像失色之必然。多少以為偶像者,其實不過泥雕陶塑、難堪太多聞問,那些數十年如一日的題材與筆法,若非生活於真空(單純當然也是一種幸運,只是值此亂世,不免令人犯疑),便只是以故作天真的姿態,矯飾無所長進的事實,恍然大悟的時分,讀者往往比偶像本身更覺悲哀難擋,畢竟有些一次即是沒有的東西,就這麼順理成章的葬送了。
然而,頓悟的魔術時光所以魔術,不只因為照妖鏡的特性,更珍貴之處在於,有時它並非什麼寶器而純粹只是鏡子,一瞬迴光返照,即令讀者瞭然,經典原來只是經典,一切沒有錯認、沒有誤會、沒有必須洗盡的鉛華,自然沒有必須遮掩的瘡孔;讀者不過是在一個平凡日子走進章句,再安然步出,於此進出之間,我們卻有了渾然不知的背負,虛構與現實的遙相呼應,如一只晚冬的僵死蠶體,至真正遭遇的一刻,春芽才狠狠刺穿你的胸膛。
所以重讀《紅樓夢》,我才有了這樣的理解,經典既是語言已盡,卻又永遠無盡;身為作者,或許一人一生僅此一次,但身為讀者,卻能為它百轉千回,不死不已。此去經年,我身邊的她生他死、他來她去,繁盛蕭條皆有了體驗,所以好像更能懂得悲劇之為悲劇,以及隱埋於核心的、喜劇的稀微可能。
如是我聞:書中要角,既然藉著眼淚回了魂,那就不只讓他或她們活下去,使他們承擔我的背負,突破我的重圍。當我翻閱紅樓或者自己,既是知音世所稀,既是傷害勢不可免,既是所愛被愛時有錯過,既是云空未必空者,就讓她形如靜雪奔如流風,就讓她的來日大難皆當喜歡。
因為妙玉。或者不因為妙玉。而有此詩。
妙玉思凡
.來日大難
窗外分明有人。分明
有影蠢動於欲雪的晚天邊緣
讓院落提前空寂,鳥獸蹄印
為遲暮緩慢覆蓋
漫漫淹過我終年駐苔的胸膛
誰見得此處山勢頹唐?由此去──
誰由此都無法抵達月色最恨最滿的
我的心。自己對自己的誓言難能成為路引
一片林野蕭然,我燦美的惡意
生出石筍朝你們大張雙臂
究竟誰說:「來日大難」?一句孤語
意識裡反覆迴盪。彼時夜色如蜜
願誰人步履微微
欺近我小而遼廣的廊室
老燭火覆滅又生,芯是永遠剪不盡的
念頭,未曾吻過的吻。拆不開的我的雙手
掌紋越繞越緊,包纏命運的琥珀
松柏內越繞越緊,越冷淡
越親密。我的思量凝結在冬天的核心
睡──行將破土的眼睛,思量帶傷的猛禽
翎羽小小,遺留的血色聚為寒梅
花色同我心意一般汩汩,勃勃生機遙有呼應
靜──但聽窗外確實有聲
.皆當喜歡
只是那些動靜我仍抱持疑心
畢竟孤獨來自胎裡。這技倆
只比愛陌生,較欲望嫻熟一些
某些夜裡,我想你們
在月與水的中間不斷權衡距離
手勢底暗藏絃聲各異──音韻耽柔的
愛我;激越的要我愛。但你們
卻總在同一處留步、止歇
甚或斷絕為門外懸置的謎(或者
你們以為是謎……),企想以未盡的歌譜
勾引門內年輕的知音
殊不知萬般算計都惹我傷心。
每逢人間節慶,街市萬燈如湧
狂野的大水迢遞過荒涼的視野
流螢急急奔向天際,張揚晚秋可能的雨
雨落前我衣襟稍微鬆解,半裸的心
在燈下鋒芒落盡,孔竅以筆墨填滿
一只銅鏡反照我胸裡所有眼睛
梅花的殘枝倒插雪地,成為新鮮的暗示──任你們
是郎是匪,我都可以由此去
去哪裡都可以。是我說的:「來日大難。」
來日何來?不如今朝月色正好
任憑舊年雨杯中滂沱
窗內無人分明
2011/08/15 初稿
2013/09/12 二稿
作者簡介
台北人,謙沖與桀傲的二十七歲,政大中文系、政大新聞所畢業。
髮色很淺,近視很深。有金牛座該有的不該有的一切與一切之外的特性。愛過幾個人,恨比愛更加蓬勃,更近於搖擺。
閱讀小說散文與詩,有時也寫,但無關乎是小說家、散文家,更不是詩人。得過一些無關痛癢的獎。提幾個對我發生重要影響猶如核爆的創作者比如:顧城、黃宜君、蘇童與駱以軍。
如果我的生命必須被歸類,目前為止仍舊屬於一事無成那一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