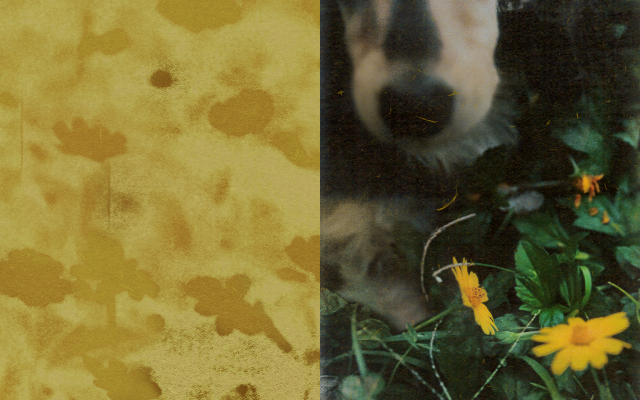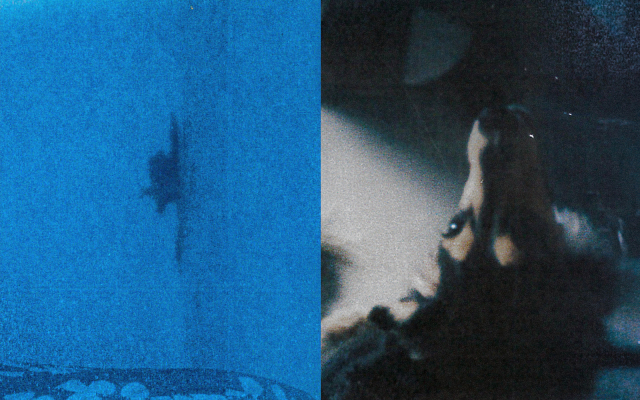自由
多年以前,彷彿也是一個微寒冬日,我和某窩在宿舍裡看著《The Shawshank Redemption》(刺激1995),無燈的小室窗簾極薄,窗外松風霜冷如針,唯有螢幕的影影綽綽提醒著時間流逝。
我清楚記得,在那個寂寥冰冷的木質空間,螢幕底間歇的喧雜,與窗外車輪輾過的爆裂雨聲意外形成一種真空,它奇異的應許了時常不被應許的沉默,在我們的不對視與不交談裡,銀行家一夕樓傾,成了百口莫辯的階下囚,從一開始的憤懣不平到忍辱負重,情節迅速推展,所有背景音幾乎消弭了,那時的我並沒有太注意故事,我單純以為,既然發生在監獄外的錯認、與監獄內的冤枉來得如此輕易,最後必然從善如流,沉冤得雪。
彼時我更在乎的是,我們並肩而坐,專心於同一個方向這件事,即便不對視、不交談,亦能肯定彼此身處同一個監獄,數算著同一份毫無意義的曆日,那份安全感厚實至,我自願將湯匙鐵絲與相類尖銳物全然棄擲,作一個甘心遭囚之人,我自願撳滅所有燈鈕,任窗外風也瀟瀟雨打芭蕉,我以為門內涵融了整個世界的自由,除此之外別無他是。
事隔多年,當我能以一種更基礎的姿態重看此片,才想起當時確實為了一幕澎湃動心,只是當時無以名之。既不是主角拿著利器鑿挖泥牆的堅定,也不是好友出獄乍見藍天的感動,那是──利用己身專長而受到獄方信任的主角,趁警衛一時不察,將自己反鎖辦公室內,好整以暇的挑揀黑膠唱片,那種精確與嫻熟必然出於一種長期的中產階級教養--接著,於一片安和之中,《費加洛的婚禮》的女高音拔尖而出,劃破了囚犯與世界的隔閡,他斂目而靜,享受著暫時的真空,而他們先是悚然、隨即順著音色望向迢遙的天空,倦鳥安然,無喜無悲。
這一幕才真正打動了我。
那畢竟是多麼珍貴的一瞬,理解有些東西向來只在門外,即便此去經年,因著各式自願與非自願的理由束手就擒、就坐、甚而偶有慷慨就義的壯烈,但是「自由」從來不是假想能及的產物,那橫亙於我與我們之間的,曾經從容最終困窘的沉默,是自由之不可得的確切證明,一旦我們成了我們,人與自由之間的距離即非我們所能觸及。
這也是為什麼,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為什麼冬雨依舊,卻再也進不去同一個房間,即便已經習於闃靜與幽暗,有些事情昭然若揭,當我扭動門把如啟動一個宇宙,那畫面快速遞換歷歷如昨:
「我到今天也不明白,這兩個意大利女人在唱著什麼。事實上,我也不想去明白,有些東西不說更好。我想那是如此的美,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美得讓你心痛。我告訴你,那聲音飛翔得比在這個灰暗地方的任何一個人夢想的都要高遠。像一隻美麗的小鳥,飛進了我們這個灰色的鳥籠,讓這些圍牆消失了,在那一刻,每個囚禁於蕭山克監獄的囚犯,都感到了自由。」——《The Shawshank Redemption》(刺激1995)
作者簡介
台北人,謙沖與桀傲的二十七歲,政大中文系、政大新聞所畢業。
髮色很淺,近視很深。有金牛座該有的不該有的一切與一切之外的特性。愛過幾個人,恨比愛更加蓬勃,更近於搖擺。
閱讀小說散文與詩,有時也寫,但無關乎是小說家、散文家,更不是詩人。得過一些無關痛癢的獎。提幾個對我發生重要影響猶如核爆的創作者比如:顧城、黃宜君、蘇童與駱以軍。
如果我的生命必須被歸類,目前為止仍舊屬於一事無成那一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