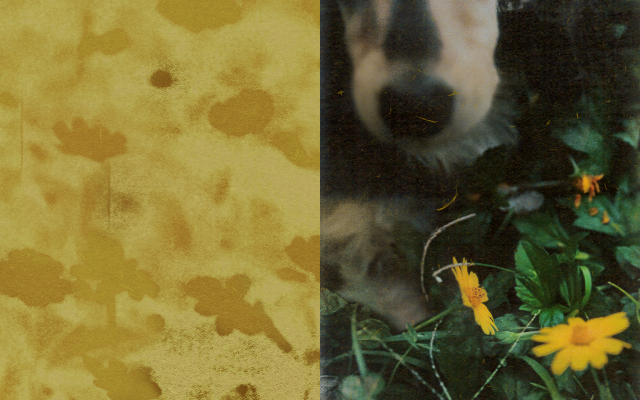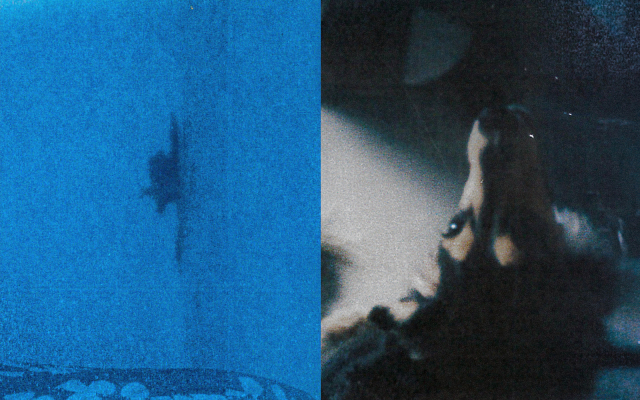讀畫
上個月、隔了不很久的 KTV 聚會裡,朋友a 笑說贊助這次活動一千元,因為「值得記念的第一幅畫賣出去了。」這個消息著實讓我們開心不已,只因知音難尋、藝術知音則更難,在此起彼落的祝賀與調鬧裡,耽於寫作的我們也若有寬慰。
對於繪畫,我的理解長期隔著一片毛玻璃,雖然我也曾是那個,拿著鉛條與軟橡皮,一吋一吋將維納斯雕出紙面的小孩;我也曾執著於色彩般配,致力填滿各種形狀,「色筆沿著邊緣密匝一圈後往內塗滿,染料便很難溢出」──並且為這樣道聽塗說的小技巧心動不已。
是的,我的作業必定細緻、精密、間不容髮。
但那些色彩我執、光影焦灼,反覆更換座位只為讓亮度更適切等等作為,其實都是隔著毛玻璃的理解。毛玻璃的意思是,你明知時間經過、人影蠢動,但實情如何──作者與我的,沒有對應,失卻情境,此種「理解」無非是機械式產物。
直到後來,不再信手塗鴉、提筆作畫(連一張卡片也逐漸慳吝),不再將博物館美術館作為假日首選,名家經典多半流於工作素材的後來,當我逐漸嫻於抽象,樂於思索,嘗試以一種第三者的角度審視生活的後來,才發現原來「抽離」,致讓我身更加涉入。
如果單從粗淺的感情加以解讀,從前對於梵谷的動心也極為自然,那些或暴烈或溫柔的場景,確實反照出少年時期的無畏和膽怯──藍紫星空飛旋流轉,黃花狂暴一如怒目,幾近死滅亦欲掙扎的鳶尾,群鴉低飛過騷亂的麥田,指引我幾多年後,還能從容辨認出兩個翻閱舊書的身影,於頁與頁之間留下翻汙的指紋,那個下午安然靜好,絲毫不知山雨欲來。
研究所的日子,因著內外夾攻的各種理由,我逐漸傾心於慕夏,暴烈溫柔或許風韻猶存,更多時分卻是一層一層洗淨鉛華,四季天女照樣眉眼昂揚,衣袖翩飛,背景還是暖的,人物卻少見曲折、亦無張狂用色。
所以我理解了,對於作品的動心,必然來自生活與物件之間的反覆參照,我的抽離、你的介入,使得橫亙在眼前的毛玻璃頓時破碎,意義歧生。
我也理解了,何以從梵谷到慕夏,多年前的詩句歷歷如讖:「像一隻女鬼拿青苔抹臉/越抹越深越淡。」我終究不再是那個非黑即白的善良者了,一切多麼清楚並且接受,那些逐漸遞進的層次,屢屢後退的界線,那些歡愉、爭辯、憤懣與悲傷,猶如註定失卻的防波堤,光陰翻湧,如露如電之間,它終究要一點一點的崩毀與佚失。
作者簡介
台北人,謙沖與桀傲的二十七歲,政大中文系、政大新聞所畢業。
髮色很淺,近視很深。有金牛座該有的不該有的一切與一切之外的特性。愛過幾個人,恨比愛更加蓬勃,更近於搖擺。
閱讀小說散文與詩,有時也寫,但無關乎是小說家、散文家,更不是詩人。得過一些無關痛癢的獎。提幾個對我發生重要影響猶如核爆的創作者比如:顧城、黃宜君、蘇童與駱以軍。
如果我的生命必須被歸類,目前為止仍舊屬於一事無成那一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