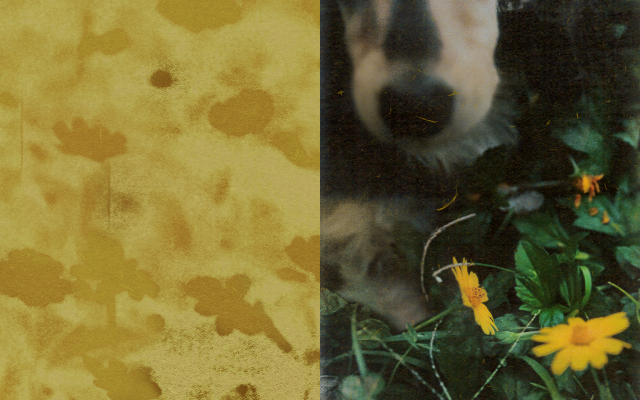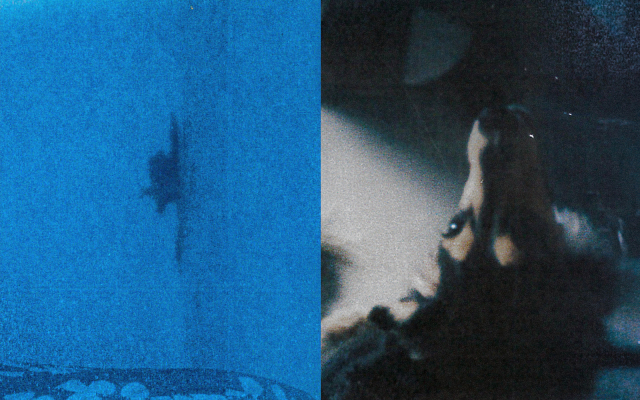時光之硯|高第聖家堂(Sagrada - The Mystery of Creation):一百年的遺願
去年底十二月,我與家人到巴塞隆納去遊覽了一星期,在這之前,去過的歐洲城市雖然不算多,至少對想像中的「西洋古典都會」、「歷史文化大城」算是自認見識過的。沒想到,巴塞隆納的視覺魅力密度,觀光美食熱烈,和地理優勢之珍稀,讓我又開了新的眼界。
怎麼說呢?比如光是從一條大道南下,二三十分鐘的步行路程,就有沿途的壯闊林蔭街景,寬敞的公園襯著噴泉藍天,商店街的人潮媲美饒河街(萬頭鑽動舉步維艱啊),列名世界遺產的瑰麗建築好幾間。而這條路最後,還直通到海港前,看著鷗影飄灑千帆間,心中除了舒暢,對這座城市的得天獨厚,更有三分的嫉妒。
比如這短短一週裡,我們接連參觀了:畢卡索美術館(並且發現這位總是畫我們看不懂的抽象畫的大師,原來早在十五歲就畫出我們看得懂的、非常成熟的油畫),達利美術館(發現我鍾愛的冨樫義博《獵人》的部份風格,儼然取材自這位怪才的手稿),米羅美術館(這就真的太難懂了!)——同時擁有這三個如雷貫耳的名字,該說這城市有多過份?
但它還不滿足。真正厲害的是,巴塞隆納幾乎可以說是:「高第的城市」。

安東尼.高第(Antoni Gaudí i Cornet)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加泰隆尼亞現代主義」(Catalan Modernism)最重要的藝術家/建築師。出生於西班牙雷烏斯,十六歲前往巴塞隆納攻讀建築後,這位大師終其一生都在這座城市裡,揮灑他的藝術奇想。他的風格,當然一點也不「傳統」,但和我們認知的「現代」——那種幾何的,極簡的,強烈的大色塊大線條大張力的建築又不一樣,高第崇尚曲線,師法自然,從樹木森林石頭中汲取靈感,而且非常注重採光。
光用說的,不容易想像,但真的到巴塞隆納走一趟,會發現僅僅相隔幾條街區,就有好幾座他的代表作隱身在路旁,讓人一看,就明瞭這位頑童是如何開心地在「玩」創作:深邃的奎爾宮大門(Palau Güell, 1886-88),玩具屋塗裝的文森之家(Casa Vicens, 1883-88),外星人巢穴似的(《第九禁區》裡的蝦族?)米拉之家(Casa Milà, 1906-10),還有一整面牆就是一部童話,上頭的十字如一把利刃插在惡龍背脊上的巴特婁之家(Casa Batlló, 1904-06)。
最後,在離開前一天,我們當然去參觀了聖家堂(Sagrada Familia),那座舉世聞名的,自 1882 年到現在歷時一百三十多年還未蓋完的老教堂。當地的地鐵,有一站就叫做「聖家堂」,老老舊舊的,就位在這近乎永恆的工地下方。步出地面,回頭一望,眼前那四座塔(從單面看只能看到四座)如螞蟻丘一般,像被風化過的外觀,和我在明信片上看過無數次的印象沒有不同。隨著人龍前往買票,付不低的門票費,我得承認在那當下,心中不是很甘願的。
沒想到,一踏進室內,那瞬間心裡的猶豫,一掃而空。
在我眼前的,是這輩子從未看過的景象。不只是沒在「教堂」裡,在任何建築中都不曾看過:黃色綠色藍色的光,水彩渲染似地,從窗外泛入窗內,成一塊塊斜斜的光柱,打在瓷磚地面、牆面、柱面。屋內的柱子,一根根帶著微微的弧度撐起穹頂,如枝幹撐起了森林,每個遊客走在其中,都像沐浴在彩虹裡。
.jpg)
這讓我想起了《阿凡達》。誠然,《阿凡達》對自然太過繽紛的描繪,是我一直覺得這部電影重量不足的原因之一,沒想到在現實世界裡,我卻看到那樣的風景被重現了。而且這一次,被震懾被收服了。
聖家堂的浩大工程,在 1882 年剛開始的時候,建築師並不是高第,然原本的設計者在一年後辭職了,而高第接手時,地下室聖壇的部份已經在建造中,他就保留這部份,並把地面上的設計全部換掉。從這時候開始,直到高第過世的 1926 年,四十三年間他幾乎全心投入,最後甚至就住在教堂裡的工作室。且因為這是一座「贖罪堂」,只接受信徒個人的捐獻而沒有公家單位、宗教官方的挹注,據說年老的高第,還曾自己坐在路邊募款。
聖家堂的特點,除了內部的燦爛廳堂,外部的十八根塔柱(其中代表耶穌基督的尖塔預計高 170 公尺,將使落成後的聖家堂成為全世界最高的教堂),還有三座繁複的立面(Façade):誕生立面,復活立面(又譯受難立面),光榮立面(又譯榮耀立面)。在高第過世前,整項工程只完成不到四分之一,三座立面當時只有誕生立面(Nativity façade)完成了大半。不過,高第其實心知肚明自己看不到完工,他的名言是:「沒關係,我的客戶(即上帝)不趕時間。」
於是在紀錄片《高第聖家堂》(Sagrada - The Mystery of Creation)裡,我們看到了攝影團隊前去採訪如今的施工者,包括總設計師、雕刻師、電腦藝術家、彩繪玻璃繪者等等。而在他們身上,最令人好奇的疑問是:參與一個延續「原作遺願」已近百年的工程團隊,是什麼感覺?
我想答案應該可以說:他們既是創作者,同時也是考古人。在最大限度上,這個團隊試圖挖掘,重現,或推敲當初高第的設計,包括各種模型、手稿,以及在西班牙內戰時期(1936-1939)被毀壞的真跡等等。在他們的工作室,就真的有個房間擺滿了模型碎塊,待他們重新一一拼湊,追回當年大師的願景。
另一方面,還有個迷人的角色,是來自日本的石頭雕刻家外尾悅郎(Etsuro Sotoo)。他在三十幾年前旅行到巴塞隆納的時候,愛上了聖家堂,從此留下來奉獻心力,雕刻一尊尊石像。他在鏡頭前說著流利的西班牙語(還是加泰隆尼亞文?),邊敲著石磚說:「其實,我只是聽見上帝旨意的人。像這塊石頭,你們聽這聲音,如果敲到對的地方,那聲響是不一樣的。沒有它(石頭)的允許,我不能雕刻它,它才是真正的大師。」
外尾悅郎視他的工藝為「還沒有開始,已經完成的作品」,他只是順著上帝的旨意讓它面世。過去的他是個佛教徒,非常嚮往「禪」的境界,但為了參與這工程,他必須學會「從高第的角度看這世界」。於是他改信了天主教。另一位設計師則說:高第的作品處處學習大自然的結構,他覺得人類不需要創造不存在的東西,因為不存在大自然的,表示它沒有必要。
而在 2015 年的現在,聖家堂已經完成兩個立面,除了誕生立面還有復活立面(Passion façade),但這第二個立面是後世的建築師荷西.蘇比拉克斯(Josep Maria Subirachs i Sitjar)在參考高第的手稿後,用尖銳剛硬的線條風格,不重其「形」而重其「意」地重現的。這當然引起了爭議。然,這「用現代的眼光重新詮釋」的企圖,對比於「絕對地遵從原意」,誰能說孰高孰低?更有趣的是,還有人形容聖家堂「像一座迪士尼樂園,他們一直在試圖重現一段根本不存在的過去。」

但也許更直接的,是不少人認為根本就不該繼續這工程,應該保留現狀成為古蹟。另外的爭議還包括:現在還未動工的光榮立面(Glory façade),完成後將是教堂大門,而根據高第的設計,在其前方還會延伸出兩百公尺的大道。但這一區早在數十年前,就已經蓋了樓房,若真的要照原定計畫,勢必得拆除兩個街區的住家,這樣的「都市規劃」與徵地過程,可以想見一定會引起波瀾。這一切既「社會」又「政治」的煩惱,想必是當年高第完全意想不到的吧?
紀錄片中,當然也提到高第過世的情景。那一天,衣衫襤褸的他在「下班」後,依例步行前往市區的巴塞隆納主教座堂(Church of San Felipe Neri)去禱告,沒想到在路上被一輛電車撞倒。路人不認得他,以為是流浪漢,耽擱了一陣子才被警察送到聖十字醫院去。當他的同事第二天找到他,傷勢已經無從挽救了。
高第的願景是,把聖家堂建為一座「窮人的教堂」,從最虔樸的出發點仰望上帝。現代的設計師則說,它是一首和平的讚美詩,要散播四海一家的概念,是把神性當做美學來崇敬的聖殿。當談到對未來的期待時,有人表示,聖家堂的意義不在完工,而在建造。希望直到落成的那天,每個人類都跟高第一樣,有著對神和對大自然的堅定信仰。在這建築背後的故事,是超越特定的時空和世代的。而它的存在,又證明了人類對純粹的「美」的追求,可以傳承不懈。

直至今日,聖家堂的進度約莫是百分之五十,而目前預計的完工日期是 2026 年(高第的百年忌)。亦即未來十年的工程,將等於過去這一百三十年的量。這樣的樂觀背後,除了有現代電腦技術(Computer Aided Design)的幫助加快了設計,還有每天數萬人次的門票收入,讓工程的預算無虞。
那天在堂裡,我清楚感受到一個充滿故事的歷史現場,和一個超成熟的「觀光景點」的有趣結合。待它真正完工的那天,將會是巴塞隆納——甚至全世界——的人們,多麼開心的一天?
【張硯拓】
1982 年次,曾任資訊軟體工程師、產品企劃師,現嘗試寫作。經營部落格【時光之硯】多年,文章以電影心得為主;信仰:「美好的回憶就是我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