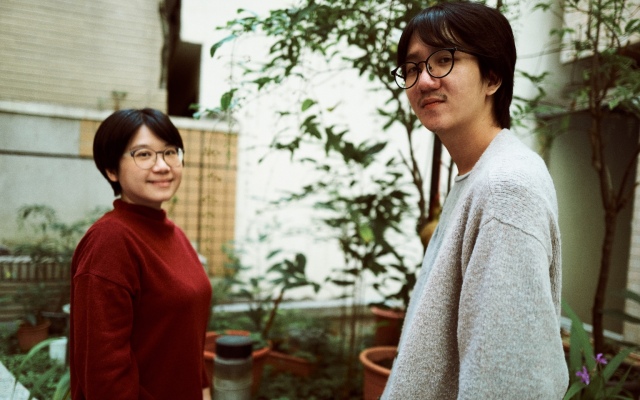流動的窗口——言叔夏的負面書寫與負片風景(上)
「天亮以後我就三十歲了。如此而已。」──言叔夏以這句話收煞了她的名篇〈白馬走過天亮〉。雲淡風輕,千帆過盡,但仍暗暗浮露了暴風雨和十年漂流的痕跡。與此篇同名的散文集於二〇一三年出版。初試啼聲,讀者驚艷;若不誇稱「事件」,也是一道淺淺「刀口」。黃錦樹所作的序,預示了稍晚一場大規模的散文論戰;更晚一點,中文系與台文系的彼此問詰,亦可在言叔夏這本散文集裡讀出癥候與蹊徑──不過,那仍是言叔夏自身獨特的症狀與路徑。
一、港町,山路,療養院
十八歲出門遠行。但言叔夏更早就在原地離開了。她在學習指認家鄉的同時,異常正確地把家鄉誤認為異鄉。
言叔夏出身林園,高雄與屏東交界的邊緣小鎮:比(愈來愈像台北的)高雄更南,或許甚至也比(以春天吶喊與國境之南而聞名的)墾丁更南。她來自於、而且似將恆屬於正午烈日底下漆黑得發亮的南方。這早已是她的馬緯度無風帶。
成長過程裡,卸責的父親離家躲債、長期人間消失,成為她「別針般地別在胸口左側的洞」、鳴笛般嗚嗚作響⋯⋯;討債者上門投擲「土製炸彈」,彈震症讓母親必須倚賴藥片入眠──但遠在爆炸之前她似乎已是「閣樓上的瘋女人」⋯⋯。多年以後,那曾被幼年的她指稱「媽媽原本要打掉妳」的妹妹,未婚懷孕了;當她面對她當初提議「拿掉吧,好麻煩」的幼小姪女,手足無措⋯⋯。
言叔夏散文裡所透露的,時間序列裡連續的家庭事件,遠不及於時間之流凝止、似可濃縮成幾幕家庭的(或反家庭的)景深構圖負片靜照。這是她因砍斲而生的成長,她的原初場景:午後密雲籠罩,母親攜著年幼的她穿過港町,於港口海堤上枯候那總也不來、卻同時似乎隨時要來的魚怪(其實已然來過了,我們都在那魚腹裡。言叔夏日後察覺了這一點)。母親也曾經領她沿著一條密林夾道的山路,於林間空地遭遇那些一一吊掛樹頭的貓尸(死亡總是懸吊著)。那最初的房間──陰暗窄仄的隔間,陌生遠方風景在電視小螢幕上投影出來的冷光,燃亮母親如貓的眼(言叔夏此後的房間宿命而完整地繼承了此一圖景)。她最初的旅程──全家人每年搭乘切穿山巒的午夜國光號,或沿南迴鐵道繞過島嶼南岬,漫長至失去時間的旅程,窗外風景流動的光影,往赴東岸玉里探望經年生活於療養院、與父親有如鏡像的伯父(日後,言叔夏將不停暗夜行路或流離遷徙,去探訪「另外一個我」)⋯⋯。
這些事件與場景,不免讓人在閱讀時暗暗猜疑:她的書寫瘋狂、以及瘋狂於書寫,(黃錦樹所謂對於文學的激情),是為了驅除她不時懷疑自己內裡所遺傳了的、近乎家族性的瘋狂因子。而她對於(廣義的)死亡及其翳影的書寫,則或許是一種對鏡猜疑、與蛇排練,是她生的方式、亦是她書寫的動力。
二、房間,窗口,放映室
散文集《白馬走過天亮》出版之後,許多讀者著迷於她所書寫的「自己的房間」。十八歲離家就讀大學,開始從一房間至另一房間的漂流旅程;不同時期,她蹲踞於不同的浮島房間。
然而,與一般印象相反,事實上言叔夏從未寫過她的房間。她從未工筆描繪、亦未著墨具體細節──早期習作裡的房間,尚有清晰輪廓,但在書寫的延展裡,它慢慢沉入一片漆黑,恆常只有沉默,以及不知來處、惘惘威脅的窸窣細響⋯⋯。房間內永遠只有尋常書桌矮几、衣櫥(總有黑暗事物隱身於內)、以及「窗」。這是言叔夏的獨特空間感:區隔了島嶼遷徙過程中一個又一個房間的,竟然並非房內的細節或格局;房間與房間的決定性差異,最終居然只在於「窗外風景」之不同:或是遠處的鐵道(切割縱谷的夜行列車投影於窗牖),或是河堤(從學院沿河行走、卻彷彿能夠抵達幼年的南方港口),或是來來去去的腳與鞋(這是她的地下室手記時期),或是多年之後窗下吊死人的樹(懸吊起一連串的死亡如暗房內一列等待顯影的濕漉黑白底片)⋯⋯。而且不知為何從來沒有貓的蹤影。
始於巴什拉的家屋隱喻,終於海德格的在世存有。言叔夏的房間從文學空間過渡到哲學此在。言叔夏的房間,既延伸自家屋、同時也對立於它。沒有客廳、廚房、餐室、庭院⋯⋯等一般憶舊抒情散文裡構成家庭意義的場景,只有母親在密雲午後觀看 VHS 公路電影的陰暗小房間──言叔夏一方面逃離母親凝望他方的「瘋女人的閣樓」,一方面卻在遙遠的他方鑽入自己的地下室陰暗小房間。家宅缺席,但言叔夏挪用了巴什拉的現象學,建立了她自己的「房間詩學」:空間不但不是意識的容器,反而「意識,永遠是朝向自身之外的甚麼的意識⋯⋯」,她的眼、心、與身體,永遠朝向他者與他方,透過窗口──「窗口」才是她的房間的核心。正因如此,言叔夏以窗口所構成的房間,才會同時也是東華大學課堂上或電影社的「放映室」──她不只一次提及,她的文學啟蒙極可能其實來自於電影。「銀幕作為窗口」的隱喻在此浮現;同時,此一隱喻的反面,「銀幕作為鏡子」,恐怕也無法迴避:它倒映了她的原初場景、那些關於傷害的劇場。讀者幾乎可以看見:言叔夏抱膝蹲坐於房間中央或一角,沉默凝望著發光的窗口裡,那些反複搬演的記憶裡的創傷場景、以及這些場景所蒸餾或揮發出來的幻影。因而,她的房間遠非吳爾芙「自己的房間」所宣告、進而由性別論述所外延的「自我完成」──恰恰相反,房間乃匱欠和缺乏的象徵、而非它的滿足。它不是容器,它是容器上的裂縫與破洞,不止息地流洩、漏失⋯⋯克莉絲蒂娃所言「漏的容器」。那麼,每當她在生命的尖芯時刻、獨自蹲坐房間中央,就是一再把自己擲入那些生命的孔洞裡去。房間打開深淵吞沒她,但它也內裡外翻、包裹她、成為她的圍護。一個承載創傷的空間,但也是創生的空間。它逼近克莉絲蒂娃所言的「chora」,「陰性空間」或「宮籟」,捲縮摺疊又延伸攤展,既是向內亦是向外。故它也接近海德格所論述的「此在」(Da-sein),「四因」從「四方」向心凝聚而後得以向外解蔽(poesis)生成的創造空間。
然而,海德格的「此在」並非某一穩固不移的棲居所在,它預設了一條「林中路」,必須一路追問與求索才能抵達。那裡是詞的密林,語言的道途;字如橡實,句子沿著葉片蔓延,意義匿於蕨葉的背面──言叔夏散步,並且穿過它們。

三、散步到他方,流離至異邦
對言叔夏來說,從一房間遷移至另一房間,這叫「流離」;離開房間、折返房間,這是「散步」。然而,透過回憶與夢境,房間裡起居的她,總像是在時間裡流離遷徙;沿河堤踱步、或循林中路行走的她,則彷彿永遠揹負著她的房間、透過窗口向外也朝內張望。這是言叔夏的歧途,也是她的蹊徑。
正如語言令人割離真實層、進入象徵界,求學也是一趟愈行愈遠的離家之旅——並且注定再也無法返家。高雄、花蓮、台北,最後(目前)落腳台中,言叔夏幾乎行遍島嶼;透過每一扇房間窗口,透過每一回外出行走,她也描摹了一系列的台灣城鄉風景。千禧年之後那一波「地方書寫」熱潮,或挖掘並扎根故鄉風土誌、或回應地方文學獎命題作文──在地的或土地的認同書寫。這是「新鄉土小說」的主流。散文裡,既有城市曲徑幽巷裡的即物抒情(比如舒國治)或都會市井冷暖的尖銳洞澈(比如黃麗群),也有南方故鄉的古意回訪(比如楊富閔)或山川地誌的詩意測繪(比如吳明益)。然而,言叔夏卻彷彿流離異邦,不生根、不翻土、不溯溪、不貼地。在她的流徙裡,她偏好透過窗口或散步來描繪四季、節氣、明暗、晴雨、氣象、霧霾、煙雲、河霧⋯⋯。浮光掠影,心象風景。半透性與流動性,漫滲與淹溢。它們乍看沒有台灣風土戳記,卻無疑是這個島嶼的氤氳。沒有戲劇化的離散敘事,沒有界碑,也沒有景片,只有「漂流的傢俱」和「窗口的房間史」,以及由此而遭遇的流動風景。一旦離家,甚至早在離家之前,她就已然漂流不止,恆常流離。
最特別的是,言叔夏再三提及移動之中的各式交通載具——它們幾乎都成了她的「有窗口的房間」。切過島脊山脈或繞過島嶼南岬、前往後山精神病院的長程夜車;每日來往高雄市區與林園邊鎮之間、被晨煙或夕霧包圍的中學時代通勤巴士;東部沿岸藍白鋅鐵車殼的老式平快車,遇到「有海的小站」便於月台落車;浮燥心亂時,路旁隨意揀拾某一路線巴士、搖搖晃晃直至它的終站;凌晨時分,自交流道口之接駁轉運站(有如「發光的夜間馬戲團帳篷」)發車的北上國道客運⋯⋯。這些「有窗的車廂」無一不是她「移動的房間」。同時,它們難道不也是一座座「移動的電影院」嗎?車廂昏暗,座位臨窗,風景在窗框之中浮露、漸層、流動、摺疊、皺皴、纏卷、明滅⋯⋯。窗口即銀幕。窗口反過來讓房間幻化為一只暗箱或影院,並且漂浮了起來。
言叔夏的散文裡,「散步」幾乎成為作者印記。強曝日光底下、夕色日暮裡、午夜微光的虛線上,她披掛著她的窗口(同時扛負著佈滿她個人星系的房間)散步,恍若一名「持攝影機的女人」⋯⋯。言叔夏一如 Brian Henderson 論述法國新浪潮導演高達時所言,取消了固定鏡頭的框內景深調度,拒絕了框與框、鏡頭與鏡頭之間的剪接蒙太奇(此二正是同樣善寫回憶與幻夢的駱以軍所嫻熟的「劇場化場景」與「蜂巢敘事」),改以游移行走之攝影機運動、讓框內的音畫風景永恆流動。散步的言叔夏,讓書寫成了她開向世界(世界亦是一間漆黑暗室)的窗口──散文即是她的房間。也因此言叔夏從未描繪任何一幅全景圖(panorama),從來沒有一整片風景如案頭卷軸圖畫、轆轆展開──她的窗口恆是「有限視野」,更重要的是,她對此高度自覺(所以她才反覆描寫房間或載具的窗框)。幽暗房間裡的裂口狹縫、回憶或幻夢的濾鏡。偷光的鑿洞。午後白晝裡安靜散步之貓,那雙縮小成一線窄縫的瞳孔。針孔成像,光影散射。
但散步也永遠不只是散步而已。不是沿路撿風景、拾取牆頭凝艷花果或簷下冷暖人情;但也不限於在行經之處打開一扇扇窗口。既然言叔夏的房間包涵洞穴寓言,窗口亦是反身之鏡;那麼,她的散步也總是行路難:追問的道途,既是花園歧路、也是林中路,總在行走與移動的過程中,擦著世界的牆、翻著記憶的土,以哲學的腳走文學的路。(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