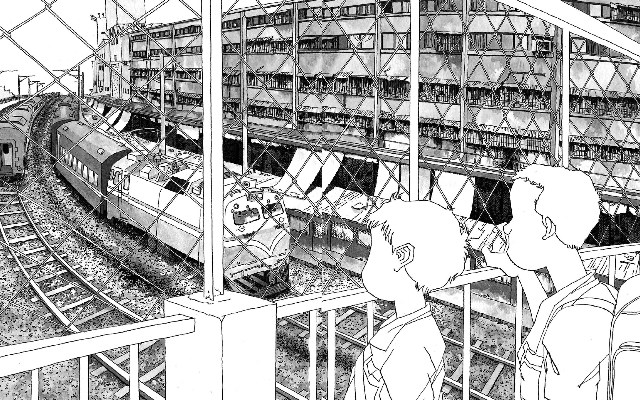帶著敬意和弄得漂亮是兩件事情——專訪《返校》《天橋上的魔術師》美術設計王誌成
夢醒,行走在貼滿封條的學校,漸漸走入記憶頹杞的鬼域。穿梭在那些人還存在、已不存在的時間裡,空間也不斷變質。
《返校》上映後七天票房破億,遊戲 IP 轉化及故事的社會意義廣受矚目外,也展現台灣電影製作的成熟度,其中美術設計功不可沒。人稱「頭哥」的王誌成,從《南國,再見南國》的一人小組到《返校》統合團隊,二十餘年來參與大小電影現場無數。與侯導合作開啟了他的電影美術之路,後也參與王家衛《一代宗師》、擔任盧貝松《露西》、馬丁史柯西斯《沉默》台灣區美術指導,並以《范保德》拿下台北電影節最佳美術設計,近期《天橋上的魔術師》將中華商場重現更是引起一陣討論。
《返校》主創團隊年輕,他用經驗守護,在產業還未能健全分工的階段,縱向傳承台灣電影美學觀,橫向連結國際團隊技術。他背負責任,但也忍不住小抱怨,「莫名其妙就變成我是現場最老的,厚!」
新舊之間的現實
創建《返校》宇宙第一步,尋找翠華中學。因遊戲設定在六〇年代,還在運行中的學校都已大幅翻新,團隊朝廢棄學校方向搜尋,一路往南,最後才在屏東潮州找到已廢校十七年的校舍。以廢為底,他反而要煩惱怎樣翻新:「怎麼把它回覆成人聲雜沓、師生進出,白教官幾乎是掌握整個學校運作的一個氛圍?又是一個問題。」
電影美術,是統合美學與現實的學問。比起技術,現實問題如拍攝時間,時常在執行時成為更大的阻力:「最難的應該是說,怎麼跟導演組去抓到一個平衡點。什麼時候要新、什麼時候要舊?在演員的拍攝時間裡,怎麼讓我們有時間做舊又翻新、或是翻新又做舊。」即便前製做到精,也難以避免現場執行的困難。

《返校》拍攝現場。以廢校十七年的校舍為基底,美術也要思考如何回復成還有人的狀態。
預算也與時間一環扣一環,壓力落在美術現場應變與效率。頭哥難忘一幕,是方芮欣從門縫偷看張老師與殷老師在音樂教室的對話。先是方芮欣記憶中鮮明的現實場景,而後灰飛煙滅,成為記憶塵封狀態。這場看似以特效瞬間磨舊空間的戲,因預算限制,其實是美術團隊連夜趕工達成。鏡頭先 pan 一次舊場景,定住不動,美術組趕緊改變整個世界,再拍回來。
 |
「舊黑板和鋼琴原本就是那個學校的,我們覺得那東西太棒了,就去找新的東西,一模一樣的鋼琴、一模一樣的黑板,瞬間把舊的踢掉之後再把新的擺進來。牆壁也趕快刷完作新,海報啪啪啪,很像超級變變變。」怎麼做、怎麼拍,美術與導演、攝影密集討論,才有可能在預算控制下拍出理想片段。
這樣的過程,是合作也應該是激盪。從最一開始頭哥就決定要保有不同於導演的視角,知道徐漢強玩遊戲玩到哭,他選擇不玩:「搞不好我有些意見會是導演的盲點。如果我們都是一起的玩家,可能會有共同的話題,但那東西有可能是 player 自己的世界觀。」
「我覺得美術最重要的功課,並不是去服膺導演的指令。它絕對是指令,但最過癮的過程應該是你跟他激撞:我可以推翻他的東西,他也可以推翻我的東西,而不是導演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
一只茶壺的表演性
《返校》讓人驚艷不只是復古仿舊,而是與遊戲概念呼應的意象式場景,許多便是由美術組發起。頭哥想的不是複製遊戲,而是如何抓住核心精神,再造屬於電影媒材的氛圍。例如魏仲庭行走在走廊上,巨幅白紙垂落,風吹紙搖,自然產生一股緊張與壓迫感,那是屬於大銀幕的視覺呈現:「原本遊戲設定是在教室門口有個桌子,寫著『忌中』,有個蠟燭在那邊。但我們想把那個符號給放大。」
魏仲庭和方芮欣接著走進防空洞,遇見殷老師與同學們。其實早就決定要在高雄明德訓練場現成防空洞拍攝,但頭哥評估走廊氛圍的重要性與憑空搭建走廊的成本、困難度,最後說服劇組將整場戲搬到台中公賣局的倉庫,讓美術組在倉庫裡直接披掛油紙,改在門後新搭一個半圓形的空間做防空洞。原本只打算去那裡拍攝工友老高的小屋,「後來再加那個防空洞的戲、另外一場張明輝老師被槍決的戲,去台中 CP 值就有了。」他笑開,把兼顧美學與精打細算視為己任。
.jpg) |
美術不只是執行,更可能影響場景走向、觸發劇情與情緒。他談第一個參與的電影製作《南國,再見南國》,那時林強飾演的扁頭與一幫兄弟賭博,侯導只指示:「他們在賭博,一言不合要打起來,你看一下這要怎麼做。」慌亂中他才想起來,剛剛在路邊雜貨店有看到一個老人泡茶用的泡茶車,不如讓他們喝茶喝到打架?

捨現成防空洞不用,頭哥為了前一幕走廊氛圍而重新搭建一個半圓形空間作為防空洞。
最後那場戲一個 take 就成功。林強飾演的角色最討厭人家因為頭扁叫他阿扁,對方偏偏講不聽:「他一不爽就翻桌,那個水還在煮,水是滾燙的,角度不偏不倚就灑到泰哥,泰哥整個火了,兩個人就打起來,侯導看了就很爽。」
「這個小小的茶壺跟《返校》大禮堂的景,美術的意義不同在哪?對我來說,這兩個東西強度是一樣的。」從一個道具到一個場域,美術是盡其所能、用想像力去完全表演:「你有辦法讓演員在該發揮的地方發揮出來,美術的力道與功課就在這裡。」
《返校》拍攝過程中,美術助理們有時撞牆,他引導要更靈活思考導演要的東西是什麼?畢竟現場本來就是活的,「《返校》成品對照工作本也還是有差別,那就是導演創作的空間。這個空間很難抓,但是一旦頻率有對上,你的工就會很順利。」
這樣的溝通彷彿讀心,要先確認的是本質:「過程中你會知道,這個導演創作的本質是很強的,而且他要的東西都不會變。侯導也不會變、王家衛也不會變,一年前要的東西和一年後要的東西是一樣的,只是他沒有說,徐漢強也是一樣。」
美術要相信角色、相信故事
話語間,頭哥總是顧全所有人的思考,但這般細膩一開始其實是被迫的。
「像侯導或像王家衛導演,大家都知道他們拍片沒有文本。我年輕的時候會覺得說,『啊今天是要拍什麼、我要準備什麼?美術壓力好大喔⋯⋯』但他們又不是不知道要拍什麼,他們好像了然於胸,只是不跟你講而已。」不知所措的現場高壓,頭哥回想起來只能苦笑,「而且侯導當阿公以前真的很兇⋯⋯你看他現在笑面笑面,以前他真的會拆景⋯⋯」
如今他養成習慣,傾向弄越完整越好:「我可以的話,就是整個房間全部都弄,不是像拍廣告,只要一個角就好,也是在侯導那時候養成的。像《千禧曼波》雖然沒講到舒淇要去浴室,但我浴室也弄了。」後來舒淇果然進了浴室,但他還是被侯導罵。原來千算萬算,少買衛生棉。「你永遠想不到這些事情。回過頭來想,永遠百密一疏。」
但走過《千禧曼波》、《最好的時光》,「漸漸漸漸,我就體會到一種感覺是:你可以試著用他的立場去想像他的故事世界,就可以抓到一些些脈絡。」理解導演、理解故事,或許可視為美術設計的出師。他笑著嘆氣:「那真的是好久好久以後才體會出來的。」
 |
了解演員個性、角色性格、劇本設定,這些都是美術的功課。有時候初讀本會有些疑問,對他來說那是有趣的地方:「之前在做《范保德》的時候就想說,哪有一個五金行老闆這麼帥?(笑)」但實際去嘉義探查,的確五金行有許多老闆個性鮮明,「我就說服了自己,范保德他真的是一個更特立獨行的五金行老闆。」
不相信故事,是很難做美術的:「你一定要想辦法進入這個角色的世界,才有辦法去設定他的世界,一定是這樣子的。」他用看漫畫小說打比方,吸引人的角色總是想讓人成為他,美術則是更進一步去想像:「我變成他之後,我的房間應該變成什麼樣子呢?我的家應該是什麼樣子?」
帶著敬意,才能功德圓滿
設身處地為故事打造場景,頭哥心中理想的美術或許可用「舒適」來形容:「最好的狀態,就是當導演、攝影師、演員一到美術幫他準備的場域,他就放心了。包括演員一進去會覺得:啊,這是我的世界,這是我的房間⋯⋯什麼都不用想。美術最好的狀態就是那樣子。」講起信念,他靦腆和驕傲揉雜:「導演他似乎也曾經稱讚過我說,我的美術場景不會搶過演員,這件事情就很重要。」
「美術肯定不能強過演員。很多失敗的戲就是這樣子,都在看美術、在看聲光效果,演員在演什麼?不知道。」
念茲在茲的準則,頭哥講來有前輩的氣魄與風範,「有些年輕的夥伴比較難拿捏,會覺得說『欸是那年代的東西欸!好炫好酷!』,就很想把它搬進場景裡面,但是不適合,那東西一放進去就可能搶過演員,太花了太搶了太跳了,都有可能。」他相信電影依然是群眾合力的項目,「不是只有你電影美術一個人。中國電影最近弄的大堆頭很容易有這種毛病,極度揮灑技術,同時就會弱化其他項目。」
有一種炫技失敗,是忽略戲劇的本質。他眼中無論中國強檔鉅片、好萊塢續集都容易犯這樣的失誤:「我覺得電影美術的課題也在這裡。那麼大的資源弄出那樣的東西,但人的戲沒有出來,這個片子也就可惜了。」
 |
他一直都是愛看電影、對人的故事著迷的。在日本留學時,《搶救雷恩大兵》上映。他在電影院裡被拍攝手法給震撼,但散場時另一個畫面更深刻:「走道另外一邊是個七八十歲的日本老男人。我永遠記得他那個身形,跟落寞站起來、獨自離開的樣子⋯⋯你永遠沒辦法想像真正經歷過那樣殘酷年代的人,看到這樣的影像對他的衝擊。」
拍攝《返校》前他也去景美人權園區,看監獄裡的圖書館,那些政治犯度過監禁或是生命最後一段時光的地方。「有些經驗你真的沒辦法完全理解,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對這些人、這些故事、這個歷史表達小小的敬意。有這種思維,你去做陳設拿捏就會比較準。」
「你帶著敬意,跟你想把它弄得漂亮真的是兩回事。很多人都可以弄得很漂亮,但是你要弄到有準度在。對我來講,這就是一個莫大的功德。」
如同從前他看《悲情城市》而慟,會不會若干年後也有許多年輕人被《返校》感動?「我就覺得我功德圓滿,一輩子做這件事情,也就夠了。」
 |
組隊幹大事
那是電影人都懂的熱血。自日本武藏野美術大學映像學系畢業後,他返回台灣,也是一心想做電影,可惜那時一年根本沒多少片可拍,只好從廣告開始。有天他騎著摩托車,在忠孝東路上看到一台綠色小卡車開過,上面寫著「侯孝賢電影社」,他加緊狂追,試圖從前座玻璃看看侯導是不是在車內。「結果沒有,是連碧東先生在開車。」連碧東,吳念真導演的弟弟,在許多新浪潮電影裡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幸好後來他還是認識了這位「東哥」。起初他藉由廣告認識《戲夢人生》美術盧明進,盧剛好軋不過來,轉介《南國,再見南國》美術一職給他。他興奮前往侯孝賢電影社,負責聯絡張羅的人正是東哥。與黃文英面試後,他的電影美術生涯就此展開。
二十年過去,言語間他依然保有那樣的衝動。即使是前輩了,只要年輕導演想衝、想和侯孝賢那時候一樣用一千六百萬拍出《悲情城市》,「我可以的話,或你看得起我的話,我非常願意加入你的團隊。那很過癮啊。」
說穿了,頭哥也就是個資深影迷,期許台灣電影人組隊幹大事。影視產業有許多沉積已久的問題,高工時、低薪、過勞、缺乏工會等等他都切身感受,「尤其是主創,你一裝傻的話就是整個片子的災難。裝傻到節骨眼,這就不對。拍片的條件就很現實,如果不去面對、又把本子寫得天花亂墜,到時候就是會有問題。」
但他同時也是樂觀的。如果能夠更精準掌握拍攝、思考取景與創意之間的平衡,「戰戰兢兢把事情做好,台灣就有機會。」有很多現實的問題,或許現在是他可以慢慢處理的了:「是我這個位置的人的功課,我也只能說慢慢改。」
這次《返校》有不同團隊參與,也像是台灣美術設計的成果發表。負責油漆與各種表面質地加工的是曾與李安、魏德聖合作過的法蘭克質感,領頭的陳新發師傅一起去了潮州的舊校舍,再返回台北搭建禮堂場景,重現與舊校舍一樣的各種質感。置景部分則與南部的工班合作,起初在拍《阿嬤的夢中情人》時,他藉由在南部做劇場的妻子認識了劇場木工,從小案子開始越做越大,如今可以撐得起一整個翠華中學的施工。
如果產業更好,也才會有更多新血願意進來。他一路上看賓哥(李屏賓)、廖桑(廖慶松)和年輕人合作,總會輕輕提供實際的提醒和幫助,現在他也持續給予:「之後會變怎樣很難說,但我覺得我還可以再拉幾個、甚至是再拉一個世代起來,希望是這樣啦。」
畢竟他也曾是那樣一個少年。即使現在大家喊他「頭哥」,他從不曾忘記那個滿腔熱血追著小卡車跑的「大頭」:「後來想想,我美術人生的原點就在那裡。就是那個騎著摩托車在看,侯導有沒有在裡面?那個小毛頭的狀態。」
永遠做個小毛頭,可能是他給電影最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