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正泰・聽說耶穌在便利商店門口徘徊 EP3|我倒希望能為每一段關係標價
13.
2020.05
耶穌沒有跟我索取貼紙,但我帶他回老家時硬是塞給他幾張,很難說他欣不欣賞。老家巷口的便利商店店員說很久沒看到我了,我說我搬到市區了,他沒有說什麼,但我們彼此都有一種熟悉的親切感。
他是個胖胖的小夥子,很年輕就生了一個女兒,他老婆也是這間店的店員。就我的觀察,這間店的老闆可能是他媽媽。他媽對我很好,記得我喝咖啡的一些小習慣,還有菸的牌子。我每天就是起床出門到便利商店,什麼都不用說我就帶著我要的東西回家,當時被困在另一個難關裡,覺得好像永遠無法逃離那裡,現在看到店員,產生的那種懷念的感受,我才察覺到原來那已經離我這麼遠了,什麼逃離,我其實根本停不下失去的腳步,哪怕是難關,還嫌失去得太慢呢,我根本無法留在任何地方。
我跟店員聊了兩句,他女兒看起來已經上小學了,一個小大人一樣有著嚴肅的眼神,我只記得她還是個嬰兒的樣子。他爸相比之下顯得無比懶散,他看著耶穌笑笑地說,新朋友?我四周觀望了一下,神秘兮兮地說,其實呢,他是耶穌,就是那個耶穌。耶穌展開雙臂說,你好,我是耶穌。
當然,他不相信,氣氛很僵,那是春天的一個晴朗的下午。
14.
2019.07
在仁愛路旁的辦公室裡開會,《遜到簡直是個藝術品》快要發片了,但我們什麼事情都還沒搞定,會議中我們取得零個共識,場面一觸即發,於是草草結束,六個人擠在小電梯裡下樓,我們烏煙瘴氣的表情經過電梯的鏡子無限反射,變成一股無比巨大的無力感,在那台電梯裡盤旋。一從電梯走出來,我說:「你們真是太可笑了。」
那晚不歡而散後,金剛一到左輪就拍上桌子狂吼:「我們可笑?他以為他是誰啊?」
而阿祖則摸黑回家,躺在床上,獨自作了一個夢。他夢到我們在夏威夷演出,在演出前,他拿起一塊磚頭敲劉暐,劉暐被擊倒後他轉身要敲我,我見狀一溜煙地逃跑了,這個夢後來變成他四處在追打我,逢人就問,你有沒有看到許正泰?手上還拿著那塊磚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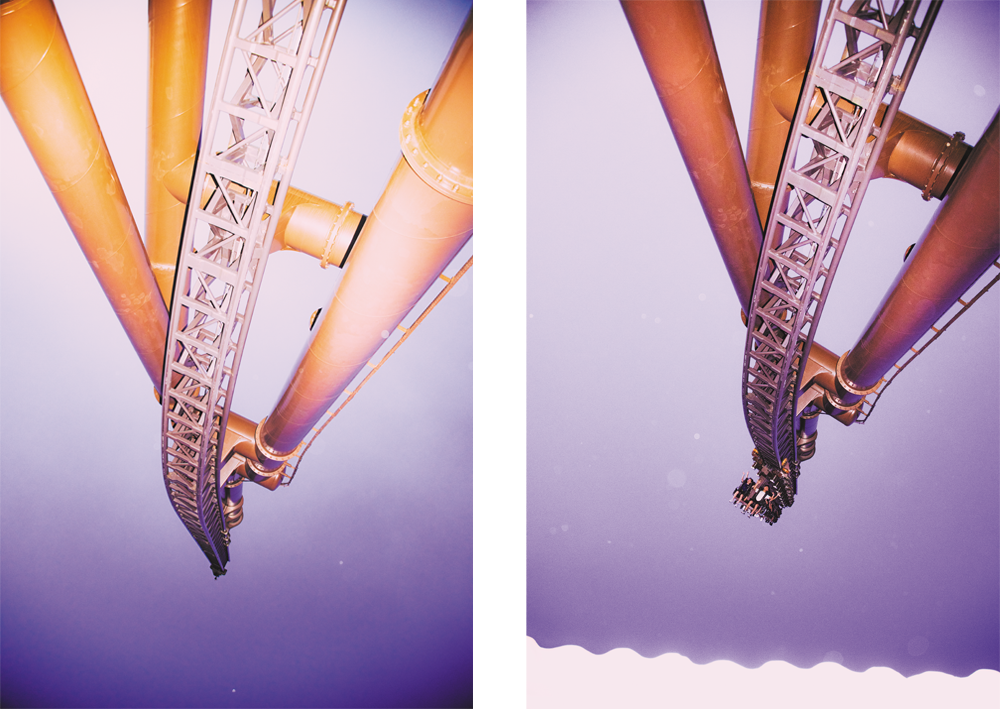

15.
2020.10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說出那句話,我沒有把我自己排除在可笑的行列之外啊。」
「你想解釋什麼,那件事已在那一天完成了,它既然已經發生了,就已經不會不曾發生。」
「你這很像我會說的廢話。」
「對。這就是你會說的廢話。」
「我也沒有後悔,我只是說,那句話不能代表我當時的意思。」
「你當時的意思是什麼?」
「我的意思是⋯⋯我當然還有別的意思⋯⋯。算了,當時說出這句話怎麼樣都不是想讚美人。」
「對啊,你還想擦脂抹粉啊?」
那個辦公室我們借過兩次,兩次都是野心勃勃地想在一個安靜的地方好好解決問題,當然都沒有成功。叮噹叮噹,限時優惠,你有問題需要被解決嗎?請洽在仁愛路旁的 xxx 股份有限公司。你可以驚喜地發現只要稱得上是問題的,其實都不會獲得解決。
我跟耶穌在那台電梯裡,沒有按任何樓層,電梯靜靜地懸掛在電梯井,我有點害怕這種純粹的懸空,我說:「是啊,真是滿爛的。」
耶穌說:「這台電梯裡根本沒有鏡子。」
我說:「是啊,所以那天在無限反射的究竟是什麼?」

16.
2007.04
那晚中山高的路面黑漆漆的,我只記得幾台車的尾燈在前方飄移,後座的美國人歐布萊跟我不確定名字的加拿大人都喝醉了,一路上都在放聲高歌。劉暐手握方向盤,直直地盯著前方。到了這條公路的終點轉幾個彎,再開幾個小時,直到看到一片海從盡頭升起,那就代表墾丁快到了。
三點半,我快要睡著,歐布萊還在唱歌,劉暐不發一語,我感覺車速漸漸放慢,越來越適合入睡,在我幾乎睡著時車子正好在路肩停下,車內突然靜默,劉暐看著前方,然後緩緩地轉向我們,說,煞車壞了。
歐布萊跟加拿大人下車不久後搭便車繼續南下。公路旁一望無際的漆黑,放眼望去一盞燈都沒有,最近的客運站可能在五十公里外,想到這裡讓我很崩潰,在車旁來回走,大聲嚷嚷,劉暐坐回車裡,趴在方向盤上。過不久他下車,說:「欸,許正泰,你要不要先冷靜下來?」
劉暐撈了撈置物箱,我還是哭喪著臉,置物箱裡還能有什麼?不就 CD、書、空菸盒,那都不是我現在需要的,我現在需要一台客運,或是安全感,這置物箱明顯無法提供。
一本被擠得凹凸不平的冊子被他翻了出來,那是這台車的說明書,他若有所思地翻著那個冊子,像是在圖書館享受閱讀樂趣的小學生一樣。普通來說,說明書不會說明該如何駕駛一台煞車被踩爆的車子。我不可置信地看著劉暐,他又說了一次,你總之先冷靜下來。說明書最後夾著另一份薄薄的文件,上面寫著道路救援之類的文字,劉暐撥了電話大約半小時後,我從照後鏡看到一台拖吊車閃著黃燈靠近。
我們坐在車頭被吊起的車上,此刻我們與正常世界有一個 45 度角的差距,所以應該算是躺著。沉默地透過擋風玻璃仰望夜空,說些無關緊要的話,比如,北斗七星,會是那個嗎?過了不知道多久,終於出現一面路牌,上面寫善化,我們問了對方一句:「善化是哪裡?」
這台車的原廠修車廠在善化,拖吊車司機說,清明連假這裡很有可能沒開,如果有開應該是八、九點。我再度崩潰,天漸漸亮起來,離八點還有他媽的三個小時,劉暐拿一根菸給我,說:「你不要那麼容易崩潰,我剛剛看到那邊有一間早餐店,先吃個東西再說吧。」
很久之後我才知道,善化國小是陳金鋒的母校,我很喜歡陳金鋒,但不知為何,善化跟陳金鋒之間我對善化更有感覺。吃完早餐,天完全亮了,很熱,一夜沒睡的我們坐在路邊;然後,修車廠旁邊終於有住戶開始活動,他們說修車廠今天不會開。我把頭靠在牆上,萬念俱灰,真想好好睡一覺,劉暐走到對面朝馬路揮手,我問他要幹嘛,他說他在攔便車。我已經懶得崩潰,於是走過去跟他要根菸,也胡亂地在一旁朝車子揮手,沒想到真的有台車慢慢在我們旁邊停下來,我們就這樣到了高雄。
那天我們前後搭了三台便車,從善化到墾丁花了八個小時,最後一台車是非常友善的三人組,他們不知道春吶,但他們知道車城有洋蔥跟一間很大的廟,他們此行要去拜拜,那間廟的門口有賣鹹蛋,然後拜完拜後他們堅持要請我們吃鹹蛋。烈日當頭,我們五人一字排開,手上都抓著一顆鹹蛋艱苦地吃著,遠方甚至有海市蜃樓在搖曳,每一口都吃得我們嘴唇龜裂。然後他們說,要不要去海生館?我們說,不了不了,我們真的好想睡覺。
到了墾丁後我就與劉暐分開了,我去找大學同學,他則直奔春吶會場。到了民宿睡了一覺後,當晚我跟同學在海邊找喝醉的陌生人玩了通宵。這兩天我們沒碰面,兩天後我們搭上客運,輾轉回到善化。看到修車廠拉起鐵門的那一瞬間,這世界產生了很細微的變化,而春假差不多要結束了。
車子一下就修好了,劉暐在省道上買了兩包檳榔,我隨後睡著,只知道車子偶爾減速進休息站,劉暐眉毛低垂,說,我真的不行了,得休息一下。然後進休息站買咖啡;這一條回家的路我很模糊地醒來幾次,只記得劉暐一個人瞪大眼,拼命往嘴裡塞檳榔跟咖啡。到了台北時,兩包檳榔已經吃完了,他把我載回家後,說:「我要回去睡覺了。」我對他點點頭,然後看著他那台白色小轎車慢吞吞地在巷子盡頭轉彎。
17.
2020.12
我相信人與人之間的基礎是交換,其實跟買賣是差不多的意思,只是買賣很清楚,有錢當作衡量公平的標準,但大部份情侶或是朋友終究不會為彼此的善意定價,因為我們喜歡一個概念,感情是無價的,我認為要是不這麼想的話,人會無法活著。所以感情也是最不可靠的,通常最親近的人會帶給彼此最大的折磨,不是說誰故意或是誰錯了,這只來自於每一段關係的定價不透明。
我就是這樣,你也是這樣,我們把自己的好意當作禮物,都渴望給少部份人一些特權,我們不用標價了,跟我談什麼錢?於是在生活中給彼此佔一些便宜,時不時撒嬌一下,情緒勒索一下,這都可以很公平,就是一種交換,而我們的心在一些公平的交換中得到安慰。當你心痛的時候,我願意為你煮碗熱湯,當你遇到困難我想要站在你身邊,因為我有一天我也會心痛也會有難關,而我也會需要你這麼對我。
但這種期待經常讓人失望透頂,已經是定價不透明了,你要怎麼期待當你拿出你最寶貴的善意時別人也同樣看重?在颱風夜為你買碗麻油雞與單純買碗麻油雞給你哪一個好意更有價值?而你又要多感動對我來說才公平?我們在這一大片灰色地帶裡只能靠默契,靠感覺,靠信任,那都是浮動的標準,多麼動輒得咎,多麼需要藝術天份。而且在不斷修改自己的價格之後,你才發現,大部份人並不是沒錢付,他們只是單純喜歡殺價而已。我沒有把我自己排除在外,我也是這種殺價狂。更何況,真實與虛構同時都能化為語言,當一個人說:「我為你付出這麼多為什麼你如此對待我?」——這句話裡面有什麼能拿來判準?
這種黑箱交換永遠是問題,你我都無所適從,每天都有誰又辜負誰,誰又背叛誰,如何判斷誰的錯比較多,誰比較無辜,有這麼多資訊被隱藏在事情後面,你要怎麼相信人的感情呢?
那並不通用,那都只是我的一廂情願。錢就很萬用了,我這麼說倒不意味著我愛錢,我是滿喜歡它的,但它目前不是我的全部,它只是一個工具,很中性,養樂多一罐十元,清清楚楚,拿出十元,正大光明地從便利商店走出來,沒人難過沒人流淚,你比剛剛的你多擁有了一罐養樂多,綜合各種層面來說,沒有比錢還可靠的東西了。
我倒希望能為每一段關係標價,這樣一切都會簡單很多,沒有委屈沒有失望,想想看,一個人在路邊跟另一個人說:「你委屈?我為你付出那麼多,他媽我一開口就要收錢的,我上個月跟你說這麼多事,一共一萬零三百一十七塊,你呢?說起來也才三千五百塊,你有什麼資格委屈?」
對方回話道:「是的是的,但你忘了算我聽你說這些廢話的精神賠償。」
「喔?是這樣嗎?這種事怎麼不早說?你怎麼收費?」
「一分鐘一百塊。」
那人掏了掏口袋,說:「那之前的算一筆勾銷,我還有十五分鐘,求求你就聽我說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