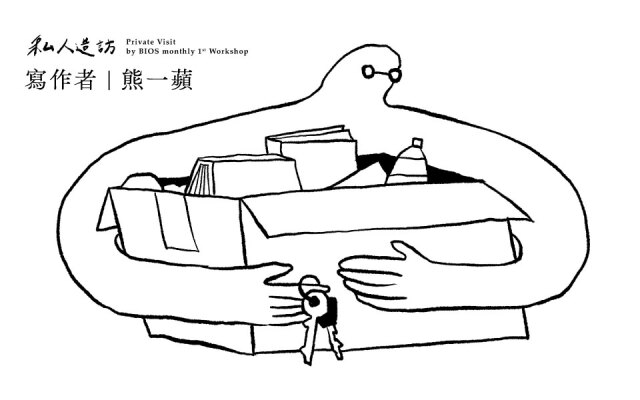男朋友夢工場|沈信宏 ╳ 熊一蘋:不是那種異男,那要成為哪一種?
熊一蘋與沈信宏是第一次見面。見面時他們才知道彼此都是高雄人、鳳山人、念過同一所國中。甚至,想寫過同樣一本書。
關於那本書,沈信宏先一步寫好了。他的散文集《成為男人的方法》,如同「男人」的使用說明,先是產地、必備零件、組裝方式,似在解釋市售功能:用於搬運重物、居家清掃、開車買房、戀愛結婚付月中費用。但在使用說明的背面,沈信宏以他的文字說出男子真實心聲,好累啊⋯⋯
熊一蘋說:「今年看到信宏這本書時,心裡有一個『啊,會不會被寫掉了』的想法。」卻也藉由它,更釐清自己在心中儲放與發酵的念頭:「身為異男的很多想法,大多時候模模糊糊的。」透過自我書寫與彼此指認,人們認知自己,也找到同類。
同類
沈信宏與熊一蘋可能是同類,然而同類者,也不過生物分類法裡頭某一個層級,他們兩人間的最大公約數,除了地緣、生理性別,或許還有某種偶爾會被他人辯識與指認的陰性氣質,夾在字裡、藏在生命經驗的褶曲裡。
沈信宏寫到第三本書,終於寫回自己,從《雲端的丈夫》裡妻子與丈夫的花腔轉換、《歡迎來我家》各種不同家內角色的 cosplay,來到他自身的人生整理術。「寫這篇〈成為男人的方法〉,從小時候整理到長大,發現每個男人成為父親、談戀愛的路上,一直不斷有人跟你講男生要怎樣。」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曾成為「不適者」,但沈信宏一直覺得苦惱,做不好一個男生,「我還是會一直嘗試,但就很累(可能女朋友還會恨你)。」
人世間的分類帽,偶爾也會將「陰性氣質」戴在某類男孩頭上,比如長髮或瘦弱,比如文組與沉默。沈信宏與熊一蘋都曾在人生的某段路上,被沒有魔法的分類帽罩頂,戴上以後,像昭告了世界其他人該如何對待你。
覺察往往伴隨著如初次被紡錘尖頂刺傷的感受,熊一蘋自剖他成長的過程大多順利,性別意識可能是很久以後才有的。紡錘的來臨無聲息,也不一定每次都刺穿了什麼。「第一次的挫折,可能是國小時。剛入學的我都跟女生一起玩,大家圍一圈玩互相丟球的遊戲,裡面就只有我一個男生。有一次,我不小心丟到一個女生的臉,她哭了,大家圍去安慰她,並且轉身跟我說:『男生怎麼可以這樣子。』」
熊一蘋早已忘記具體細節,留下的只有當時身為「男生」的原罪感,讓他意識到自己不能再跟女生一起玩了,才跑去跟男生玩在一起。

沈信宏的紡錘,比較像是《睡美人》故事裡的魔紡錘,一碰千年,只不過他被戳出的血點,不是讓人沉睡,而是清醒。國中時他經常被笑娘娘腔,他自述當時身形弱小,似乎沒有跟上同齡男生的成長速度。面對那些總是一直講髒話、打來打去、勾肩搭背,開著生殖器玩笑的群體,他如今很直白地告訴我:「很恐怖,無法融入,那不是我的樣子。」
沈信宏自那時起便知道,他期待另一種與人交友的方式。「我對人際關係可能有比較深的要求,像是情感依託,要聊更深刻的東西。但對一般異男來說,情感依託不是那麼容易昇華的。」雖然,他也想過要更努力變成一個更男生的人,我問他,如果不舒服,為什麼要?「因為你還是會被笑是人妖、被欺負啊。」當時血點,如今是作家指上,敲擊鍵盤時朱紅的痣。
軌跡重疊,他們二人後來都念了文組、進了中文系與文學研究所,也走上寫作的路。對熊一蘋來說,一直處在一個身邊女生比男生多的環境,可能是他無法意識自己究竟「偏陽剛」還是「偏陰性」的原因。「因為我一直在一個不受這社會性別框架約束的環境,這個環境可能本身就跟外面不太一樣。」熊一蘋定位自己是性別意識的晚熟者,直到他研究所與現在的女友交往以後,接觸了女性主義的觀念與談論者,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麼跟他的經驗不太一樣」。
熊一蘋與他的長髮,其實應該是他成長經驗裡,最直接被說不像男生的一件事,而且通常來自長輩或性別意識很敏銳的人。譬如,一位性別所的老師稱讚他頭髮漂亮,熊一蘋知道,對方想要讚許他能勇敢地展現出自己,沒有努力符合社會對男性的期待面貌。「可是其實我沒有,我不是抱著那麼強的意識去留長頭髮的。一開始我只是因為方便,也覺得留長髮沒什麼,留久了才覺得這樣比較舒服。」
比如熊一蘋的長髮、比如沈信宏的花襯衫,大約都是現在他們的一種標誌。可標誌的由來,都有所本,像是一條從南到北的成長路,從高雄到北部讀書、從家人為自己選購的衣物到自己的衣櫃,更是從男孩變成男人的艱苦談。
熊一蘋坦承,長髮的由來,一開始只是不敢去台北的理髮店。「在高雄都剪家庭理髮一次五十塊,上台北後理髮廳都很時髦,只好等回南部或很久才剪一次。」在他的文章〈晾她的衣服〉裡也寫過:
「我要為自己買一些衣服,每個人都很熟悉這件事吧,但我居然活了快三十年才準備面對,一想到就幾乎被自己的羞愧壓垮。走進 Uniqlo 的瞬間,我的視野立刻浮現一層薄薄的白霧,心跳加速,噁心的感覺從喉頭湧上。」
不分男女,你或我或許都曾像這般,羞恥於隻身走進試衣間與理髮廳前的大落地鏡前。沈信宏說自己也曾是這樣的人:「一開始會很害怕,要拿衣服、要去試穿,都很有障礙。所以會找女生朋友陪著去,模仿她們,才漸漸知道該怎麼做。」
你知道嗎?在鏡子前面看自己,也是一種天賦,不是每個人、每個時候都為此感到自在。如熊一蘋說的:「就是會覺得某些事情很不自在,像是會感覺自己穿的衣服哪裡破了一個洞,褪了色,甚至會覺得我沒有可以穿去買衣服的衣服。」沈信宏鄭重補充:「進去店裡,人家會看你啊。他會判斷你買不買得起、你是不是這間店的風格。」
當然,現在的他們已然能自由地走進店裡買衣剪髮,雖然對熊一蘋來說還是得「鼓起勇氣」,才沒問題;而沈信宏則是跨出了多一點,他開始感到自在:「其實就是當你賺的錢夠了,經濟獨立了以後,對啊,你會很開心可以進去買衣服,不用管零用錢多少。」他與他的花襯衫一致,美麗新世界自在開展。
發光體與趨光體
沈信宏在散文裡,寫過這樣一段文字:
「從此以後我也將成為樹或是安全駕駛,有時則是美少女戰士擁有無限次變身的機會,無疑地這就是成為更好的男人的方法。」
更好的男人,是樹或是物、是超能英雄還是人類?問起他們心中是否有一個這樣的想像原型。沈信宏不提父親或是長輩,而是帶我們回到從前,想成為的男性,更像是每個班級裡面的核心人物,比如,高中時每個班上都有的那種運動男孩。「你開始會去買一些他風格的衣服,會模仿、學習他,每個班裡面應該都有這種閃閃發亮的男生,吸引著大家的目光。」沈信宏想要成為的模樣,與其說是一個做出什麼事的男人,更接近會發光的人,他補充道:「就是一個被大家喜歡的人。」
熊一蘋花上更長的思考時間,分析與作答這道題目。「好像很難找到,就像剛剛說的,我成長環境一直是女生比男生多(甚至強勢),我好像不需要有一個男人的榜樣。」熊說起自己對父親的形象認同,似乎父親一角,永遠先於男人的身份。
「我後來想了很久,想成為的那個男人模樣,其實很像滅火器的歌。」他們的歌裡,總有一個像是熊一蘋自己,又不只是自己的原型。「跟他們一樣,我是高雄人,青少年時期可能也是那種『歹子』,然後上台北打拚,追求成功,才慢慢跟家裡和解。」熊一蘋心中的男人,竟然很接近傳統台語歌裡的男人形象,「就是那種很隱忍,從不多說什麼,攻擊性不會很強的男人。」
長大後的男孩,如今也有被誇獎「很男人」、「很 man」的時候,每次聽到這種評價,他們心中也各有回聲。
熊:「不是,對方到底看錯了什麼?」
信:「雖然知道這就是一個『good』之類的誇獎,但對方並不是真的對你的性別氣質有很深入的觀察,才說出來的,可能只是想表達你力氣很大。」
沈信宏的自我認證,大約是一段長長的過程。如同謝凱特為他寫的推薦序裡所見:「異性戀,已婚,育有一子一女,像信宏這樣被我歸類在直男的人物,或許也像不見蹤跡的書名一樣活得沒有困惑,但更可能的,是他把困惑藏得很深。之所以反身觀看、描摹自我,想必是當今對男人的預設值已經不敷使用,於是試圖鬆動框架、增添選項,調整男人的『身形』。」信宏說了:「從小到大,你還是會一直想要符合大家對你男人形象的期待。但是後來發現,每次都做不好,所以後來就算了。」

「我就做自己的樣子,不要管別人說男人要怎樣。」當然,自在總還是得拿出什麼來交換。「可能真的也要達到一些經濟地位或走入家庭,人家才會被滿足期待,才比較不會對你的男性氣質,有太多的質疑。」至此,信宏的說法是:「你才能比較坦率地,把你本來隱藏著與一般男性氣質不一樣的東西,展現出來。」
好異男?壞異男?
除了成為男人,當代男性的課題不少,像是得經常被別人、被自己放在性別議題下檢查:「你是一個好異男,還是一個壞異男?」
「性別議題,與其說是一把尺,不如說它是我內在的一個創傷。」熊一蘋坦承,曾經被「自己到底夠不夠格當一個足夠友善的異男」這件事自傷。最早接觸到討論男性「不夠同理」的議題時,他會驚慌著自問:「我也有這個習慣,那要怎麼辦?我要改掉嗎?那改掉不等於把我的本質切掉嗎?空出來的一塊,怎麼辦?」那是一段他極端迷惘的時間,相比於許多能快速換位思考的同性,他的自傷感來自:「我比較難代入人家情感的特質,被點出來了,我很受傷。」
直到最近,他才試著尊重自己的異男認同,「就像我尊重女性與同志,因為不清楚他們的想法,或他們在成長過程中背負著哪些不該被輕易碰觸的東西。」那麼自己也是如此。現在他終於知道,可能就是不會有一個好異男 sample,也不會有一個壞異男 sample。「我就是不要再卡在好壞這件事情上面了,我就是異男,就是這個樣子。」
沈信宏認為好與壞是從我們身處的教育與文化成長來的。「因為開始有了這樣的性別意識,才有了改變,讓你意識到不能這樣說話、不能這樣表現。」當然,這始終是一場硬戰,沈信宏以自己的兒女為例。「像我兒子或女兒,還是會聽到很奇葩的話。比如長輩跟女兒說女生不能怕燙,因為以後要做菜;男生不能哭,也不能帶粉紅色枕頭去幼兒園午睡。」以父之名,信宏覺得實在太恐怖了,這是一個仍然在發生的群體洗腦。「我會試圖洗回去,可是你沒辦法靠一個人防堵、一個人糾正,這是很無力的。」
但是某些私密時光,只有同伴與夫妻關係的時刻,他們兩人都會試圖更真誠地與另一半、另一種性別的對象溝通。沈信宏認為,那個狀態反而比較舒服,誰都不用那麼嚴格,可以更輕鬆地討論為何被影響、為何這樣想。「不那麼政治正確、性別正確的時候,其實也沒有那麼不好。」
熊一蘋也是如此。「我女友可能會看到一個事件,說這個男的怎麼可以這個樣子,然後我會告訴她,因為異男的成長過程與訓練,讓有些事變得做不到、有些事又變得理所當然。」
這並不是在幫誰說話,也不是認同。「因為我就是異男啊,就跟女性主義讓很多女生告訴我們,為什麼女生成長過程中,會這樣子表現一樣。比起罵來罵去,這種交流與互相了解,不是比較好嗎?」儘管性別論戰裡,臭異男和死台女的戰爭不會停止,但從相處中了解各別性別的限制,或許才會產生第三條路。

【性別啟蒙之書】
最後,今日異男談心的現場,也請他們在記憶中選出一部印象深刻,使他們對主流性別觀點開始思考的作品。
熊一蘋的選擇:《亂馬二分之一》
我小時候看到亂馬時,非常非常衝擊。
因為雖然他的性別認同很明確是男生,可是他有時候會選擇變成女生買包子吃,只因為老闆會多送一個;或是想要吃甜食的時候,他會用女生的身分去享受。我就覺得,天哪也太爽了吧,當時年紀小,只知道性別有兩種,憤慨跟不平的是,為什麼每個人只能選一種。
不知道該說它讓我有一個更加多元的性別想像,還是讓我變得一直無法建立自己身為男性的自覺。但它確實是我啟發我對性別思考的啟蒙作品,或許應該說,它延後了我自身的性別啟蒙,也有可能。
沈信宏的選擇:《盛夏光年》
小時候不知道,喜歡女生好像是一件很理所當然的事。不會去想「你必須要喜歡女生嗎?」曾經跟男生,也有一些交心的時候,但是你不會覺得那是喜歡。一直要到比較晚,看到了《盛夏光年》,才去回推,才會發現,原來生命中,你可能是別人的余守恆,也可能是別人的康正行。那些曾經可以交心的男孩與那個親密感,它很特別。
或許小時候的喜歡,不分男生或女生,看了這部電影,我才想到可能有些人,再推進一點就可能不太一樣。我覺得,年輕的時候我們的喜歡其實都是無性別的。
當男人們戀愛,當男人們長大,請成為一個男人,不要只成為一種男人。就跟所有人一樣,我們最初想成為的樣子,它並沒有性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