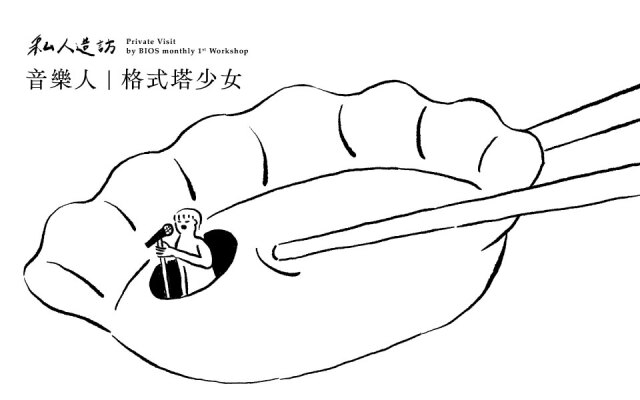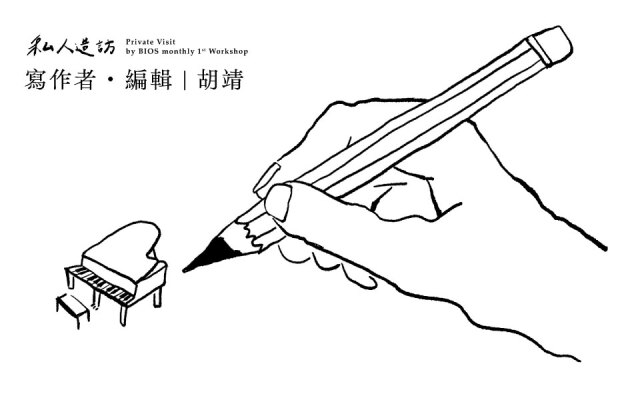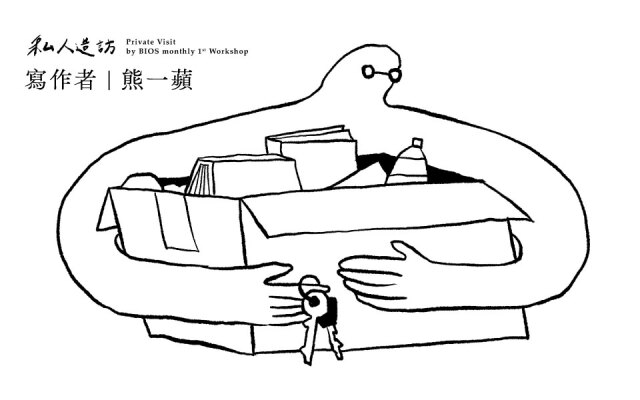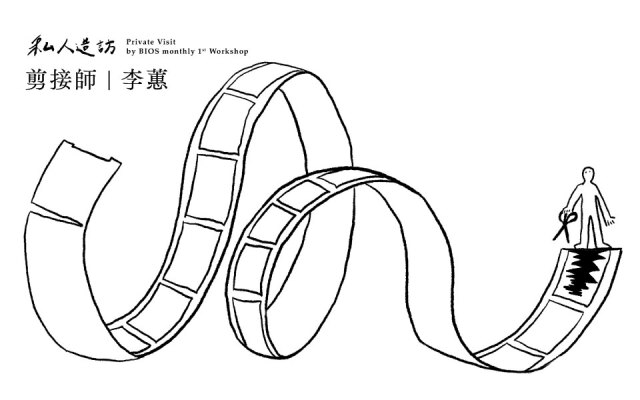私人造訪・魏于嘉 OA|我是半個編劇,但什麼時候算是「一個」?
雷聲從另一頭傳來。
今年頻傳的颱風消息暫且打斷 OA 的自我懷疑。
27 歲北上讀台大戲劇研究所,三年磨練,畢製兩齣戲《現世寓言》與《媽媽/歌星》,前者摘下台灣文學金典獎,後者獲得台北文學獎優等,看似拿到編劇出道的入場券,她的懷疑總是比肯定還要多。
台灣文學金典獎劇本組得獎感言她說,自己算是「半個劇作家」了,語帶興奮伴雜著一些疑問。那是十年前,她三十歲:「今年剛滿三十,得了人生第一座文學獎,古人常言三十而立,立起來之後,究竟是蹦蹦蹦的往上跳,還是咚咚咚的往下沉,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十年後的現在,OA 從台北搬回老家台中。她坦言,可能也是她累了吧。除了看戲與朋友吃飯外,她是個不太出門的人,還補了一句:我一直都沒有很適應都市生活。
出門看什麼戲?OA 說自己的品味怪,時常與他人呈現大逆風的狀況。「我也不太敢講啊⋯⋯因為我知道大家覺得那個好,那講出來,人家覺得你誰啊⋯⋯」
「那個叫什麼名字,去年那個⋯⋯(雷聲轟轟) 那個導演叫 ⋯⋯(轟隆轟隆),你跟那個比,那個渣渣,你是個菜渣,欸,能講什麼話啊。」
字面語氣看似無奈,實際語氣並非如此,從耳機傳來的,是能和雷雨抵抗的爽朗大笑。
我是藍領小孩
她說,自己算是比較少的那種人。
少,是體感難以補給的匱乏,是成年後意識到在資源上無法彌補的龐大差距。家裡是開小工廠的,她迅速地補充:小工廠是只有三、四個人的那種,那種家庭小工廠喔——「我說的比較少的那種人,是因為我是南投來的小孩。」
「如果真的講藍領的話,我就是藍領小孩,我是認真的藍領小孩。」
她說,直到 20 幾歲前,自己是沒有任何藝文資源的。
相較傳統家庭的寄望,家人對她的期望更簡單。最好就是妳長大了,去工作,學歷重要嗎?家裡並不在意,回來幫忙家裡。最大的期望不脫父權輩的家庭想像——結婚。生個孩子。然後呢。
「結婚也是有城鄉差距的。」城鄉差距點出的不只是資源分配多寡,若粗暴地以 27 歲做為分界,是一個人從此有了光譜般,「那端」與「這端」的人生分別。27 歲前的那端,OA 在中部唸書,過去讀五專是唸理工科的,大學又跳到外文系。
那端的友人大部分是上班族:人生進度大部分在 30 歲左右結婚。結婚就包括買房子、生小孩、買車。跟台北生活者相比,中南部的夫婦兩人努力一下,或許買得起房。
「我們從事這個行業——藝文產業的人是非常少數之少數,尤其還要在台北比較多一點點。」而這端的朋友們,大學戲劇系出身,或者在大學就對戲劇有濃烈傾向,一路讀上研究所,活在劇場圈內,相比另一端朋友,有買房結婚想法的人不多,包括即將奔四的她也是。
看似有著自由不受拘束的人生,關於創作者,是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浪漫想像嗎?
OA 卻反問,「藝術真的很偉大嗎?藝術真的超棒?劇場大家都要來看嗎?」
「拜託,劇場是一個千萬分之一的人才會進來的地方,要知道這一點。」OA 在那端被視為異類——浪漫的異類 aka 文藝青年——起床鬧鐘不用再按N次稍後提醒、中午避開社畜優雅地進食、週一不用上班順便去看個電影,被那端朋友投以無數羨慕的眼光,然而位在這端的她表示:可是這沒錢賺啊。
垃圾模式
耳機繼續傳來的模糊的聲音。OA 用著有點陽春的白色有線耳機說話,看來我們的耳機都不是太好?
「有聽過台語一個詞叫 uē-sái 嗎?」「buē-sái?是那個『袂使』(台語:不行)嗎?」「是 uē-sái,如果你要用國字寫,它就是話語的『話』,然後大便的那個『屎』。」
我才曉得,「話屎」就是 Gossip Talk 的意思。根據心理學的說法,一起講八卦有助於人際關係的維繫,行走江湖,這是在所難免的事。「不是說自己有多高級,只是不想有天成為耳語的源頭,不想變成話屎的事主啊!」OA 說,劇場是一個很強烈、很強烈追求人際關係的地方。
然而混藝術圈,免不了交流意見的場合,面對一個所有人大為讚賞、但自己並不喜歡的作品,OA 為保人際和諧,總選擇當啞巴。反正講不了什麼好話,那乾脆閉嘴。「因為對別人來講,可能是 LV 啊。那個我的視角,我看覺得像垃圾。」
撿起地板的紙屑,不難。那似乎更接近紙屑飄在半空,落到地面,也就是在變成垃圾之前,上演要不要指出屑屑的情境喜劇,歷經百轉千迴,使她選擇放在心中。
「指出來(垃圾)就會被說——哇你好髒喔,為什麼你看得到垃圾,只要講出來就一定會跟人吵架,可是我心裡就想說,『哇,天啊,真的不知道大部分的人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不喜與人爭執,也不太經營人脈,OA 坦承,這就只是選擇而已,「啊自己不跟人家玩,為什麼還要覺得人家要找你?」
但話鋒一轉,OA 在大學部學生面前,也會語重心長地提醒:「在大學時期是最容易交到朋友的,盡量能夠交朋友就交。講實話,大家互相吃口水過活,就是這樣,真的要跟團體一起過,比較容易活下來,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話說,她也到了被稱呼為「老師」的年紀。「被叫老師的時候,我就開始發抖。」對於名聲有尷尬癌的 OA,連稱呼都造成她不小的壓力。
她不是那種「視名聲位階為糞土」的狂狷之士,做個市井小民也好——「創作的人就是很平實的在做自己,默默做一些事情,換一點錢嘛。講難聽一點,我們也是來賺一點臭錢啊,賺一點錢過日子而已。」
0
「喈喈叫(kainn kainn kiò)沒路用。」OA 不喜歡「喈」(kainn)。
十年以來的創作,雖能養活自己,但談到編劇生態,能夠維生到何時,一陣清風吹過,「還是回到收入。這很殘酷啊。我那時覺得自己只是半個編劇⋯⋯」OA 收斂起笑容:「後來會想,那怎樣才算一個編劇?」把寫劇本當作興趣,幸運的話,這份興趣成為工作或許能一直寫下去,但沒有被搬演上台,一切就是 0 ——收入 0、年資 0、名聲 0。
「能夠寫出一個劇本算編劇,還是你的本有被演出算編劇,或者你能夠以此為生算編劇?」她說,成為全職編劇是需要勇氣的,勇氣的背面是——假使無法適應市場需求,那就只剩窮困潦倒的獨角戲。
但還是有很爽的時候,「就是劇本全部寫完後的五分鐘。寫完了,不錯喔。」僅此而已。五分鐘結束,又會墮入漫長的改稿修羅場,這裡不好、那裡不好、自我懷疑,咻(修)咻(修)咻(修)⋯⋯修成通通都忘掉原本寫的是什麼樣。OA 體認到編劇最需要的技能,第一是人際溝通、第二要有耐心,寫劇本能力則是排到第四、第五之後。
但屏除現實,只有一件事是必要的:疑惑。
她說寫《大動物園》時,至少經歷了三種以上的情緒調換。2018 年與臺南人劇團合作,以木柵動物園搬遷事件為發想,討論在世界變遷下,人類如何與動物共存的主題。
創作是把自己發射到另一個世界去,必須填充的彈藥是疑惑。「其實只有你能解答自己的疑惑,但解答的東西不是一個完成值,你知道嗎,那是循序漸進的改變」。
但,「我是整個劇組裡面對動物最無感的人。」OA 刻意疏離,她害怕其他生命的死亡,對於動物生存權利的情感連結相當低。一開始收到合作邀約,像寫命題作文似地蒐集相關書籍、資料來閱讀。
《大動物園》以木柵動物園搬遷事件為發想,討論在世界變遷下,人類如何與動物共存的主題。(攝影:陳又維)
《大動物園》(攝影:陳又維)
進入寫本階段前,她獨自逛動物園。相較感受性強的創作者,她說自己是理工腦。但逛動物園那天她非常情緒化,「我都可以有,我真的是看到那種⋯⋯ 我還記得我應該有落淚,我可能就在某一刻,就默默的⋯⋯」儘管她也說不清楚落淚的理由。
她把疑惑、以及對解惑的迫切通通寫進劇本——「還有很多別人不一樣的樣貌,即便如此,還是能從你的答案,去把它們創作成一個作品」。
在黑暗中爬行
然而,《大動物園》票房非常差。OA 肯定地說出「非常」。
那時在水源劇場連演三週,主打長銷型作品,推票推得辛苦。OA 平坦地說,「我不是能扛票房的人,我沒有任何票房號召力,我沒有什麼,也不會去干涉或者介入票房。」但她知道劇團的所有人都很辛苦。
偶然在演出期間,轉輾收到陌生人來訊:「我可以冒昧請問你嗎?」「為什麼你那麼知道我們在想什麼?」OA 沒想到,《大動物園》評價在動物工作者的圈子間傳開,讓許多不熟悉劇場的人因此踏進劇場。
觀眾難得的反應與回饋,固然讓人振奮,但 OA 還是選擇了疑惑,「如果我寫一個劇本,很懂的人很懂,可是不懂的人很不懂,那對我而言,到底算是成功還是失敗?」她說,這是共業承擔,團隊來找你,導演集合人手,如果大家的意見重疊佔比率,能夠達到六七成就很高了。
何況在編劇這條路上,難以控制的事情比想像中得還要多更多。
2018 年後,OA 除了接劇場邀約的案子,影視圈的劇本頭也找她進來。這幾年除了《返校 Detention》的影集外,曾經著手三到四個影視的案子。
秉持著陌生友善原則,凡是工作案找上門,找她聊聊,她不太拒絕,但也同時悟道「聊了不一定會做,做了不一定會做完,做完不一定是做好。」進入影視產業工作鏈後,劇本端最常面臨的是各種喊停、各種延後。
她這樣形容:我們做的事就是一個人面對黑暗。「我們永遠,因為我們都是走在最前面,我們做的事是從整部劇的開始啊。」
又是另一個屬於編劇的 0。
活著就好
「啊,不行耶——真的滿腦子就會是那個畫面,我們寫劇本一定要有畫面感。如果腦子都是那種東西,怎麼可能會健康啊?」寫劇本時自然會有畫面感,若是寫類似《舞伎家的料理人》的情節——少女情誼、人們互道關心、食物療癒的畫面,就算晚上趕稿,肚子有點餓而已。
但如果像《恐怖家庭醫學》般的題材,想像北野武面無表情的說著「如果再這樣置之不理下去,後果會不堪設想!」畫面總是一個面目猙獰的女人,有時跌倒,有時捂臉⋯⋯ 下面字幕打著「究竟是為什麼?」、右側的小標是「OO痛危機」,還有聽了讓人疑神疑鬼的配樂,的確有害健康。
那個談起編劇時似乎總也不怕的 OA,原來很怕死。
她並沒有要分享深刻的生死觀,簡短一句話帶出一個事實:做什麼事情也比不上自身健康與精神狀態穩定。人們對於創作會有無限的憧憬,燃燒自我,為了達到創作的最高境界,但這在 OA 看來,「沒這個會死」才是把自己給逼死的源頭。
例如人們常有編劇或文字工作者會去咖啡店寫稿的刻板印象,但實際上她對咖啡一滴不沾。當開會大家要買咖啡,又會有點難以理解,為什麼沒辦法喝咖啡。開會也是。當劇組沒日沒夜地工作,「晚上開會影響睡眠」的需求實在難以啟齒,要等有了一點工作資歷,才有辦法開口。
「所以我每次都開玩笑說,不知道為什麼我在劇場啊,到現在還是講這句話,不管個性或身體都是。」
台大戲劇研究所時期,每當同學對未來有所迷茫,會找老師討論商量。老師都會一率這樣說「能找到別的事情比劇場更容易活下去的,就去做別的。」在對戲劇抱有熱情才來讀研究所的同學耳中,聽起來殘酷:人真的能如此輕易放棄嗎?
「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要做。」OA 如今懂了這份殘酷:「如果要做的話,就盡量不要在這個過程倒掉吧。」
「我說的倒掉不一定是指說,不做這件事情(編劇)就算倒喔。如果找到更想做的事情,或許是更健康的事情也很好。」
直到有一天可能,可能有一點點什麼。我們都是努力活下去到可能有好事發生的人:「還能夠慢慢的活著,跟慢慢的活下去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遇到好事之前,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私人造訪 Private Visit】
BIOS monthly 首度開設媒體寫作工作坊,真是辛苦了(自己說?)最後一份稿件,由 BIOS 及講師群媒合(=通靈)陌生相遇可能帶來的火花,讓學員們走進專訪現場,展開一場私人造訪的交流與寫作練習。
*本工作坊獲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藝文補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