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書寫治癒任何傷口:專訪馬欣《反派的力量》(下)
翻開作者簡介,會發現馬欣更精采的履歷是擔當各種音樂評審,以及撰寫樂評。她回憶學生時代去余光音樂雜誌打工,最幸福的就是整理唱片庫,「從一排排抽屜拿起一張張老唱片,讀上面的簡介,那真的很開心!」這樣的著迷,同樣源自哥哥姊姊的收藏:
「他們留下一大堆六、七零年代的黑膠唱片,讓我很早就接觸西洋音樂,聽了覺得實在太動人了,就會想翻字典看他們在唱什麼。」而當年的歌詞和現在很不一樣,充滿隱喻及深意:「瓊拜亞為什麼會寫那樣的歌詞給鮑伯迪倫,那麼愛他那麼憧憬他的才華?還有〈The Sound of Silence〉,那歌詞像詩又像預言:人們會對霓虹燈膜拜,聽不到對方在說什麼,以後的歌也不會被傳唱……這些都完全符合現在的光景。」
形容自己小時候是個沉默、不被老師理解、被當成怪胎的小孩的馬欣,說當初聽到第一句歌詞:“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就想掉淚,因為那呼應到那麼小的自己,不知怎麼對爸媽、對老師表達自己的心情。她也說起人生中第一張唱片,那是媽媽帶她去國父紀念館旁邊的麥當勞,路過一間唱片行,她進去跟老闆說「我要買披頭四。」老闆說小妹妹妳要買披頭四是幫誰買嗎?她說「我要買披頭四,你幫我選一張!」從此像著了魔一樣,一頭栽進音樂這無形的、永無止盡的寶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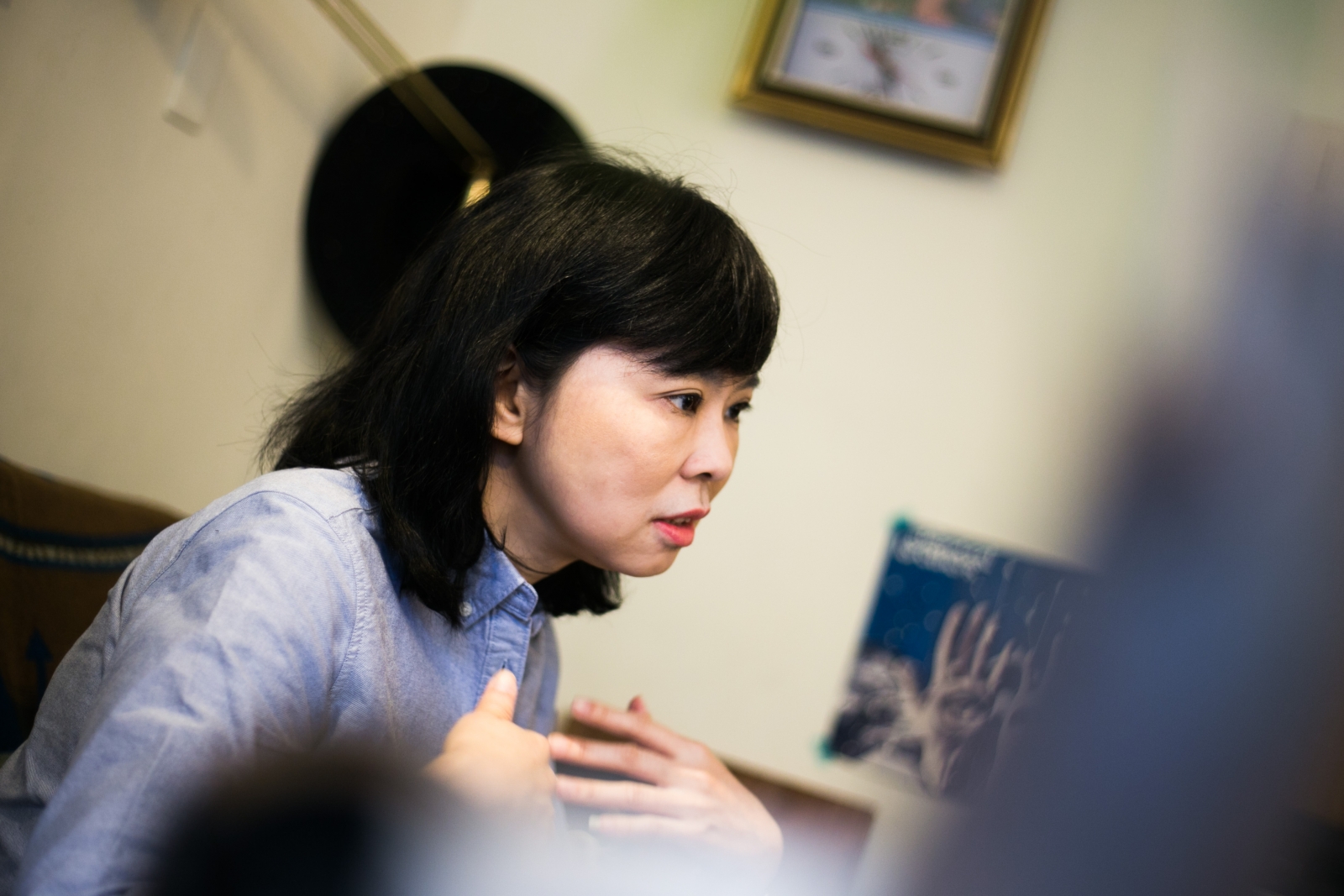
「我們早就失去我們的音樂遺產了」
我趁勢問,那對台灣音樂產業的現況,有什麼看法?馬欣斷言「我們還沒到(商業銷售的)谷底,還會再往下。」她說前幾年是靠星馬的歌手拱起來的,如今星馬撤了,再加上大陸的創作/唱跳歌手紛起,兩年內一定就不會再稀罕我們的人過去。「屆時,無法再賺那種十倍、二十倍演出的熱錢,台灣就得反思自己的音樂品質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她舉武雄的「出得起香蕉,只請得到猴子」說法為例,註解台灣對品質的不尊重:「先砍前端詞曲創作者的錢,反而後面的包裝都加倍,」她語重心長地下結論,「我們早就失去我們的音樂遺產了。」
於是現況,便如李宗盛說的:你丟垃圾給聽眾,他們也吃。「但這不是消費者的問題。你沒給他美感的環境,他會以為音樂就長這樣。」馬欣嘆,我們太著迷於九零年代那種號子似的熱錢,天上掉下銅板就會忍不住去接,沒考慮底子到底夠不夠好?「根本在於,沒幾個唱片公司的主管敢問自己:我做出來的東西自己會聽嗎?會反覆聽個十遍嗎?會在五年後再拿出來聽嗎?」以前滾石的時代也許會,但現在早就不是這樣,變成什麼東西合乎當下的 tempo(節奏)就趕快出。「其實都不是外敵,是我們的品質先下滑,人家才有機可趁。就像金瓜石的淘金熱,淘光了就廢棄了。我們到現在還在找金瓜石的剩餘價值。」
然而,唱片銷售會下滑,是否也因為「數位串流」造成了消費行為的質變?對此她不但覆議,還點出了癥結:「串流就代表你什麼都能得到,也就代表你什麼都能晚一點再聽。這『晚一點』的念頭就是對音樂最大的傷害。譬如我買披頭四那天,別的都不想聽我只想聽披頭四,但現在串流一打開,可能正在夯什麼我就聽聽看,披頭四就下個月再說吧!最後就變成永遠不會聽。」她形容現在聽音樂就像去大潤發或 IKEA,今天買杯子,明天買掃把,那清潔拖就永遠擺在那邊。「所有商品都變成一次化,音樂的獨特性也被稀釋掉。就像 Mitty 那部電影(《白日夢冒險王》),現在的雜誌和唱片一樣都是夕陽,讀者人人有手機,網路上照片那麼多,出版社就不會再去找專業的攝影師,花時間去山裡靜靜等待拍一隻雲豹了。」

人人舞台化的時代,交流的焦慮
聊到這,我想起馬欣曾經說過,網路時代容易讓人「舞台化」,我問,這是悲觀的描述嗎?她想想回答:這其實有好有壞,端看你對它的依賴,及能不能在「上台前」養成獨立思考和獨處的習慣。「如果有,就算把自己舞台化,你也會知道自己需要多大的舞台,如果只需要 Legacy,就不會為了登上小巨蛋而迷失自己,或因為沒登上而失落。」她提醒:別舞台化到失去本體性,要知道自己的舞台是怎麼搭起來的,及台下的腐蝕性有多快。當它開始腐蝕的時候,有沒有抵抗力去面對?「戲棚子總會拆,拆的時候你如何面對自己,如何獨處?這才是最大的課題。」
她也感嘆,網路上人太多了,很容易有渋谷街頭那種人潮一沖就散、自己無足輕重的感覺。「在熱頭過了之後,突然覺得自己無足輕重,才會意識到這是幻影術。幻影術很好玩,但你不能變成只在裡頭尋求溫暖,這『尋求溫暖』的動機很可怕。你可以維持三十七度 C 就好,但如果要四、五十度,那就會自我焚身,變成因為沒有人按讚和回應而難過。」
我也問,那對於現代人溝通的簡訊化、數位化,有什麼看法?馬欣說她覺得《雲端情人》的詮釋是最貼切的:「我們每個人都變成只會 po 幾句文,沒辦法好好溝通,只會用 LINE 傳符號或一句話,但那不可能是完整的交流。於是這反而造成交流的焦慮:亦即你很想溝通,但不知道要講什麼,心中有太多東西藏著,又永遠言不及義。別人凡事都覺得你幹嘛不 LINE 我就好?幹嘛打來跟我講一小時煩死了?而且每個人都忙,就慢慢變成有很多心事在現實裡無法消除,只能跟貓狗講,或只能跟雲端情人講。試想:如果有個電腦,她那麼像人,又可以給你那麼風趣的回答,誰能抵抗?」
「寫下去,無論任何傷口都可以被治癒」
最後我問馬欣,身為一個寫作者,最快樂的是什麼時候?她想了一想回答:「無時無刻。」她說寫作有個好處,就是你會成為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且這朋友永遠不會離開你,就變成無時無刻的快樂。雖然那朋友有時候很煩,會一直逼你去寫,或突然不想寫了,但寫作最大的好處就是作品永遠比寫的人聰明。「你的筆會帶你思考,把很多脈絡、思路整理清楚,就像《愛麗絲夢遊仙境》的白兔先生,你會發現原來自己這麼想,原來我的潛意識這樣看事情,那不是虛幻的,而是幫助你釐清。」她非常鼓勵不管有沒有發表的慾望,都用書寫來整理自己。「那真的會把你帶到一個比較堅強的地方。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你的潛意識就可以有多大,甚至更大。」
訪問最後,馬欣提到《鋼琴師與她的情人》:「像他們在沙灘上彈鋼琴,那麼惡劣的環境,卻很快樂。她說她的鋼琴很聒噪,就像筆也很聒噪,但是一直寫下去,無論任何傷口都可以被治癒。如果你有煩惱,就慢慢寫下來,不管有沒有發表。」那是個和自己較勁的過程,就像原本困在一個小房間,覺得好吵雜音好多,你用手上的筆,或繪畫的筆去開鎖,就會進入另一個房間,前往更寬闊之處。

訪談結束後,我和馬欣又閒聊了一陣,關於 freelancer(自由工作者)的作息管理之困難,讓她每天四點睡變超級夜貓子(自由讓人晚睡,絕對的自由讓人絕對地晚睡!);也聊到影痴的生活永遠在焦慮和趕場,深怕趕不及新片又下檔了(要死了!我還沒去看《鳥人》)。
我們相談兩小時,那文字密度十倍於臉書,百倍於 LINE。結束後道別,又各自趕電影去了。回家我點開賽門與葛芬柯的〈The Sound of Silence〉,一遍遍聽:1964 年原版,2009 年搖滾名人堂紀念版,《守護者》電影配樂版⋯⋯當然靠的還是串流。“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終究論述裡那些時代觀察、科技進展、消費質變,還是要放進個人的生命脈絡中,才能體現溫度。有的冷了些,有的熱了點,不變的是記住它們的人,生命從此被改變。
而時代繼續走,有些句子還是會繼續被傳唱。隔著水,隔著風,隔著不必說的說。

《反派的力量:影史經典反派人物,有你避不開的自己》
作者: 馬欣
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15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