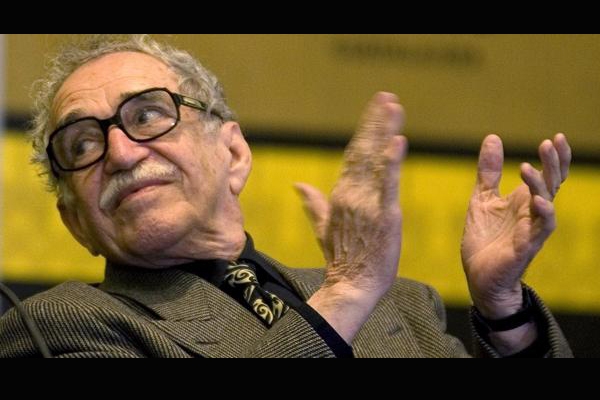有時跳舞|天台上的裸體
三月二十五日,我去香港看了巴塞爾藝術展。
在那之前沒幾天,我才聽過編舞家 Boris Charmatz 在講座裡說到,現在每當舉辦跨類別藝術展,通常你都會看到很多很多的平面視覺作品、一些立體雕塑裝置、幾支影片,還有,那麼一點點舞蹈──好讓大家打起精神來。
香港巴塞爾藝術展也不例外。在一個如此大型的跨類別藝術商展中,有 350 間藝廊帶來的三千位藝術家作品,其中有十幾件較大的雕塑或是裝置藝術會佔據會場顯眼的中央位置,四周圍繞的是坐滿茫然遊客的休息區。為了對凡人釋放善意,這些作品經常被賦予對應社會議題的責任——也就是Socially engaged art ,大型裝置顯而易見的優點就是大,給人熱鬧滾滾又很有份量的感覺,但運費可不便宜,於是藝術展的多數依舊是油畫、水墨、水彩、版畫、複合媒材等能放在屋內一角展示的形式。看完了成千上萬的視覺藝術作品,暈眩中我開始尋找那一點點讓大家打起精神來的舞蹈──還真的有,不多不少,一場。這支名為《公爵夫人》(Duchesses)的舞作,在巴塞爾藝術展精美又具有國際觀的雙語手冊中,這場舞蹈的簡介如下:
Between arid ecstasy, radiant meditation and cruel hypnosis, Duchesses explores an unlikely dance, sovereign and prisoner from the most ancient game of humanity. The hula-hoop, symbol of sexual liberation, becomes for the Duchess a choreographic device, instantaneous and incessant, without a past or future – a universal two-wheeled vehicle.
當權者與囚奴上演一場最古老的人性遊戲。《公爵夫人》在狂喜、冥想與催眠之間,利用象徵性解放的呼啦圈,跳出一部非比尋常的舞蹈作品。Please note that the program contains nudity and adult themes. Parental discretion is advised.
本節目非親子節目,內容含裸露與成人議題,敬請斟酌入場。
看到裸露與成人議題,我稍稍緊張起來,心想要是舞作太過撩人我被引誘了該如何是好,另一方面又得自打強心針,想說我這樣的老鳥什麼前衛表演沒見過,豈是那麼容易就被你征服的嗎?——比起掛在牆上的作品那樣傲視著觀眾的迷惘,表演者與觀眾在現場的對決結果是平等且無法預料的,這就是表演藝術的好(或者辛苦)吧。
對決的夜晚到來,我在銅鑼灣搭上雙層巴士,奔上環城高速來到半小時車程外的柴灣工業區,因為是香港,自然工業區裡住戶也是密密麻麻,辛勤百姓下工放學後正嚼食美味小吃,或信步在夜涼當中。我下車後一時分不清方向,看見路上有三名充滿藝術氣息的人士,連忙尾隨進入了某工業大樓停車場,任由緩慢龐大業務電梯沉甸甸地把我們拉上二十一樓。一到樓上眼前突然一片清澈,這個名叫「永天台」的藝文空間裝潢新潮而簡約,材質光滑的吧檯與書櫃連結成流暢的線條,陽台上燈光與植栽設計高雅,我到的時候,裡面已經站了許多人,除了我之外所有人似乎都互相認識,三五成群站成小圈圈,每一圈都組成平均,有兩、三位外國人加上一、兩位英文流利的有型港人。這個畫面,很香港,而外面確實就是柴灣碼頭、另一面則是港島夜景。
演出即將開始,眾人魚貫爬樓梯上了天台,看到地上擺放的坐墊,有些穿得太好的人士不太情願地拉拉褲管。全體坐定之後,環視四周,與樓下藝文空間裝飾得滴水不漏的氣氛正好相反,陰暗的天台上除了水泥、管線以及通風口之外甚麼也沒有,一切都是裸露的、粗糙的。而舞者兩人也是一樣,一男一女的舞者分別是法國與瑞士籍,他們走近舞台脫下袍子,拎著呼拉圈站上舞台,說是舞台,只是一方有日光燈從下方照射的塑料台,在冷冽的日光燈照射下,兩位的裸體特別死白,他們把呼拉圈放在腰際,就那樣開始搖呼拉圈。我已經讀過說明,所以裸體、慘白燈光與簡陋舞台我都不太驚訝,我知道跟性有關,也知道會有呼拉圈,我以為它們不會做得這麼絕,會先來一點旋律、一點劇情、至少會跳一小段舞,但是沒有,兩人就是直接了當地,搖呼拉圈,and Hula-Hoop only。
這很難嗎?對於會搖呼拉圈的人這當然沒甚麼,但是持續不斷地搖呼拉圈,能撐多久?眾人在黑暗的天台上力持鎮定地忍著不動,剛才那種藝文人士的光芒都被打碎了。我們就在這裡看著舞者乏味重複的動作,看著他們面無表情、為男舞者不斷被呼拉圈打到的小弟弟感到疼、看著兩人的情緒分別進入興奮高潮又下降為精疲力盡,身後工業用電梯的運轉聲是唯一有趣的配樂,偶爾飛過天空的噴射客機簡直就是聖誕假期。我們坐著的椅墊直接放在水泥地上,屁股開始疼痛,雙腿變得麻木,坐在第一排的人忍不住騷動,先後離席,最後當燈光終於暗下,我看了下手機,整整一小時,那一男一女不間斷地搖了一小時呼拉圈。
剛從學校畢業、在拍賣高級紅酒的公司上班的年輕女孩跟我說:「我覺得有點悲傷,好像老夫老妻的性生活。」我說:「不只吧,大概人生的整體說穿了就是那樣了。」但我不覺得特別悲傷,可能是因為我不再年輕,對很多人生的無奈都能泰然處之。
我心想幸好沒有什麼舞後對談,這樣的表演稱不上前衛,80 年代就流行過,但是太坦率、太真心,在這樣一個場合裡,他們的坦率真心讓我心都痛了。這種坦率表演我偶爾還會看到,通常是在一個偏遠但空間寬敞的地方,觀眾大約會在五人到五十人之間,去的都是親友與同行的「稀有動物」,要不是因為這場秀被列入巴塞爾藝術展的一部分,大概不會有這麼多人來看吧。回到沙龍裡,看來觀客們也都已經從驚嚇中恢復過來,容光煥發的藝文界人士又拿起酒杯互稱好友了,在這明亮的社交圈中,我只是局外人,局外人就算不認識主辦人、沒有很多好友一起看秀,也沒什麼面子可丟,回家還能寫一篇文章,標題叫做「天台上的裸體」。
【有時看書 / 有時跳舞】
從大動物園畢業之後,女作家開始關注人類的世界。繞道十四個動物園後,回到美國紐約居住,「有時看書」、「有時跳舞」。這個「一動一靜」的專欄,主要目的是在作品與文獻資料中尋找、拼湊,建構出藝術家們在生活中的形象,換言之——找出藝術家們的「萌點」。
萌,日語漢化之後的動詞,簡言之,就是「被可愛的特質所吸引」。
【何曼莊】
1979 年生,台北人,著有《即將失去的一切》(2009,印刻)、《給烏鴉的歌》(2012,聯合文學)、《大動物園》(2014,讀癮),是作家、翻譯、紀實攝影師、數位媒體製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