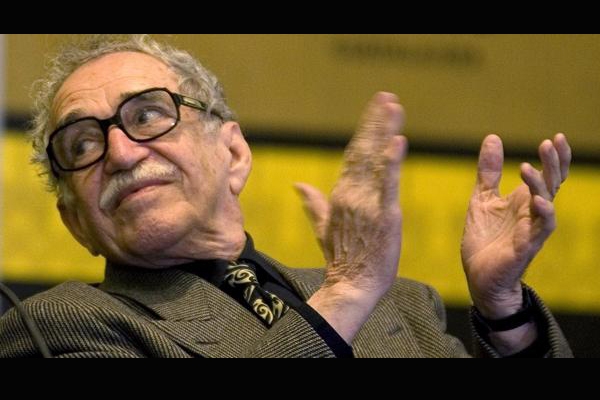有時跳舞|歌劇院裡的腦洞:哲學與預算
我坐在大都會歌劇院一樓 Orchestra 席,心裡知道這個位置的票一張要一百四十美金,今晚上演的劇目叫做《來自遠方的愛》(L'Amour de loin),一名划著輕舟的吟遊詩人在數十條 LED 燈組成的地中海之間,來回傳話,一邊是王子(是一名很壯碩的男中音)、一邊是女伯爵,雙方都拼命想像、不斷美化對方,又患得患失,這部戲在西元兩千年首演時,被說是對保守國家主義的反思,但在我看來,這根本就是當代最重要的議題之一:靠著 messenger 傳話維持的遠距離戀愛啊。
這是一齣法語歌劇,我面前有個小螢幕,提供四種語言的字幕,我選擇了英語,但這樣一來,當我看著台上時,視線就掃不到面前的螢幕,稍微有點困擾,但想想這故事簡單緩慢至此,其實也漏不掉什麼劇情的。幸好從小就懂得自開腦洞,靠著這項才藝,我長大成為一個在劇院裡很能撐的觀眾。
我這個外行坐在位置上,既不懂作曲好壞、也不懂唱腔優劣,面對一個空虛的舞台與單薄的故事,我只好想著,曾經有一個晚上,巴賽爾大學一名前途大好的年輕哲學教授,前往德國拜羅伊特(Bayreuth)歌劇節欣賞華格納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的首演,那不但是華格納耗費二十六年、賭上一世英名的作品,也是國王為華格納建造的歌劇院啟用之夜,吸引了不只是歌劇愛好者,還有大量的報紙記者跟各界高尚的知識菁英。年輕的哲學教授曾經喜愛歌劇、仰慕華格納、還熱情推廣拜羅伊特歌劇節,但在那個眾星拱月的文壇盛會上,他說他看見了「醜惡、怪誕、像是被最強烈的胡椒給嗆了」,他被苦澀的失望纏身,中途離場。那名哲學教授叫做尼采,那是一八七六年八月,從此以後,尼采對華格納的憎惡有增無減,他甚至氣到寫了一本書《華格納事件》(The Case of Wagner),如果這書名還不夠具有針對性,那就再加上副標「一個音樂家的問題」,那年是一八八八年,隔年尼采就瘋了。
看戲人並不是天天都能拿尼采當藉口,但今晚剛好可以,華格納的問題之一可能想給的太多,而今晚我面對的則是相反:空洞。
中場休息,燈沒亮就有人往外跑。
如果你都進到歌劇院了,中場休息二十分鐘還坐在位置上滑手機,那簡直是錯過了歌劇院最精華的戲碼了。中場的大廳中庭,水晶燈從五樓一路垂吊而下,照耀著在這寒冷冬夜精心擠進華服,露出肩背的婦女們,其中某些過度努力的愉快神情,透露出一種贍養費的光暈,而我的直覺果然正確。
「等會,別讓那個女人看到我。」跟我同行的 M 說。「那個穿紅色的是我朋友的前妻。」
「朋友的前妻又不是你的,怕什麼。」我說。
「但是她真的很煩,很做作,關心的只有錢,我不知道我朋友幹嘛要跟她結婚。」
我看著那位太太,她看上去四十多歲,紅色的捲髮中間插了兩朵小紅花,穿著有皺褶的細肩帶紅色緊身短洋裝,在這種天氣裡,好像穿得太少了。
這裡的酒廊,一杯葡萄酒要二十美金,是外面的兩倍價錢。M 說若是他一個人來肯定中途就回去了,我心想,尼采應該也是自己一個人去看歌劇的吧。
「所以下半場怎麼辦呢,還能撐下去嗎?」我問。「我可以。」
他說他也可以。
這時靠近我的四名穿晚禮服的女性拜託我幫她們合照,我等她們站好,四人中有的皮膚光滑緊實,有的則完全選錯了禮服的顏色,但她們都陶醉在這偶一為之的戲劇化氛圍中,歌劇院的戲不只在台上進行,包廂、大廳、階梯、酒廊、甚至廁所裡,都是舞台。我可以嫌棄歌劇故事太單調,但絕對不能責怪歌劇院浮誇,因為鋪張本來就是歌劇的本性,「魅力、刺激、魔幻」,大都會歌劇院的文本這樣寫著。
我原本是與歌劇無緣的人,既沒機會看,也沒興趣。在台北長大,幾乎甚麼戲劇舞蹈都能看到,唯獨歌劇很少,即便住到紐約,林肯中心有三棟建築,最豪華氣派的就是正中央的大都會歌劇院,每季上演不同的作品,我依舊只是個過路人。
阻擋在我與歌劇之間的一道高牆就是票價,歌劇的預算規模龐大,維運歌劇院的成本也比其他劇場昂貴,我在 City Center 花 35 元能坐到舞台角落的位置,在歌劇院呢?上網查了一下,看來這齣全新製作比古典作品《阿伊達》還花錢,想跟一樓沾上邊,最少得花上 85 元,那麼最高貴的票價在哪呢?第一排正中央的票價是 315 美元,但這還只是第二昂貴的,最貴的二樓正對舞台的包廂,一張票 460 美元,每個場次的五樓便宜票 25 元左右都還剩很多,但是最貴的票是絕不會剩下的,這就是歌劇,或者說,這就是奢華,這個晚上,有人會選擇吃掉一塊 460 元的牛排,也有人會選擇買一張 460 元的歌劇門票。從十六世紀末歌劇在梅蒂奇豪門盛世的義大利萌芽以來,就是在婚禮上拿來炫富的娛樂。坐在二樓包廂的華服貴族們,生活百無聊賴,坐在包廂裡互相眉來眼去,不但看戲,也享受被看,然而真正把金權掌握在手中的,永遠是那位按時進歌劇院包廂打瞌睡的老夫人。
中場休息時並沒降幕,那幾千盞 LED 燈組成的海,流洩著蓋滿舞台,在全黑背景中更加閃亮,只有海中央豎立一具現代感十足的天秤式爬梯,看樣子這五幕劇是打算一景到底了。
耳邊很多人說,這個舞台看起來很貴,用 LED 燈幾千盞聽起來很酷,但真的比較貴嗎?
這齣兩小時多的五幕劇只用了一個數位化場景、一具很像從 JFK 機場借來的爬梯,加上小船與船槳,三個主角,服裝毫無特效,連拿出來幫男主角蓋的被子都有點不夠長,合唱組出現時間不到五分之一,看起來都是很省錢的安排。
歌劇的成本除了舞台、服裝、聲光的製作費,還要支付藝術家的酬勞。這齣劇要支付費用的主要對象,包括作曲家 Kaija Saariaho 女士、指揮家 Susanna Mälkki 女士與交響樂團、還有舞台設計是 Robert Lepage 的設計公司 Ex Machina。女作曲家配女指揮家,是這檔戲的宣傳重點,大都會歌劇歷史 136 年,總共只演過兩位女性作曲家的作品,上一次則是 113 年前。
藝術家收多少費用是藝術界永遠的謎,我唯一確定的是:大都會歌劇確實有省錢的計畫。
2011 到 2012 年間,大都會歌劇院搬演的是(把尼采氣到中途離場的)《尼伯龍根的指環》,當年在紐約製作這個舞台的也是 Ex Machina,這齣戲沒有別的,就是花錢,光是演完一輪全長就要花兩天,2012 會計年度裡,大都會歌劇院的收益共約兩億三千六百萬(美金,真的),但是支出卻是三億一千七百萬,有八千一百萬的赤字!同一年度,隔壁棟的紐約愛樂收益是一億九千六百萬、支出是六千八百萬,同樣是歌劇院的舊金山歌劇,收益是一億五千萬、支出是七千萬,管理階層與董事會都表示:我們該省錢了。

一百多年前的大都會歌劇是怎麼工作的呢?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大都會歌劇院一百年」這本手冊中,第一頁便這樣說:「因為第一季上演義大利歌劇賠了好多錢,所以接下來七季都搬演德國歌劇⋯⋯」,原來歌劇院赤字已是悠久的傳統,而為了省錢而演出的德國歌劇第一發是哪齣呢,呃,是《尼伯龍根的指環》中第二部《女武神》 (Die Walküre)──為什麼今晚處處鬼打牆都會碰到華格納的指環呢?一八八三年啟用的舊歌劇院在時代廣場旁,那時當然沒有 LED 燈,舞台布景一切靠手工,演出也是人力密集,後台不但充滿齒輪機械、還得靠人手動操作,演出時甚至有專人躺在桌下不斷對著鍋爐吹氣。
一九六六年歌劇院搬到林肯中心,那一年演出的是史特勞斯的《沒有影子的女人》(Die Frau ohne Schatten),故事設定在神秘未知的南方島嶼上,主角是半人半神的女王,必須在許多幻想場景之間變換,對舞台設計是巨大的挑戰。當然一切背景還是手工畫的,歌劇院五樓的塗料室沒有大到可以讓舞台布景平鋪,所以得分成四塊拼起來;舞台上的布景是真的雕塑,換場景得靠好幾個人推動,排練時導演跟工作人員都在上面跳來跳去,想到這裡,我眼前的燈海閃耀著七彩光芒,五十年前的舞台人員絞盡腦汁用摸得到的東西建構幻想場景,而五十年後同一個舞台,設計師輕巧地用光影仿造海洋。
散場後,我跟著一襲金光閃閃、足以藏進一隻袋鼠的裙襬進了女洗手間,這是近來我唯一進女廁沒見到長龍的一次劇場經驗,我挑了一間空的廁所關上門,發現左手邊的金屬衛生紙座上竟然內嵌一體成形的菸灰缸,曾經有閒階級女士人手一菸,菸甚至跟衛生紙一樣重要的時代,現在劇院已經全面禁菸,但這舊時代的金屬化石卻沒有那麼容易消失,並不像 LED 燈一樣可以說關就關。
我忍不住拍了一張照片傳給戒不了菸的編舞家,他說他想要這個。
「好啦,下次我若有幸再來歌劇院,我就帶一隻羅賴把進來,拆一座這個給你。」
尼采對自溺於殿堂的華格納深刻失望,卻又在比才身上找到了希望。在《華格納事件》一開頭,他說自己聽了第二十遍比才的《卡門》,每一次聽都覺得自己變成了更好的哲學家。就算只是發瘋前的那幾年短短的時光,比才讓尼采知道自己還能喜歡歌劇,知道歌劇還能承載真摯的人性,真正拯救了他的心情。
那天晚上回家後,我便夢見了自己到歌劇院偷拆菸灰缸紙座,有些人偷仙桃、有些人偷火種,而我則是到歌劇院偷菸灰缸,大概這就是屬於我的風雅。
第二天,報紙藝文版對此劇一片好評,票房還不錯,希望歌劇院今年不要再赤字了。
【有時看書/有時跳舞】
從大動物園畢業之後,女作家開始關注人類的世界。
繞道十四個動物園後,回到美國紐約居住,「有時看書」、「有時跳舞」。這個「一動一靜」的專欄,主要目的是在作品與文獻資料中尋找、拼湊,建構出藝術家們在生活中的形象,換言之——找出藝術家們的「萌點」。
萌,日語漢化之後的動詞,簡言之,就是「被可愛的特質所吸引」。
【何曼莊】
1979 年生,台北人,著有《即將失去的一切》(2009,印刻)、《給烏鴉的歌》(2012,聯合文學)、《大動物園》(2014,讀癮),是作家、翻譯、紀實攝影師、數位媒體製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