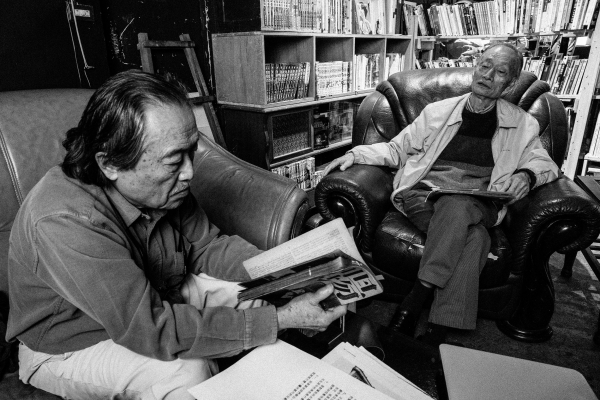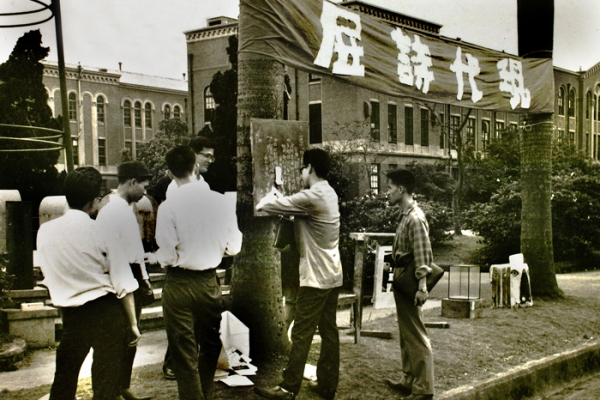專訪紀錄片導演萊拉.巴卡尼娜:即使痛苦,還是會有好笑的事啊
生於蘇聯,長於拉脫維亞,今年 55 歲的導演萊拉.巴卡尼娜(Laila Pakalnina)內心住了一個搞怪少女。兩年一度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請到這位拉脫維亞知名導演擔任焦點影人,稱其「獨具慧眼,經常在平凡事物上發現其不凡之處」,但紀錄片大師飛來台北參展這幾天,臉書上不說電影,而是充滿生活的 NG 片段:想跟粉絲學卻失敗的手指愛心(看起來像手指抽筋);硬是塞進兩個無頭假人模特兒中間拍照,許願自己不會有天失去這顆腦袋。她觀看世界自有獨特視角,能從再平常不過的場景中看出幽默及生命力。
1991 年大學畢業後的第一部紀錄片《麻布日記》(The Linen),拍攝貨車送洗亞麻布料的日常工作,與醫院裡病童的生活互相對照,萊拉便以初生之犢之姿入圍坎城影展。至今累積三十多部作品的她,也隨著這些作品飛向世界各地,是柏林、威尼斯、坎城等影展的常客。她說,電影是她說話的語言,而這種語言,她從十七歲就想學。
其實,我不確定能不能拍電影
「那時候,我突然發現電影裡有很特別的語言、很吸引我。我就心想,好想學怎麼說這個語言。」萊拉說起電影,眼裡有孩子的興奮。自高中以來,拍電影一直是她的志願,她補充道,但在那之前,她的夢想是當冰淇淋銷售員,說完自己咯咯笑了起來。這大概可以說明為什麼她會在晚上八點的老咖啡館裡,戴上老花眼鏡、在菜單上鎖定冰淇淋紅茶。
只是,因為招生流程問題,萊拉剛開始並未如願進入全蘇聯唯一的電影學院,而是先去讀了新聞,「我內心已經想做電影了,所以就選了個感覺比較接近的東西。後來發現,在那種社會主義的氛圍之下,比起做新聞,電影還是比較有機會說點什麼。」若說新聞是窒息式地被控制,那電影大概還有幾個縫隙可以呼吸。畢業後她順著有氧氣的地方走,終於來到莫斯科電影學院,成為塔可夫斯基的學妹。
「那時候(拉脫維亞)還沒有獨立,所以雖然我在讀電影,但我其實不確定我是不是真的能拍電影。」萊拉說,當時說的「電影產業」,其實就只有一間片場,直接受政府管制。我問她,不知道能不能拍電影,為什麼還去唸?她又笑了,音量和聲調都提高,「因為覺得我最後還是會拍電影啊!這就像一個夢想,即便不真實,你還是會想要嘗試。」結果真的被她等到了,1991 年,萊拉還沒畢業,拉脫維亞宣布脫離蘇聯獨立。
 |
 |
 |
我們失去了整個世代的電影觀眾
「電影是我們最重要的藝術形式。」(Of all the arts, for us the cinema is the most important.) —— 列寧,1919
獨立,對拉脫維亞的電影工作者而言固然是件重要大事,但萊拉說,他們在開心的同時,也意識到電影產業整個被摧毀了的事實,「在蘇聯時期,都是政府付錢拍電影,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列寧說的那句名言,電影是最重要的藝術。他或許是對的,但他在講的可能不是藝術,而是將電影作為宣傳機器(propaganda)。」沒有電視的社會主義時代,電影成了最佳政令宣導的管道,當局者當然願意投注資金,然而,現在呢?
「沒有錢啊,前幾年根本沒什麼本國的劇情片,紀錄片相對有點存活了下來,因為不太需要那麼多錢。」拍不出本國劇情片,人們也就漸漸失去了觀影習慣,後來,拉脫維亞就如同其他非強勢文化輸出國一樣,被好萊塢大舉入侵,「我們的電影就失去了整個世代,現在的年長者,只覺得電影是給年輕人看的。」獨立至今二十多年,像一段困難的重建之旅。即使如此,對萊拉而言,拍自己的電影依然是重要的。
「為什麼我們還是要拍電影、不讓觀眾看好萊塢就算了?因為我們要建立身份認同,拍自己的電影、呈現國家的獨特特質。像我覺得動畫也很重要,要給小孩子看自己國家的東西、說自己國家的語言。」整個世界的電影太多了,但拉脫維亞人不拍拉脫維亞電影,誰會去拍呢?我說,台灣或許也正面臨相同挑戰,小國小民力抗大鯊魚,結果萊拉卻不能接受我說台灣小:「小?!台灣有兩千多萬人,拉脫維亞只有兩百多萬啊!」啊,好的,抱歉。
 |
她說,小地方,讓「電影是藝術」這件事變得更單純、合理,不必迎合大眾市場,反倒讓小巧的東西有機會在黯中發光。
「我覺得觀眾多大真的不是問題,那對製作人才有意義。除此之外,每種電影都有觀眾,如果觀眾越大代表電影越好,那全世界最好的電影就是肥皂劇啦。對我而言,商業片是娛樂、沒有不好,人們就是需要娛樂;但藝術是藝術啊,其實就像在音樂裡會有流行或搖滾,即便彼此像不同的星球,但偶爾也會相遇。」
她停了一下繼續說,「雖然不太常啦!」然後自顧自地又笑了起來,繼續攪拌她的冰淇淋紅茶。
想要看懂電影,本身就是錯的?
除了觀眾大小不重要,在萊拉的作品裡,故事線也永遠不是最重要的。我大概沒什麼慧根,初看她的幾部電影時,數不清頭上冒出幾個問號。
《夢之地》(Dream Land)裡,她拍攝垃圾場裡的生命,總是讓人有點害怕的老鼠才剛被她拍的有點可愛,下一秒就被貓叼走;在《水》(Water)中,女孩來到游泳池游泳,竟被管理員警告「水很冷喔,妳確定?」真正跳入水裡後,又發生一連串令人有點毛毛的事件:正經八百的男子朝她吐口水、把一隻隻肥嫩的魚丟進池裡;《黎明公社》(Dawn)中,捍衛蘇聯革命理想的男孩揭發了父親的反體制陰謀,因而展開一部明明以人為主,卻又覺得人不是主角的電影。

《夢之地》(Dream Land)劇照。
《夢之地》(Dream Land)劇照。

《水》(Water)劇照。
「電影的語言是很全球化的,像我現在在這裡,我離我家鄉、拍電影的地方很遠,我說我國家的語言你們聽不懂,可是你們能看我的電影。」她明白自己無法討好所有人,因此更加灑脫,「你不可能為所有人拍電影,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所以我們也才需要不一樣的電影。」有人分析她受里加詩意紀錄片學派影響甚深,也有人說她屬於新寫實主義一派,但萊拉本人並不這樣要求觀眾,在觀影當下別想太多、只要盡情享受與電影的連結。大多數時候,我看不懂。她似乎有想表達什麼,但我無法形容?萊拉看著我說,「或許『想要看懂電影』這個動機本身就是錯的?」她回憶自己第一次看費里尼電影時的感受,「我感覺,嗯,這是個好東西,但我無法解釋好在哪裡。這就是為什麼我通常不喜歡在放作品前對觀眾說話,即使有時非說不可,我也會說,你不需要懂我的電影,因為電影無關理解,而關乎感受和情緒,試著去感覺吧。」她說,像《黎明公社》當然有其歷史背景,大家去查也查得到,但這麼做的意義是什麼?拉脫維亞是個小國,來自各地的觀眾對其一無所知也是自然的。
 |
|
|
去除故事線,萊拉在畫面和音效上花更多時間,回歸自然的狀態,看電影本來就是用眼睛和耳朵,「視覺和聽覺應該各佔 50%,兩個都很重要。不過影像的剪輯我會很快,在聲音上我通常會花四倍的時間。」相較於當代劇情片的配樂時常被擺到最後、製作時間也壓縮,她的想法非常特別。
萊拉曾在一次專訪中提及,自己開始重視聲音,是因為一次在莫斯科電影學院的拍片經驗。當時他們用的是一台噪音極大的老舊攝影機,拍攝過程中不斷發出噠噠聲干擾,最後他們不得不丟棄所有音軌,重新錄音。後來,她便養成了分開錄音、再堆疊音軌的習慣,有些音效也不是在當下錄的,說起聲音,她常常用的是「氛圍」(atmosphere)這個字,或許海的「氛圍」也能疊在城市上啊,她說。
真實的東西,還是要從紀錄片裡拿
從紀錄片開始,但拍電影拍了超過二十年,萊拉不斷在紀錄片和劇情片之間來回,她說,這是她點子不斷的秘訣。「我知道很多導演拍了劇情片,就再也回不來紀錄片了。其實我一開始真的只想拍紀錄片,因為我覺得觀察生命非常有趣、很有啟發性,結果畢業六年就拍了第一部劇情片。」萊拉表情有點調皮,「但那時我卻發現,我還是好想拍紀錄片,我覺得它給我更多素材,拍劇情片當然比較多技術面的成長,但很多真實的東西還是要從紀錄片裡拿。」為了這份真實,萊拉也不怕辛苦,像拍攝《夢之地》,團隊得在垃圾場搭建臨時的棲身處,然後無聲等待,等待一隻鳥、一隻老鼠、一隻貓,最久一次超過 36 小時。
不怕等待靈光,萊拉考究生活,以紀錄片、劇情片雙軌並行的方法,讓自己不至於無聊。靈感枯竭?於她而言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萊拉說,自己並沒有想要透過電影說什麼,一直持續地拍,是她自發性的需要,她表達的方法。
「很多人說人生下來就是在承受痛苦,但對我而言,即便人生真的有痛苦,還是會有好笑的或是開心的事。」她的作品只是如實地反映她眼中的世界,可能有點瘋狂、有點幽默、有點諷刺,甚至有點悲傷、有點詭異。她不把懂或不懂視為觀影標準,鏡頭裡被野放的人與動物充滿荒誕,既然真實世界什麼都可能發生,若我們只是為了正確答案活在這世上,不就太無聊了嗎?
 |
【採訪後記】
這天專訪發生在晚上時間,眾人都有點累了,只有導演還神采奕奕。
有超過十年慢跑習慣的她前一天才飛來台灣,打趴時差,據說早上六點就起來跑步了。
而且她還經過一整天 TIDF 的跑攤行程,甚至因為點了那麼童趣的飲料而笑容滿面。平均年齡只有她一半的團隊到底為什麼這麼軟爛——我們到底在喝什麼提神的咖啡?以下分享導演與冰淇淋紅茶的相遇故事:
「嗯嗯嗯嗯——我從來沒看過這種飲料,我的冰淇淋紅茶(浮誇)」
「(攪攪攪)⋯⋯嗯——看起來怎麼像啤酒?」
『原來啤酒才是妳想要的嗎?約錯地方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