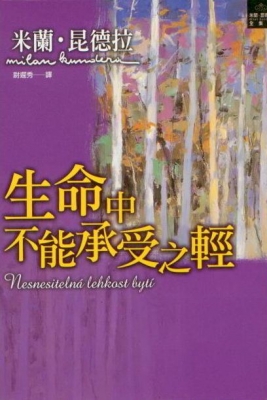愛情常態|雙生火焰——碧娜鮑許《穆勒咖啡館》
她走進來,所有的顛簸顯得太過精確而小心翼翼。她不是她,不是我在等的人。我等的人,她的恍惚裡有一種帶著創造力的恐懼。神色斑駁而肢體從未放棄與時間搏鬥。她將狠狠附著在一個男人胸前,勾著他的頸項,把自己全然交付。不顧每一次剝離與墜跌,她將再一次從地上爬起來,伸出雙手,更強烈地纏縛住男人的身體,以此對抗瞬間落下的疼痛,更緊更無助地,擁抱。
我等的這個女人沒有出現。走進穆勒咖啡館的是另一個亞洲面孔的女人。當然,碧娜鮑許也不在了,換了一個跟她一樣身形修長的舞者。還好,多明尼克.梅西還在,他跟著烏帕塔舞團三十九年了。這樣深切而灼熱的擁抱,他從年輕給到現在。仍是那張雕像般的臉孔,只是,擁抱的時候,雙手禁不住顫抖。
我們究竟能在一個地方停留多久,又能在哪一個地方持續安居?
有人進來,有人出去,穆勒咖啡館不是一座實體環境,也不是一幢神思交會的心靈空間,它是一個盛裝故事起落、愛恨伏流的微型宇宙。於是,他們在那裡反覆衝撞而找不到出路、脫下了衣服又失心穿上、撞開的椅子被一一扶正、來來回回奔跑而漸漸失速崩塌、伸長的手臂在虛空裡打撈無盡……
這難道不是愛情的隱喻?而愛情不也就是生存的隱喻?關乎如何把自己飛快丟失而後緩緩把自己撿拾起來。每一次從頭來過,都是洗刷了血痕之後的明亮初淨。用同一股力量,迎向愛,迎向死。女人擎起男人的身體,甩向一面透明窗扇。男人摔落在地而後爬起,擎起女人的身體,甩向透明窗扇。女人落地,而後爬起。他們是雙生火焰,反反覆覆,擎起對方,拋擲對方,燃燒對方。他們同樣認真,認真對待彼此的重量。他們的認真形成了一種擺盪的虐待,令愛筋疲力竭,連筋疲力竭都被愛甩開落地。
我們和他們一樣,只能在一個地方停留且在那一個地方持續安居。那裡不是別處,就是情感的每一吋變遷。一個人無論到了哪裡,碰到的永遠都是變遷。有恃無恐向外走的人,心裡往往比誰都清楚,家在哪裡,這一點是無從得知的。這種明確的歸屬感,留在一切事物與空無一物之間。就像穆勒咖啡館的舞台上,空空留下散落的桌子椅子,以及在那之間還沒散逸的人的味道。就像舞台三側的透明窗鏡,有些什麼留下來了,也有些什麼在靜靜流動,裡外一切清晰的朦朧的,全都映疊相逢在一面窗扇,令所有故事顯得不足卻又太滿,連傷感與探問也多餘地沒有必要。就像顧城的詩,是有世界/有一面能出入的鏡子/你從這邊走向那邊/你避開了我的一生。
【愛情常態】
我不知道愛情如果不是最暴力、最羞恥、最甜蜜的勒索,它還能是什麼?
這些是我在文學、電影、戲劇、舞蹈、繪畫、音樂裡所理解到的愛情常態。
【吳俞萱】
寫詩、影評,策劃影展與讀書會。
著有詩集《交換愛人的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