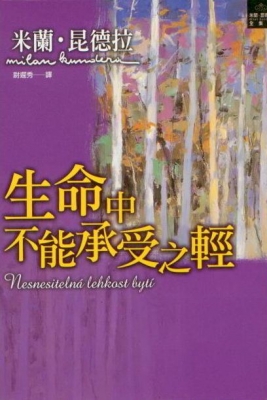愛情常態|凌遲的瞬間——伊薛伍德《單身》及其電影改編《摯愛無盡》
「能說出現在和在,才算醒過來。清醒的部分繼續躺著,往上端詳著天花板,往下探望著床上軀殼,直到認出了我,由此推論出我在、現在我在。……現在並不單純是現在。現在還是個冷酷的提醒:比昨日整整晚了一天,比去年晚了一年。每一個現在都標明了日期,使得過去的現在們全部過時,直到也許──不,不是也許──是肯定會:那一刻來到。」
小說開頭,惡狠狠地說,生活是一個陷阱。活著的人,沒得選擇地活著。
第一次讀《單身》(A Single Man)的時候,我並不喜歡那個清醒、尖銳、憤怒而無所遮掩的老男人喬治。看了湯姆.福特(Tom Ford)改編原著小說的電影《摯愛無盡》之後,重讀《單身》,我就再也無法驅趕,無法驅趕那空洞的黏稠感傷。
生活確實是一個陷阱,讓活著的人相愛,因為相愛而懂得了死亡的無能;卻又讓活著的人沒得選擇地,活在一個愛人不在的世界。《單身》描寫一個失去同性愛人的老男人喬治,為了結束而展開的最後一天。伊薛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自傳式地解剖自身內在與外在的斷裂,呈現六零年代初期美國社會窒息保守的氛圍。
而真正令人窒息的,是每一個平凡的此刻,都因回憶的侵入而成為凌遲的瞬間。小說中的喬治有一種洞悉世事的泰然自若,同時也有一種不受世事運行法則擺佈的孤傲姿態。淡漠而躁進,疏離但時刻繞回圓心,行止超脫卻情繫塵俗的感官逸樂和人際交往。他並非孑然追求純粹精神性的存在,也絕不是渾噩拋下意義、墮入虛無的遊魂;即使他已然看過最美的風景,卻不會躲進輝煌的回憶裡,亦不願奢求或喪志地等候未來。他就是,看透了鏡花水月,還能勇敢醉一回,醉一回再清醒扛起現實的,那種硬漢。忠於幾度死亡和幾度重生的持續擺盪。
電影中的喬治拘謹、易碎多了,他似乎走不出陰影,甚至抗拒承擔活下去的責任,因而純潔地膜拜逝去的愛情。那膜拜一如懺悔,具體地轉化為赴死的嘗試,而那赴死的種種排練,又無異於沉醉在自己無邊無際向下墜落的欲望之中,一面尋求死亡的終極救贖,一面攀緣生活的浮木;他放逐自己,永遠在過往的美好時光裡漂流。雖然悲傷,但卻幸福。(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的托馬斯和特麗莎則是「因為悲傷,所以幸福」。)
於是,電影中的喬治比小說裡的喬治顯得飄忽、純情、溫暖、感傷。電影中的喬治反覆召喚愛情的亡靈,強化自己死去的意志。全片的每一個鏡頭都在暗示著喬治對於死的渴望,而原著小說的每一個細節,都在呈現喬治對於生的欲望。他頂著那副老皮囊,奮而求生,坦然迎擊生老病死,笑看生命的無盡嘲弄,理解孤獨,理解孤獨的必然,因而對生命的苦難,能夠釋懷和寬容。
我好喜歡出現在電影而在原著小說裡缺席的一段話:在生命中的某些時刻,哪怕只有幾秒,我曾感受過一種絕對的清澈。在這倏忽的幾秒之中,寧靜沉寂了雜音,我感受而不思考,一切充滿存在感。我試圖去捕捉、延長這種絕對清澈的瞬間,但它們無一例外地,轉瞬即逝。我的生命就依附在這些時刻裡,它們將我拉回此刻,讓我意識到一切本該如此。
是了,這就是愛情常態。無法緊握,無法追回且又耗盡一生去追念、去沉醉那一刻。無從推諉地,讓所有一切有意義的就是那幾個零星的瞬間,真正感受到自己和另外一個人連結在一起。接遇的那個瞬間,飄搖的一生就有了著落。
【愛情常態】
我不知道愛情如果不是最暴力、最羞恥、最甜蜜的勒索,它還能是什麼?
這些是我在文學、電影、戲劇、舞蹈、繪畫、音樂裡所理解到的愛情常態。
【吳俞萱】
寫詩、影評,策劃影展與讀書會。
著有詩集《交換愛人的肋骨》,電影文集《隨地腐朽──小影迷的99封情書》。